一江碧水中的湖湘文化与生态书写
——刘创诗集《大湖之境》的诗学维度解析
周爱勇
“守护一江碧水” 的时代命题与湖湘文化的精神血脉,在诗性维度上交相辉映。刘创的诗集《大湖之境》以洞庭湖为精神原乡,在碧水烟波之间构建了一个熔铸历史记忆、生态哲思与文化基因的诗性世界。这部诗集突破了地域书写的局限,以 “水体考古学” 的独特视角、“去人类中心主义” 的生态叙事、楚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以及时空折叠的诗学技法,锻造出一套极具独创性的诗歌美学体系。诗人以水为镜,既照见湖湘文化的深层肌理,也折射出当代文明的生态困境,使洞庭湖成为观照人类命运的诗性透镜。诗人以诗性之笔重构人与自然的精神契约,在大湖之境中照见文明的未来。

一、在水体考古学中打捞文明的沉潜诗学
在《大湖之境》中,洞庭湖并非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是一座隐没在湖水中的文明博物馆。诗人以 “水体考古学家” 的姿态,潜入时间的深水区,打捞被湖水封存的历史遗骸。《大湖之骨》里的北宋铁枷是典型的 “文明化石”—— 这个 “锁不住浪的怒号” 的刑具,在枯水季节露出 “乌青发亮” 的真身,如 “沙碛中静卧的千年老龟”,将暴力历史转化为 “泛着湖光的慈悲” 意象。铁枷的 “不锈不蚀” 与 “锈蚀的覆水之声” 形成张力,既是物理存在的永恒,也是历史创伤的隐喻。诗人抚摸铁枷的 “冷峻的物理本质”,实则是在触摸文明的 “青铜色哈欠”,让北宋的政治风云与湖湘大地的沧桑变迁在 “金属脉象” 中重新显影。
这种考古学视角贯穿于诗集中的器物书写。《沉船》里的古船是 “痛饮时间的容器”,“旧物围绕着我 / 我迅速成为一个旧我”,船体的碎裂与诗人的自我重构形成互文;《编钟》中 “龙兽之纹从编钟上跳下来”,青铜纹饰的神性复活,让春秋战国的礼乐精神在 “太阳般的音质” 中跨越时空;《阴沉木》则将千年古树化为 “湖的尽头和墓碑”,其 “收敛和妥协” 的姿态,既是自然对人类暴力的静默抵抗,也是文明在水火淬炼中的涅槃见证。这些器物不再是被动的历史标本,而是具有 “言说” 能力的文明载体,构成湖底的 “文化暗物质”,等待诗人以诗性之光照亮其隐秘的精神密码。
诗人对水体的考古,还体现在对语言的打捞与重构。《洞庭考》中 “水文志翻开的潮汐,无名无姓 / 那些涨落的动词,亟待 / 一柄训诂的桨,测春秋深浅”,将水文现象转化为语言考古的对象;《楚语》里艾蒿、菖蒲以 “中药的芬芳” 与楚人 “穴位交谈”,植物成为解码楚文化的活态文字。这种将自然物象转化为文化符码的书写策略,使诗歌成为一部流动的 “湖湘文明志”,在水体的波纹中映现文明的多重褶皱。

二、生态书写中让自然成为叙事主角
《大湖之境》的生态书写打破传统山水诗以人类情感抒发为主的抒情框架,以 “后人类主义” 视角为切入点,将自然从人类叙事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独立的主体意识与叙事权力。在诗人笔下,白鱀豚、白鲟、麋鹿等濒危物种不再是被观赏、被怜悯的对象,而是作为生态悲剧的直接言说者,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在《白鱀豚走进茶馆》中,“视觉极度退化” 的渔者与 “凭借超声波讯号” 挪移的白鱀豚形成镜像对照。这种对照不仅模糊了二者的身份界限,更深刻暴露出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 “失明” 的本质 —— 人类因过度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丧失了对生态系统健康运行的感知与判断能力。而在《白鲟标本》里,“刷上桐油” 的防腐处理,既是对自然生命的物化过程,也象征着人类文明对野性力量的规训与压制。“希望有一条白鱀豚,在时光里突然转身” 的祈愿,字里行间暗含着诗人对生命自主性的深切呼唤,渴望自然生命能够摆脱人类的控制与伤害,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生存轨迹。
诗人对濒危物种 “临终叙事” 的关注,是其生态书写的另一重要维度。在《濒死的鱼》中,“补丁一样地打在湖滩之上” 的鱼骸,以其 “藐小的鱼肚白” 照亮 “湖的局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鱼骸,其袒露的腹部成为反抗生态暴力的微型舞台,无声却有力地控诉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麋鹿奔跑》里,“胆怯而坚定地偷渡” 的鹿群,坚决拒绝 “投食和驯化”,坚守着 “理想国” 的自由精神,这无疑是对现代文明驯化机制的尖锐批判。诗人的这些书写,摒弃了对自然居高临下的怜悯式观照,而是将自然视为与人类平等的 “生态主体”。当 “大湖羸弱之时”,让 “无法呼吸的鱼” 发出 “沉默的余响”,深刻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本质实则是人类文明的认知危机 —— 人类错误的发展观念与认知偏差,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失衡与破坏。
《大湖之境》将洞庭湖置于生态系统的核心位置,以洞庭湖为依托,让白鱀豚、白鲟、麋鹿等濒危物种成为叙事的绝对主角。在《水中手语》中,白鱀豚用 “流线型的善意” 丈量人类的疲惫,其声呐系统传递的不仅是单纯的生物信号,更是对生态危机的强烈警示。而《白鲟标本》里,刷上桐油的标本 “宛如一面诡异的魔镜”,清晰映照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无情戕害。诗人坚决拒绝将自然作为抒情的背景板,而是以 “大湖希声” 的哲学姿态,赋予沉默的湖水、迁徙的候鸟、锈蚀的铁枷等自然元素以叙事主体的地位。在《守湖人》中,守湖人打捞 “沉没的物种名录” 的动作,与白鱀豚 “失声的咽喉” 形成巧妙互文,生动揭示出生态保护与文明演进之间的深层矛盾。这种生态书写彻底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在 “水穷处” 的留白中,让自然以其原始而强大的生命力,重构诗歌的伦理秩序,也为人类反思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深度。

三、楚文化基因的植物性转译
楚文化的精神血脉在诗集中以植物谱系的形式得以激活。诗人以《离骚》的香草意象为基因图谱,在菖蒲、白芷、菌桂等植物中植入现代性的文化密码。《菖蒲》里,“一丛丛青绿,顺遂心意 / 在泱泱楚水聚集起来” 的菖蒲,不仅是 “楚辞走失” 的荪草后裔,更承担着 “建一个远去的、蓝图中的楚国” 的文化使命,其 “干净的香气” 成为对抗 “横行的疫气” 的精神武器;《白芷》作为 “《离骚》埋下的伏笔”,“白白净净的白芷,不言不语 / 仿佛是做了错事的孩子”,将屈子的忧思转化为植物的沉默美学,其 “根部的痛苦” 与 “楚人心底未愈的痛苦” 形成跨时空的痛感共振。
在《楚语》的宏大叙事中,艾蒿、菖蒲、芷、蕙兰等 “楚国水乡的原住民”,从楚辞中 “跑出来”,以 “萤火虫是水边植物开出的花蕾” 的诗意想象,重构楚地的语言系统。“艾蒿菖蒲们想说出,浅蓝色天空下 / 一群飞离的玄鸟,像夕阳余晖散尽的伤痕”,植物成为历史记忆的携带者与文化创伤的见证者。当 “编钟的余响” 与 “植物的私语” 在诗行中交织,楚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在植物的根系中蓬勃生长的活态传统。这种 “植物考古学” 的书写策略,让楚辞的香草谱系在现代语境中完成 “基因重组”,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刘创的诗歌如同行走的《楚辞》注本,将兰草、蕙芷、菖蒲等香草意象进行现代性转译。《菖蒲》里,“干净的菖蒲拒绝嬗变”,以楚水赋予的青绿 “筹划建一个自己的水乡”,将屈原的高洁品格转化为植物的生存哲学;《白芷》中,“白白净净的白芷,不言不语 / 仿佛是做了错事的孩子”,用拟人的笔触解构传统香草的象征意义,使其成为楚地伤痛记忆的载体。诗人更以 “植物考古学” 的视角,在《采莲图》《荷语》中重构 “芙蓉国” 的美学谱系,让荷花从文人笔下的隐逸符号,变为 “分娩微型江南” 的生命母体。这种 “植物性转译” 打破了古典意象的固化认知,在 “野葱煎蛋” 的日常性与 “纫秋兰以为佩” 的神性之间,构建起楚文化基因的当代传承路径,使诗歌成为生长在湖湘大地上的精神植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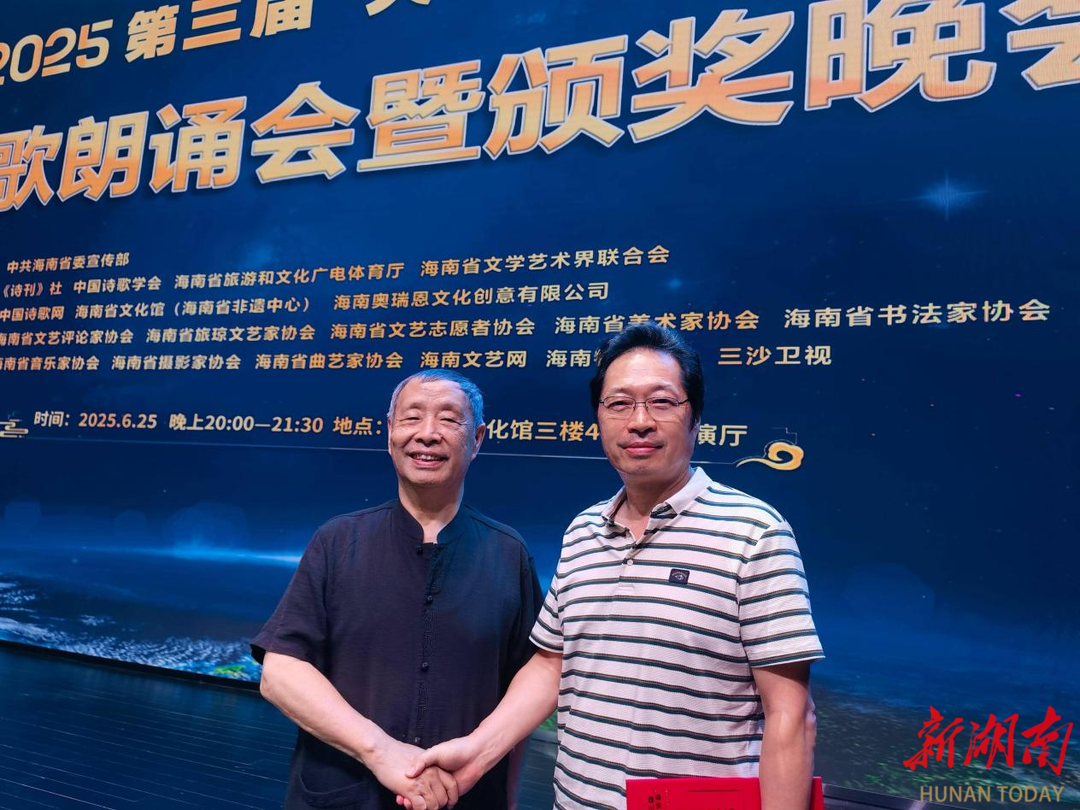
四、多重历史维度的诗性并置
《大湖之境》的时空结构充满现代物理学的哲学意味,诗人以 “时空折叠术” 将不同历史维度并置于同一诗性空间。《黄庭坚登岳阳楼》中,“雨落在不同的朝代,滴答之声 / 清晰地敲打着同样的栏杆”,将北宋文人的忧乐与当下诗人的沉吟折叠在一起,栏杆成为穿越时空的情感坐标;《岳飞的一片羽毛》里,“南宋绍兴五年的烽烟” 与 “现代性的杀戮” 在晚霞中 “痛饮江湖”,历史的暴力与生态的危机在 “羽毛的轻” 与 “铁枷的重” 之间形成张力;《废弃的小火轮》静卧 “辛亥年间干涸已久的滩涂”,却能在 “漏风的驾驶舱” 里 “复活困守的航程”,物理时间的停滞与精神时间的流动构成悖论式的时空景观。
最具哲学深度的时空折叠出现在《洞庭龙宫遐想》中:“溺水的最后时刻,我听见 / 有人提到了我的名字 / 就像有人在 ICU 里叫我”,将屈子投江的古老神话与现代医疗场景并置,“龙宫” 既是神话空间,也是重症监护室的隐喻,传统与现代、死亡与重生在 “水做的镜子” 中相互映照。这种时空折叠并非简单的古今对照,而是通过 “量子纠缠” 般的诗性逻辑,让不同时代的文明困境在湖水中形成共振,揭示人类面对自然、历史与自我的永恒困惑。

刘创的《大湖之境》以洞庭湖为精神实验室,完成了对诗歌本体的革命性探索。诗人以水体考古学的深度开掘,让器物成为文明记忆的活体载体;以生态书写的去人类中心化,赋予自然以悲剧性的主体地位;以楚文化基因的植物性转译,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激活;以时空折叠术,创造了多重历史平面并置的诗学奇观。当铁枷在湖底泛出 “慈悲的光”,当白鱀豚在茶馆里 “静坐成谜”,当编钟的兽纹跃入 “当下人间”,诗人不仅为洞庭湖书写了一部诗性的 “水文志”,更构建了一个照彻文明危机的精神坐标系。
在这个 “大湖重新觉醒” 的时代,《大湖之境》的独创性在于:它拒绝将湖泊简化为抒情的背景或文化的符号,而是将其升华为一个容纳历史、自然与人类的复杂生态系统。诗人以水为笔,在 “千重水” 的褶皱中书写文明的沧桑与希望,让每一滴湖水都成为折射人性光辉与阴影的棱镜。正如《湖之语》中所言:“放生的野鹳,消隐于沧浪 / 所有被大水孕育之物 / 终将,归还最初的苍茫”—— 这种对生命本源的敬畏与对文明出路的探寻,正是这部诗集给予当代诗坛的启示:在技术理性肆虐的今天,唯有重返大湖般的包容性智慧,才能在 “水穷处” 遇见精神的新岸。
(周爱勇,文学博士,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编:王相辉
一审:张颖琳
二审:徐典波
三审:姜鸿丽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