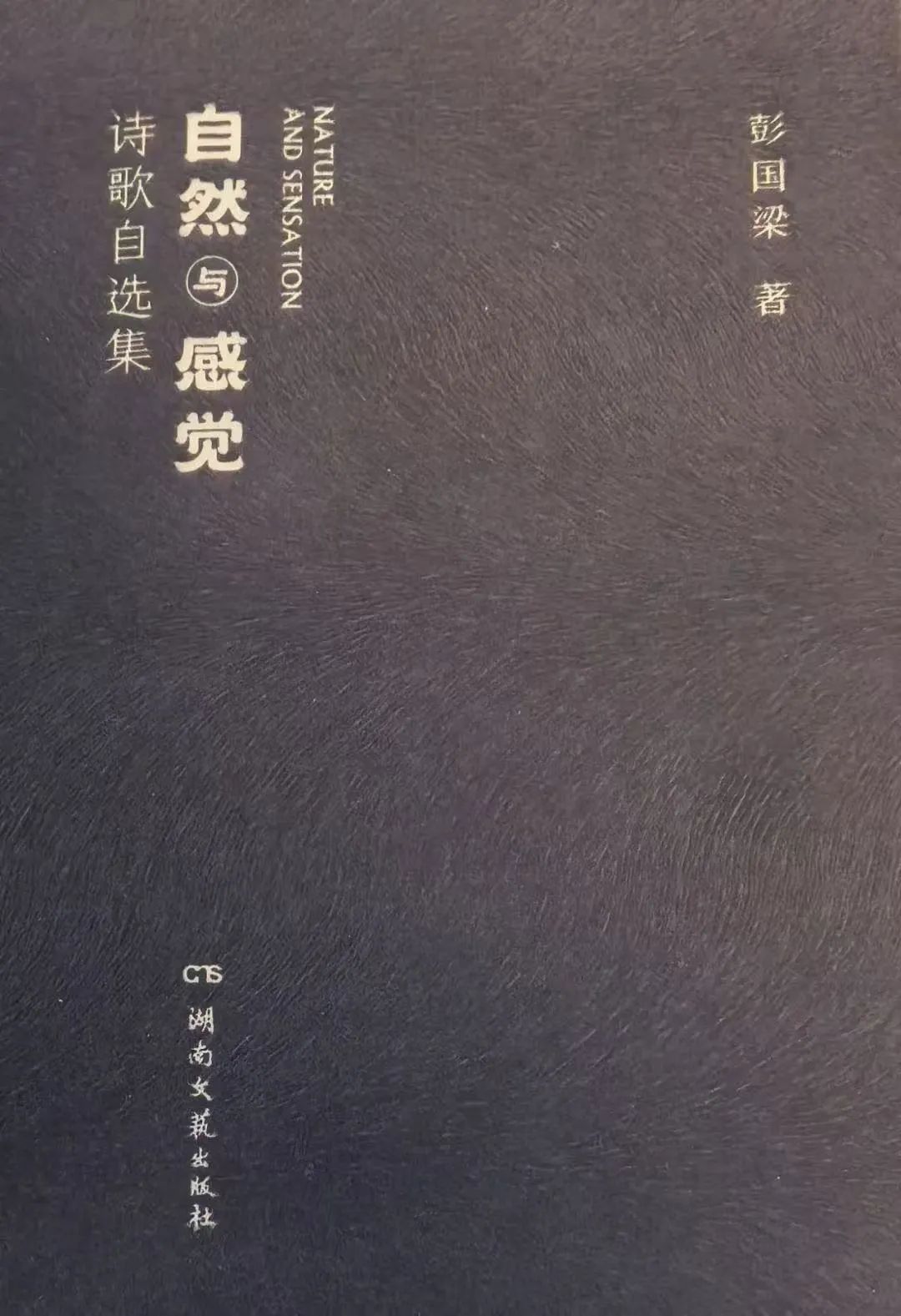
明净诗语中的乡土精神与生命直觉——评彭国梁诗歌自选集《自然与感觉》
文 | 施俊杰
在当下诗坛陷入“词语狂欢”与“意义空壳”的双重困境时,长沙新乡土派诗人彭国梁的诗作如同一股清流,始终扎根于湖湘大地的泥土与血脉。当众多诗人沉迷于拆解修辞、玩弄玄虚,将诗歌变成智力游戏的碎片时,彭国梁却以近乎固执的坚守,在自然意象中植入生命体温,在乡土记忆里发掘文化基因。这种创作姿态不仅构建了独属于他的精神家园,更在诗坛乱象中彰显出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
彭国梁诗歌中的自然意象绝非简单的景物堆砌,而是与生命呼吸共振的精神载体。在《残荷》里,他将枯萎的荷叶与衰败的莲茎,转化为历史记忆与个人情思交织的载体。残破的莲叶布满了沧桑纹路,却还在努力做年轻的摆动,即便老了也能沐浴年轻的风。自然物象与人文感悟在诗中达成亲切的共振。这种表达,与当下部分诗人笔下“无根的意象”截然不同——很多作品中的意象仅是美学符号的堆砌,剥离了生长环境与生命历程,沦为空洞的道具,失去了与土地和时光的血脉联结。
彭国梁始终让自然扎根于具体的时空,在《走一回湘西》中,湘西陌生农户的少女、掉进沱江的鞋子、大山腹部的隧道都成为诗歌的血肉,这种将地域文化与自然意象深度融合的写法,赋予诗句沉甸甸的历史感与生命张力。这种意象的厚重感,恰是当下轻飘的诗歌写作最匮乏的品质。
在生命直觉的表达上,彭国梁展现出拒绝矫饰的本真力量。他的诗句常常带着泥土的腥气与汗水的咸味,如《燃烧的稻草堆》中“野玫瑰在田埂上/鞠躬/无须回忆/漫长而短暂的一生/擦火柴的一瞬/尸体就开始化成热量”,作品以极具张力的意象,将生命的脆弱与炽热凝缩于瞬间。野玫瑰的鞠躬姿态,恰似向土地作最后的致意,而“擦火柴”的动作则成为生死界限的开关,当稻草堆燃起,逝去的躯体转化为温暖的能量,隐喻着生命以另一种形态存续,在灰烬中完成对永恒的叩问。这种对生命的感知不依赖哲学概念的加持,而是源自对农耕生活最直接的体验。反观当下诗坛,许多作品将生命体验异化为符号的拼贴,用“存在”“解构”等术语包裹着苍白的情绪,把本能的悸动过滤成冰冷的智性分析。当诗人在诗句中频繁出现诸如“不可知的深渊”“时光的裂隙”等抽象词汇时,恰恰暴露了他们对真实生命的疏离。彭国梁则始终站在土地上感受生命的脉动,他写《老猎人与狗》时写道:“猎狗是等老猎人睡了之后/从墙角那个窝里爬出来的/它知道马上要死了/它死也要爬到山顶上去/再回头望一眼爬过来的路”,这种从日常细节中提炼的生命直觉,比任何玄奥的理论都更接近诗歌的本质。
乡土精神在彭国梁的诗歌中,呈现为动态的文化传承而非静态的怀旧。他笔下的乡土不是被现代化进程抛弃的标本,而是始终在时代浪潮中保持生命力的有机体。在《一群绵羊走过街头》中,他写道:阴沟加紧覆盖/车祸不断消失/坚持/穿过这座城市/牧羊人吹着口哨/绵羊乖乖/步调一致。诗人将荒诞的都市图景与羊群的顺从形成张力,在矛盾的意象碰撞里,勾勒出现代人集体无意识的生存困境。这种书写超越了简单的田园牧歌式咏叹,既正视乡土在时代变迁中的阵痛,又坚信传统文化基因的顽强生命力。这种辩证的乡土观,与当下两种极端的写作倾向形成对照:一类诗人将乡土描绘成世外桃源,用滤镜式的书写回避现实矛盾,沦为廉价的乡愁贩卖者;另一类则以批判为名,将乡土妖魔化为愚昧的渊薮,在解构中消解了文化根系。彭国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正视乡土的斑驳与裂痕时,始终守护着其中流淌的文化血脉。这种有温度的批判与有深度的眷恋,让他的乡土书写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
湖湘文化的精神基因,为彭国梁的诗歌注入了刚柔相济的独特气质。楚文化中“浪漫奇诡”与“经世致用”的双重品格,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完美融合,将湖湘文化中“硬气”与“柔情”的两面性勾勒得淋漓尽致。这种文化浸润不是刻意的符号拼贴,而是深入骨髓的精神投射。当下诗坛不少地域写作陷入“符号堆砌”的误区,写江南必提乌篷船,写西北必写沙尘暴,地域文化沦为旅游手册式的标签。彭国梁则将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转化为诗歌的内在肌理,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自然流露,这种文化表达的深度,使得他的诗歌超越了地域界限,获得了普遍的精神共鸣。
在这个“人人皆可成诗人”却“好诗难觅”的时代,彭国梁的创作坚守着诗歌最本真的使命——用语言连接大地与灵魂。当众多诗人在语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将诗歌变成小众圈子的密码时,他始终保持着与土地、与生活、与读者的真诚对话。他的诗歌证明:真正的诗意不在云端的玄想里,而在田埂上的脚印中;不在晦涩的术语里,而在母亲唤归的乡音中。这种坚守或许不够“先锋”,却为在乱象中挣扎的诗坛,提供了一个回归本源的精神坐标——诗歌本来就应该是有根的植物,而不是塑料花。
责编:周听听
一审:周听听
二审:蒋茜
三审:周韬
来源:湖南文联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