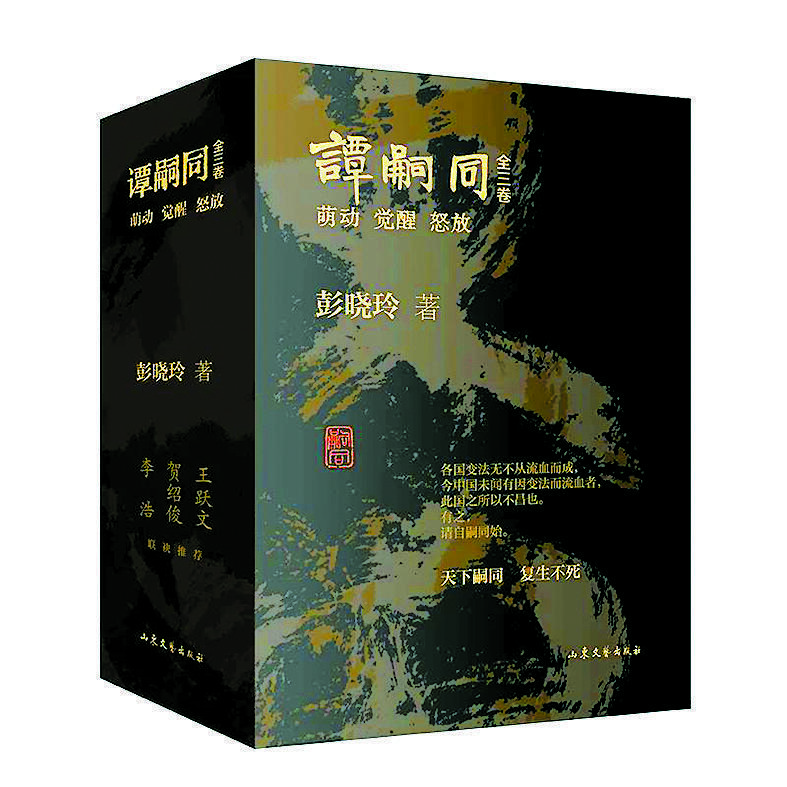
文/奉荣梅
从创作历史文化散文《寻访谭嗣同》,到出版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再到创作《拨剑欲高歌——谭嗣同传》,彭晓玲花了十年时间。我见证了她最初萌生对谭嗣同三十三岁人生的研读、创作计划的全过程,感佩她沿着谭嗣同仗剑天涯四处漫游遗踪,搜寻、发现、沉淀,与谭嗣同的精神成长共鸣的勤勉、执著。她通过阅读与行走,接通了一个更广袤的物质视野,开拓了一个更宽阔的灵魂视野,创作的长篇小说《谭嗣同》直指十九世纪末期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的忧患与关怀,她的书写超越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具有很强的审美意识与文学价值。
阅读《谭嗣同》,需要沉心静气,近百万字篇幅,有《萌动》《觉醒》《怒放》三卷,集中笔力描叙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志士谭嗣同短暂人生中最后七年的人生际遇,也对应着谭嗣同的维新变革思想从萌生到成熟、行动的三个阶段。彭晓玲不拘泥于历史小说的封闭守旧,围绕谭嗣同的七年间行踪变换,巧妙地将众多人物引领出场,叙事细密,以诸多场景、事件、对话和细节来结构整部小说,将笔触直接指向晚清动荡时代的人情世态,挖掘人物纷繁的内心世界。透过她笔下人物的命运,便可窥探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谭嗣同与众多官绅与士人的个体命运与社会动向、国家命途的关系。
一
彭晓玲说,她是在先贤谭嗣同卓绝的精神气质的感召下,来追溯一百二十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革新。她在自我的生命体验与渴望中创作,将自己的个体生命体验与丰富的审美情感融入人物命运之中,并进行艺术的传递与审美的开拓,厘清了谭嗣同的精神发展维度与精神路向。
谭嗣同是在其生命意识的寻找与建构中,在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种种意识有关的中西观念对冲和作用下,不断地走向更为内在的质询和拷问,维新变革意识的彻底觉醒,推动自己的外向性建设。谭嗣同少年即突遭慈母、兄姐同时病亡的打击,卢氏姨娘心计颇深,多方刁难他们兄弟,官僚父亲谭继洵严肃守成,父子诸多隔膜,家庭矛盾重重;青年数次科考落榜,前途渺茫;国家积贫积弱,在中日甲午战争落败,被迫割地赔款,清廷朝政腐败。
小说开头,就交织着谭家的三重悲喜,选取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春为切入点。这一年是谭家几件大事交织的重要年份,一是谭嗣同最亲密的同胞二哥谭嗣襄在台湾病故,他从上海扶兄灵柩回浏阳归葬;二是结婚数年后,谭嗣同夫人李闰终于生下儿子兰生;三是父亲谭继洵由甘肃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抚,成为一品封疆大吏。此后他往返武汉、浏阳,协助父亲管理家庭事务与公务,同时备考科举。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三十岁的谭嗣同,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浏阳组织算学社,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5月,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千余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谭嗣同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专心西学,并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次年2月入京到吏部候补知府报到期间,他结交了梁启超、吴樵、翁同龢等人。1896年7月,谭嗣同奉父命赴任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任总教习,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创建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旧政,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至8月,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
小说以时间为线索,截取谭嗣同人生思想走向成熟的最后七年,他最终突破八股科举的桎梏、家庭的阻隔,投入到维新变革的时代大潮与火热的湖南维新运动之中。
二
历史小说以史为纲,以史为本。小说《谭嗣同》通过对谭嗣同所处晚清历史变革的时代风云的叙述,展示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到戊戌变法之前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人际关系和历史趋向,再现谭嗣同以及众多历史人物典型性格和典型形象。
七年间,谭嗣同的足迹涉及湖南浏阳、长沙、武汉、北京、上海、南京等。先后出场的人物,既有他故乡的老师欧阳中鹄、涂先启和同窗挚友唐才常、贝允昕、涂儒翯、师中吉、余昭常、刘善涵、李昌洵等,真实姓名的历史人物就有几十人;他在武汉以理家兼巡抚父亲幕僚身份结识的政界人物,张之洞、王之春、陈宝箴、陈三立、蔡锡勇、杨锐、邹代钧、易顺鼎、梁鼎芬、程颂万、饶炳勋等,还结识了汉口著名传教士马尚德医生、杨格非博士、驻汉口英国领事贾礼士等各界人士;在北京、上海、南京,他又先后交结参与“公车上书”的四川人吴樵父子、曾国藩曾孙曾广钧、中西学贯通的夏曾佑、梁启超、汪大燮等志同道合维新人士;在江苏候补,与上海、南京的维新变法的“海内奇才”宋恕,汪康年等《时务新报》人员,洋务运动主将盛宣怀,英国人傅兰雅等交往频频;回到长沙协助陈宝箴进行维新变革,又与江标、黄遵宪、熊希龄、皮锡瑞等政界贤达、学子有交集。
晚清时代,中国新知识群体出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热潮,伴随着西学东渐,知识分子选择了科学主义作为富国强民的途径。身处西学东渐的时代,内外交困之中,聪慧博学的谭嗣同,极力探索维新变法之道,从挣脱自身命运的羁绊,到为国家振兴为民族救亡,一路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
个体的觉醒与独立,不仅是一个人外在的革命和新变,而且是一种内在的重铸和再建。当国家处于危亡之际,谭嗣同摆脱了个人命运的忧伤,心忧国家民族命途,并且致力唤醒民众的经世致用的现代教育、各种实业上来。
三
孤独注定是觉醒者的命运,先锋者的使命是照亮生活世界,小说家的主体力量体现在理想的道德勇气和超越精神,笔墨是呈现人物以及所处时代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谭嗣同》中多处呈现了人物性格与命运的隐喻与暗示。
小说以“葬兄”为开端,营造一种阴郁和压抑的艺术世界,让人感受到谭嗣同生存空间的霉腐与窒息,这种沉郁悲抑的氛围暗示人物最后的悲剧命运。谭嗣同从来对鬼神谶纬等一套不太相信,但是冥冥之中,有一些命运的暗示。但谭嗣同有向死而生的使命感,他勇猛精进地学习,打通诸子百家和东西方宗教,撰写了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仁学》。
西力东侵,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这个急遽变化的动因,既有自身内部的调整和变革的内在诉求外,更主要是在外力的冲击下出现的变化。谭嗣同早年在浏阳名儒欧阳中鹄、涂先启、刘人熙的指导下,研读完《船山遗书》,而船山学说宗旨为阐述人应与时同行。迫于父命,谭嗣同长年来不得不奔波于甘肃、湖南及京城三地应试,就在多次南来北往跋涉奔波、风餐露宿的日子里,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的贫弱、官场的腐败和百姓的艰苦,萌生了强烈的济世救民理想。1895年中日战争清朝溃败,谭嗣同更坚定“国难当头,更要与天争胜,要图强保种,朝廷就得卧薪尝胆地破除因循守旧之风,改弦易辙地进行变法!”“落后就要挨打。我大清国再不变法再不自强,就自取灭亡。”大胆提出变法迫在眉睫,且主张筹集变法资金以广开学校,大开议院,操练海军,兴办商务,开矿脱贫。与几位同好回浏阳办新式学堂算学社,培养新型人才。
英国人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使得谭嗣同“仿佛茫茫黑暗里,前方有了隐约的光亮”,他开始认真系统地阅读《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代数术》《声学》《电学》等书,边读边认真地写读后感想。找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尚德医生探讨阅读西学的困惑,还结识了汉口著名传教士杨格非博士、驻汉口英国领事贾礼士。他与张之洞倾心畅谈,融汇中西思想,“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因循守旧,而不知与时同行,更不知变革维新。”可谭嗣同失望地发现:张之洞虽然有兴办汉阳铁厂、两湖书院等引领风尚的举措,但毕竟还只是承袭洋务运动那一套,不敢轻言变革维新,说到底还是因循守旧一辈罢了,只是比他父亲略微超前而已。
四
历史小说创作,要求符合历史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方面的真实。写作历史小说,既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又要有卓特的历史眼光。彭晓玲在创作的过程中,注重对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外部世界的关注,使小说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时代性。她同时还注意对历史人物个人内心世界的开掘,从多重叙事中感受到作者向人物心灵“内宇宙”挺进的叙述冲动,聚焦于主人公隐秘的精神空间,揭示了谭嗣同在不同境遇下内心深层的撕裂与挣扎。
面对封建家长作风的父亲,卢氏姨娘的多方刁难,五次参加科举考试,谭嗣同有深重的痛苦,多重的内心纠结,深深的无力感。他想冲脱父亲的压制与卢氏刁难,摆脱科举的桎梏,可面对强势的父亲总是铩羽而归。他与父亲有根本的思想冲突。父亲谭继洵敬守为官本分,勤于政事,在父亲看来,走科举正途,中举人中进士,才是孝顺才是光宗耀祖。而在谭嗣同看来,如何学习实用之学,造出坚船利炮,国家才能不断强大,才能不受欺。家国情怀深重的谭嗣同,心中的忧虑是双重的、分阶段的。在张之洞受谭继洵之托,与谭嗣同谈话,劝他速去江苏候补,谭嗣同就有明显的表露:“我心中是有忧虑,过去是对身世的担忧,自《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确是对国家对百姓深切的忧虑。”
在描写张之洞、谭继洵等历史人物时,小说注重揭示人物的多重性格内涵,同时表现人物思想的变化,心理细节描述性文字教多,细腻、客观,很好地再现人物的复杂性格、思想,塑造了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
小说除了叙述历史真实背景外,也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有不少突出人物特点、呈现人物性格变化的生动细节,同时掺入了彭晓玲真实的思考与感受。
小说描述了谭嗣同七年的丰富多变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构建了他维新变革思想的萌动、觉醒到怒放的发展脉络,寻找和建立民族精神的根源,构筑救亡图强、民族精神觉醒的精神谱系。这种觉醒由内而外,又自外而内。
五
历史小说中的虚构和想象必须受历史事实的制约,历史事件、历史环境、历史人物以及时间、地点都必须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在符合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可以融入一定的想象和虚构,准确、逼真的小说细节。比如,小说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而虚构了武汉少女包世贞、少年罗成等人物;且从生活起居、风俗习惯到语言方式、行为举止,一切看似细微末节的生活小事,真实自然。
在塑造人物、构思情节、渲染气氛、描绘环境的时候,彭晓玲调动和借鉴小说样式的一切写作手法,融入自己鲜明强烈的感情。小说从头至尾都贯穿着诸多关于时局时弊、维新变法的争论交锋,人物对话与心理描写,契合晚清的小说语言风格。小说中不乏精彩的故事内核,但彭晓玲的意图并不在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是让小说中人物的心灵内面得以凸显。绵密的叙述,写作呈现出愈加宽阔、丰饶的状态。小说选取谭嗣同北上参与变革这段时代背景,呈现人物思想性格的进一步发展,表现维新志士的光辉品质和时代意义,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艺术概括和丰富的艺术想象。
小说背景不断变换,各地风土人精、名胜古迹穿插于文字之中,还有谭嗣同的数十首诗词对联,语言自然流畅、细腻,或烘托或伏笔,暗合人物性格与心理,事件的背景与推动发展。小说中有多处游览各地风景名胜的描述性段落,文人雅聚,诗酒唱酬,引用了谭嗣同与他人的诗句、唱词,全面呈现谭嗣同雅好交游的性格特征,也增添了可读性。“河流固无定,人亦困征鞍。残月照千古,客心终不寒。山行依督亢,天影接桑乾。为有皋鱼恨,重来泪欲弹。”“在嗣同眼中,京城没有什么改变,仍一如既往地喧闹,永远一派虚假的繁荣。在腐朽中有着茁壮,在茁壮中透着腐朽。它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就像一只僵而不死的百足虫一样。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幻象,光怪陆离,深不可测。”
小说结尾,在谭嗣同应光绪皇帝之招进京,戛然而止又意味深长。矛盾冲突的高峰和结局“戊戌变法”结局家喻户晓,似乎意犹未尽,但余音袅袅,想象的空间无限。
小说写的是活着的历史,要有细节,有温度,有血有肉,使得历史叙事变得饱满丰盈,既遵循人物历史的事实逻辑,又依据自身的艺术逻辑来书写历史的真实,重视人物心理、精神的情理逻辑。《谭嗣同》像历史生活的一面聚光镜,通过艺术的折光,把谭嗣同所处的那段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矛盾斗争和人们的感情情绪折射出来,通过谭嗣同与众多历史人物交集和历史事件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历史巨流的奔腾,让历史的后来者从这面聚光镜中去认识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
作者:奉荣梅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