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缘仁制礼”中的体用思想
王夫之以体用之辨来强调《礼记》和《周礼》《仪礼》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就最初创立的制度来说,《礼记》为体,《周礼》《仪礼》为用;就个体修行来说,《周礼》《仪礼》为体,《礼记》为用。三礼共同构成仁的体现,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君子之所以是君子的根本。王夫之认为礼是立人之本、修己治人之道、躬行之密用,他作《礼记章句》的目的在于“存先王之精意,徵诸实用,以俟后哲”,其中强调了他注重现实,提倡实践的观点。对于庄子所论述的坐忘顺序,忘仁义而后忘礼乐而后坐忘,王夫之认为与仁义相比,仁义更侧重于心性之体,礼乐更侧重于心性之用,如王夫之提出:“先言仁义,后言礼乐者,礼乐用也,犹可寓之庸也,仁义则成乎心而有是非,过而悔,当而自得,人之所自以为君子而成其小者也。”
在对礼学的注解中,王夫之也贯穿着“体用不二”的思想。而且常常“本”“体”互释。即本和体是同一物体,同时书中还贯穿着经与权、达与成、道与器等互为表里的概念。以下为简要分析。
《曲礼》篇内容详尽,无微不谨,此篇是下学先务,是君子反躬自省之辞。在这里他提出礼之“本”以正心修身、节情去私为要,主张存理遏欲。礼之“用”在于定亲疏、别同异、决嫌疑、明是非,他强调礼的大旨便在于本立而用行。王夫之提出“仁者,爱之体,义者心之制,礼以显其用,而道德仁义乃成乎事。”即王夫之提到的第一条阐释礼学的路向——缘仁制礼则仁体礼用。第二个路向主要体现在《四书训义》中:“夫真爱真敬者,人心恻怛自动之生理,则仁是矣。故礼乐皆仁之所生,而以昭著其中心之仁者也。仁以行礼,则礼以应其厚薄等差之情,而币玉衣裳皆效节于动止之际。”《檀弓》篇主要是记录孔子以后行礼的异同,王夫之主要研究其中所蕴含的“不易之理”和“精义之用”。对于礼的内容,王夫之指出,礼学是孔子折衷裁定周礼而定,杂含殷、周之礼。礼学有“经”、“权”的分辨,他提出“唯圣人而后可兴权,则下此者不可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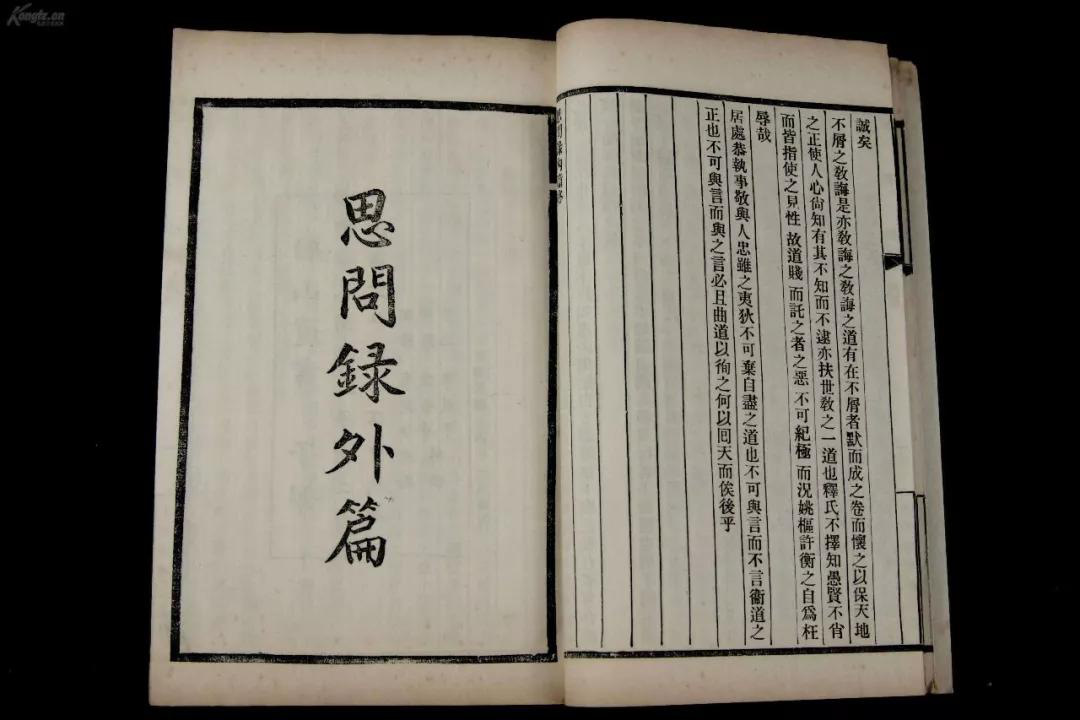
王夫之提出“运”即“载而行之”,《礼运》篇主要表明礼如何能周流天下而使万事各得其宜。他认为原因主要在于:“为二气五行三才之德所发挥以见诸事业,故洋溢周流于人情事理之间而莫不顺也。”他引用张载的观点再次强调了体用之辨:“礼运云者,语其达也,礼器云者,语其成也。达与成,体与用。合体与用,大人之事备矣。”《礼器》篇与《礼运》篇相互映照,礼器篇主要叙述了礼制的品节内容。王夫之认为礼运为“体”,礼器为“用”。他推崇张载的“礼器者藏诸身,用无不利,修性而非小成者与”,认为“运之者体也,而用行焉;成乎器者用也,而要以用其体”。
对于《孔子闲居》与《仲尼燕居》两篇,王夫之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仲尼燕居》篇论“用”之大,《孔子闲居》篇言“体”之微。继续论述体用之辨。《坊记》篇与《表记》篇相为表里,坊为末表为本。“坊者,治人之道。表者,修己之道。修己治人之实,礼而已矣。”他借此分析了性之所失,情欲之所发,而且还以《周易》里“遏恶扬善,顺天休民”来进行互释,同时与荀子的理论进行比较。提出《表记》:“以敬为本,以仁义为纲,修身以立民极之道尽矣。”《缁衣》篇被认为是《表记》的下篇,记录好恶言行的旨趣,其中好恶为仁之表现,“言行为义之实”。王夫之认为《坊记》与此三篇,本末相资,脉络相因。
王夫之 “仁以行礼”的体用思想
在《礼记章句》中王夫之特别强调了“用”的重要性,即他的崇实黜虚思想。王夫之的崇实黜虚,一方面是树立实的内涵,一方面是反对王学的空虚,反对玄想,反对释老的邪说淫词。如他多次借《礼记》反对王学之说,他在《大学》篇提出:“自姚江王氏者出而大学复乱,盖其学从入,以释氏不立文字之宗为虚妄悟入之本,故以章句八条目归重格物为非,而不知以格物为本者经也,非独传也,尤非独朱子之意也”他认为王阳明之说与郑玄之说不合,百年来学术道丧、世事纷乱都是宗王所致。王夫之批评王阳明把“亲民”解释为“如字”是释氏和墨学的余波,把“格”训“式”则是张九成和宗杲的邪说,此后有罗汝芳以“自谦”为“逊让”更是文义不通。王夫之提出:“夫道之必有序,学之必有渐,古今之不能违也。”对于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若废实学,崇空疏,蔑规矩,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则释氏之诞者固优为之,奚必假圣贤之经传以为盗竽乎?”

王夫之在《礼运》篇就孔子“叹鲁”提出,其原因在于当时鲁国徒有礼的文饰而失去了礼的实质。对于礼的简繁变化,他认为应该根据时俗而进行变化,三代以上民风淳朴,在上者可以无为而治,百姓礼节可以从简。三代以下淳朴民风不在,因此先王制礼作乐,使民复合于道。他主张礼治与时偕行,质文迁变,相因而立。对于其中提到理想社会:大同和小康。王夫之认为“大同”是同于礼,“小康”是作小安讲。王夫之在这篇借夫子之言而阐述礼不可僭之意,主张礼的文质如一。他认为君王以礼自正,同时也以礼正人,这样诸侯、大夫才能各得其正,不至于僭越失礼,最终达到政治而君安。王夫之因此得出政即是礼的结论:“礼所以治政;而有礼之政,政即礼也。故或言政,或言礼,其实一也。礼以自正而正人,则政治而君安,不待刑而自安。”百姓明白礼的法则能够自治,奉养服事无所不合于礼,这样便做到了“礼达分定”,礼才能够成为君王的“大柄”,即“秉礼以治人”“以礼治人情”,这样即便是派遣臣民去做危亡之事,他们也不会有畏惧之心。他主张做到齐于礼,而不必齐于刑。王夫之再次以体用本末相统一进行了总括:“天道人情虽无异致,而于天道之承徵礼之体,人情之治著礼之用,则本末功效之间亦已别矣。”
《内则》篇是门内之教,主要叙述德行,内容包括孝德、孝行、友行、顺行。王夫之认为这种孝友之德生于内心,能够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然而即便内心具备,如果不能施行于现实,也不能立道,内心最终也会逐步走向衰竭。倘若能够研习行礼,那么便能够在实施的过程中自然使内心充满。他还借此反对良知的淫邪之说,要求学者能够慎思明辨笃行,这样才是经说的正义。《玉藻》篇主要记载冠服、容貌称名之仪。王夫之认为“王者修明章服以为典礼之本”,可以从此篇中考辨而得知,对于继承三代礼法来说具有重大的补益。而且章服之礼也是人禽之别、上下之等、君臣之分、男女之嫌、君子野人之辩的关键,因为衣裳体现了乾坤的法像、人道的纪纲。王夫之生活的时代世降礼坏,他以此反对当时夷狄的寒毛暑裸的“便安”做法。对于《中庸》篇,王夫之认为非躬行心得不能获其指归,他反对明末后期的空谈心性、反于自得、淫于佛老之说。他提出“诚明相资以为体,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在《经解》篇,王夫之认为五经之教化民成俗,所归于礼。五经微言见之于理,礼则实行于事。所以他提出:“五经者礼之精意,而礼者五经之法象也。”如果不通五经的微言大义,不懂礼的实施,那么性情治乱之说很可能落为玄虚功利之学。
(路鹏飞,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责编:薛琳
一审:王智芳
二审:薛琳
三审:龚化
来源: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会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