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吴天宇
昨晚,乌鸦同学在群里发了一组照片,那是九三中文二班创办的《未名园》第五期手抄报,二十多年岁月的浸染,即便主人如何小心翼翼地珍藏,也泛漾出一色淡淡的微黄。既然是第五期,那么前四期想必是存在的,但我再也想不起来后面还办过几期,它是如何的诞生,又是怎样的消亡,已全然没有印象了。如果没有这一组图片,《未名园》其实在我的记忆里早已消逝了,连同远去了的模糊的青春。
但《未名园》是确乎存在的,我盯着手机里的照片,努力地回想着与此关联的残留的光影,似乎有着这样一幅画面闪现在眼前:在一个秋日的周末,我用三角尺在A3纸张上横七竖八地画下格子,笨拙地添置些不知所云的图案,然后一笔一划地抄写起同学们交上来的稿子。除此,已经不太好使的脑子里再也想不起别的东西。
用当下的眼光来看,《未名园》是那样的稚嫩。版面设计?估计七八岁的孩童都会翻出一双大大的白眼。字,似乎一大半都是我写的,看得出态度是认真的,抄写得很工整,但文字犹如死蛇挂树,了无生趣,遑论章法,这样的书写水平,居然敢担此重任,想必一是无知者无畏,二是那帮家伙也真的太懒了。
到了四十七八的年纪,许多东西也就变成了记忆和情怀。既是情怀,再粗鄙的东西也是可贵的。我斜靠在沙发上,摘下眼镜,用这两年老花得有些厉害的眼睛仔细地阅读《未名园》里的每一篇文章,不出所料,雪月风花,烟雨江南,多是些少年的新愁,如熟了五分的梅子、三分的枇杷。

有新愁的少年,遇上了歌唱的舞台,自然得横笛吹雨,拿云长啸。少年的心性,大多是不懂得谦逊的,幸得抄手之便,把自己的作品《雪》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就是应有之义了。健美的《山乡》,有一丝淡淡的乡愁。得山水灵气,和肖某人生下的女儿已经出落得盈盈动人了。加生兄一别之后,音书两违,再读其文字,恍惚间在他那张木然安静的脸上,看到了一丝难以察觉的骚气。在湘大读书,周静自然是女地主,很有担当地向我们推荐起湘潭人情有独钟的槟榔,不知如今身在南国的你,是否还会怀念起家乡的味道?凌飞是我们班年纪最大的兄长,阿P或许是他自己的故事吧,大出我们的年纪,多出我们的阅历,使他的文字里有更多的人间烟火气。在我的印象里,刘莉没有很多的言语,皮肤白晰的她,总是看着我们安安静静地笑着,只有这样的女孩,才会在《独处》里的思绪,我猜想,在岁月里,她应该是越发的安静澹然了。一语成真,把“献”字拆成“南犬”的班头,已在南方生活很多年了,我去过广州,被老朱、凌飞他们灌得人事不知,但没有见到老范,人如参商,天各一方的我们,见与不见,皆在缘分了。
KARI在群里发问:“白宫”是谁?这也是我的疑惑。白宫同志在《未名园》里霸占了很大的篇幅,有酸得掉牙的《破镜》,有装模作样的《专家访谈》,更有高深莫测的《风景》随感。指点江山,吞吐文章,如此人物,猜错便成亵渎。幸而不久,老朱同志自报番号,终不致成为迷案。
在我记忆里,老朱是九三中文二班较为活跃的文艺青年之一,但似乎另有三五人亦激情似火,骚气冲天,奇怪的是在这期的《未名园》里未曾见到,可以肯定的是,在别的几期里,定能读到他们的文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妹对现代诗的热爱达到了魔怔的程度,课余(或许包括上课)不是在读诗,便是在写诗。在他浩大的创作中,我有幸看过几首,感受有三:一、看得懂的文字都不是诗人写的;二、诗人是不受语法限制的;三、诗人的文字是让你感到晕眩的。阿妹最短也是最好懂的一首诗是写在一张便条上的,好的诗歌总是让人难以忘怀,我至今还记得,那首诗只有两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爱你是我的礼物!乘着月色,我和翟光景把写着诗歌的便条交到了一个女孩的手上。半小时之后,女孩登门:“谢军民,你出来一下”。之后,便是一段需要用无数文字和诗歌来阐述的悲欢离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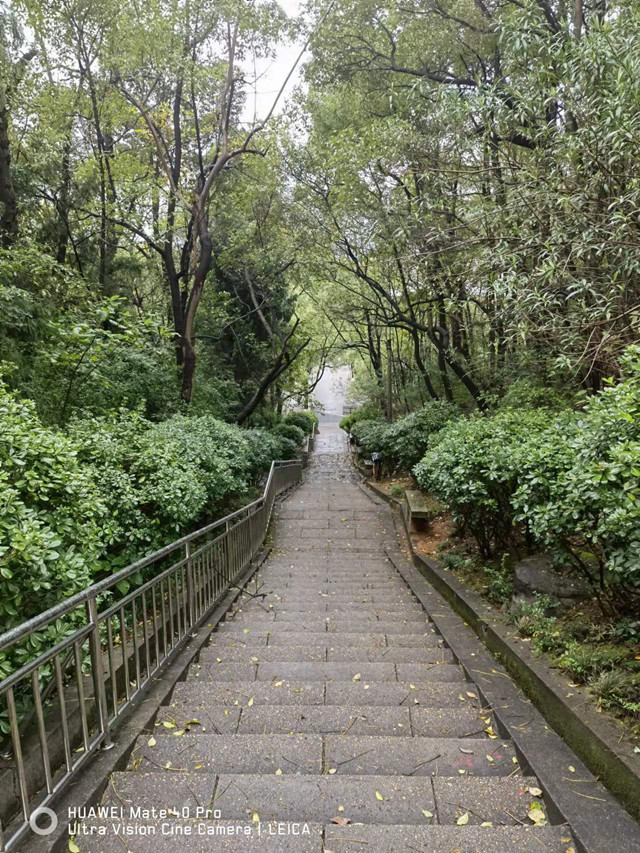
最近,徐荣创作的很多作品陆续上传到群里,在我的固有的思维里,徐荣在大学里大抵干了两件事,一是恋爱,一是当学生会主席,妥妥的实干家,和文艺倒不怎么沾边。不曾想,年齿愈长,风骚愈盛,从前的点点滴滴被他打捞起,娓娓道来,几无修饰,如一条平缓的河流,载着你泛荡向过往,他在船尾撑着舟,绝无多余的话语,沿途的风景随你自行感悟。经过岁月洗涤的眼眸,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山水就在那里,不用刻意地描绘。
说到文艺,万立刚是绕不过的,似乎班里一切与文艺有关的活动,都是他发起的。大三的时候,还创办了一个文学社(名字居然都忘记)。记得熄灯之后,10个人点着蜡烛审议着创社宣言和章程,规划着文学社宏伟的未来,如何组稿、编辑、发行,如何发展社员,如何组织诗会活动,在激烈的讨论中逐渐形成文字,万立刚当然的成为了文学社的社长,扛起了湘潭大学文艺中兴的大旗。依稀的记得,文学社在阶梯教室里举办了轰轰烈烈的创社典礼,陆续编印了几期刊物,也举办了几次诗会活动,最多的时候发展到一两百社员。我老婆说,当初认识我的时候,就是到阶梯教室参加文学社活动,我坐在台上,戴着眼镜,很有文艺青年范。然,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不到半年的时间,文学社悄然地沉寂下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只在宁乡见过万立刚一次,口中多是生活和工作里的琐事,绝无文艺之雅趣,也不知他当初热烈的梦想是否还在延续。
老徐在群里感慨:当年办报纸的只剩下乌鸦还在坚持了!是啊,《未名园》也许只有她那里还有几张留存吧,否则,曾经寄托着我们文艺梦想的《未名园》早就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了。如今的我们,除了乌鸦、老徐这两个办报人还在坚持写点东西外,距离文学已经越来越远了,远去的是青春,还有青春里燥动不安的追寻。
愿岁月静好,愿多年以后,我们还记得《未名园》里的文字。
责编:肖畅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