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与时代的共振
作者丨马笑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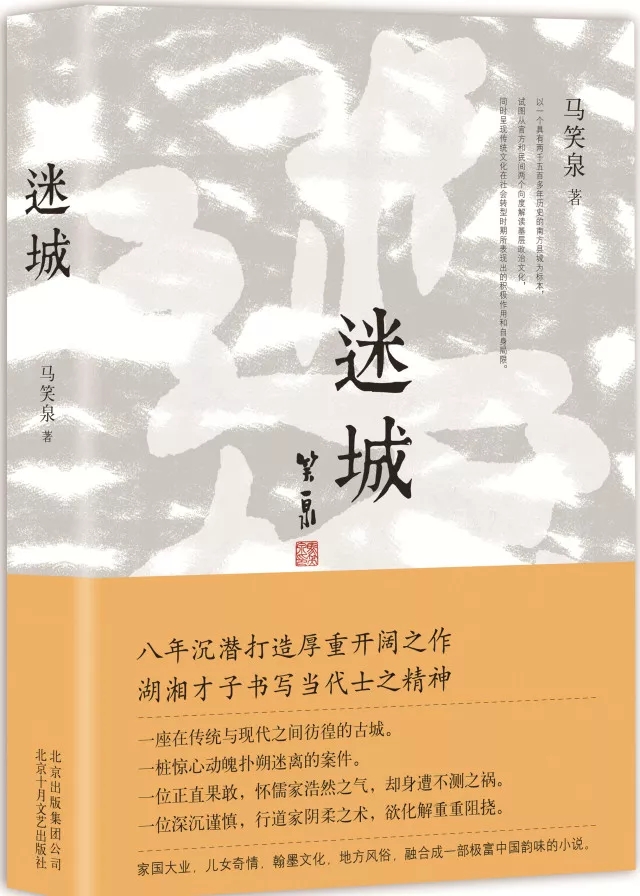
我出生和成长于南方县城,毕业后又先后在与家乡邻近的两个县城中工作了八年。作为一部以县城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迷城》当然有它的现实基座,或者如你所言,有具体指向。但小说是对现实的想象性重铸,一旦完成,它就是另一座城,一座在文本中自在自足的城。
宿命云云,是从结果回溯到起因而得到的一种切身感受。我40岁前的大部分小说皆是以县城为空间背景,这是与我的出生和成长息息相关的空间。如果我出生、成长于茶峒或者纽约,那我的写作就将是另一番面貌。这是个人难以选择的,所以我把这视为一种宿命。既是宿命,则将身心沉入其中,仔细体察,从容书写,以尽此命。
从《愤怒青年》到《银行档案》再到《迷城》,县城的精神气质和县城人的精神处境始终是我着墨最多、用力最深之处。如果能够一言以蔽之,那我也就不用写这么多字了。最深的体验往往最难言说清晰。而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本能地拒绝清晰,特别是那种简单化、概念化的清晰,就是为了维护这份体验的整全性。县城是都市和农村的连接地带,那么,它也是边界模糊之地、彷徨不定之地、含混复杂之地、冲锋和撤退之地。这种种状态都渗透、作用于县城人的精神面貌。而县城青年是县城人中最敏感、行动力最旺盛的一群,他们的处境和行为无疑能最集中、最鲜明地表现出这些状态。我所能做的就是用形象来呈现,而非理论上的梳理和概括。当然,理论上的梳理和概括也很重要,但那是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工作。最打动我的,也是让我乐此不疲的,就是敞开心怀,让这些细节一点一滴地渗透进来,最终与这座城血肉融合这样一个漫长而细微的过程。
我通过大量的细节体认获得了这座城的神韵之后,就要把现实中那些太具体的东西忘掉,以便在艺术世界中进行自由创造。而那些细节其实并没有真的忘掉,它们只不过是通过想象在文本中进行了转化和重组,最终传达出这座城的神韵。
从时间上来说,《迷城》的创作和完成正好处于我从青年步入中年这样一个阶段。从创作心态和作品所呈现的气质来说,青年时期的劲气奔涌转化为中年时期的舒缓深沉,确实是一个告别式的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端。“青年写作”和“中年写作”不仅是一个生理年龄的问题,更是一个心理年龄的问题。有到老仍是“青年写作”者,也有步入创作不久就进入“中年写作”者。大体而言,“青年写作”往往在某种强烈情绪的驱动下喷涌而出,呈现一种飞扬恣肆之态,更多地仰仗先天元气,而“中年写作”的节奏会慢下来,趋于舒缓、开阔、深沉,还包含了审慎和犹疑,后天的经验和思考的比重会逐步增加。二者皆能出佳作,只是面貌有异,气质有别。
对我而言,写作的驱动力以前是内心的呼唤,现在和此后是内心与时代的共振。其实之前也是出于自我与外在的共振,只是那时认为存在一个纯粹的、不受外界影响的内心世界。其实从人出生那刻起,就无时无刻不处在与外界的共振中。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世界即我,我即世界,何曾须臾分离。
(原载2017年11月13日《文艺报》)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文艺报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