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本来面目
作者丨卓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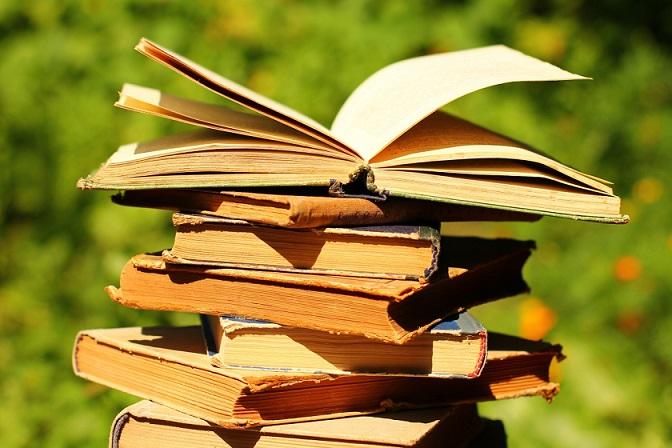
谁也抵挡不住这样一个事实:文学的圣殿已经在经济洪流中倾圮,文学行业被底层化,边缘化。如果一个人要标榜自己是文学青年是需要勇气的,“文艺青年”常常是被调侃的对象。青年们大都把目光投向了别处,有成就的作家也转行的转行,隐退的隐退,只有少数还在顽强地坚守。文学杂志发行量锐减。曾经红火的报纸副刊改版成为娱乐+生活+休闲,不再有文学园地。出版社不再热心于文学原创和纯文学,改弦更张搞心灵鸡汤、名人传记、厚黑学、成功学。内外合围,赶尽杀绝,真是哀鸿遍野,不忍直视。大概在六七年前,我们文学所到各市州文联作协进行调研,常常要遭遇一些尴尬,越是经济情况好的地区越是找不到作家来开座谈会,主席们碍于面子东拼西凑,勉强凑到一拨人,所谈内容无非是经费紧张,生计艰难。至于文学本身,拿不出几个像样的东西。一个强烈的感受,大家都不再爱文学,这种情形下,谁还有心思谈学术?方法题材、现象思潮,见鬼去吧,腰包鼓胀才是硬道理!我们都从十分艰难境况下走过来,一份大家谈起来都躲躲闪闪的事业,你还能怎样?作为省级的文学研究机构,也差点被撤销或者合并。全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省级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更名为文化所或者合并为文史所。这几年情况好转,有些地方又开始恢复文学所的名称。熬过了惨淡的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文学的种子又开始滋滋地冒芽,竟有一年比一年好的势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2003年开始编写文学蓝皮书(原名中国文情报告,白烨主编)。每年出版和发表的文学作品统计出来照样是一个吓人的数字,文学似乎依然保持着繁荣景象。一个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说实在的,每天不干别的事,光看作品——我指的是质量还过得去的作品,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文学创作从来是个体智思行为,不太需要同伙,也用不着帮手,更不需要昂贵复杂的设备,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是在几米见方的斗室里创作出来的,大脑+纸笔,现在也就是一台电脑,有没有上网的功能都不重要。同时文学创作又是极其社会化的一个活动,作家的知识结构、气质气韵、价值观念、心理构成、文化选择、审美倾向、艺术感知等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因此它必然还存在着团体效应。那么谈一个地方的作家大概一定要涉及到当地文化,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作家、作品、读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联?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全球视野,多元文化板块的漂移、重组、生成,人的流动迁徙频率加大,社会制度变革下原有的阶层固化结构被打破,这种关联度更加处在弹跳、模糊之中,“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难度加大。文化类型、族群结构、人文地理的时空流转对作家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个人感知来自社会,表现对象以人为主体。“原始之力”是创作的根本冲动,“教养”(或“理性”)则让这股力量成型并上升为艺术,这两样东西在湖湘文化中恰好是两块基石。我曾经在《原道精神与巫诗传统对当代湖南作家的影响》一文中清理了一下文化传统与作家的关系。我们知道,历代学者都谈到了湖南民间“信巫鬼,重淫祀”的风俗,巫鬼、祭祀包含奇异诡谲的浪漫主义成分,湘地文人的内感知及“原始之力”的生命冲动和艺术形式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在湖湘文化中与浪漫主义相对应的还有一种理性传统,或者说最后变成了一种理学精神。翻开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这两大传统都有最具影响力的本土代表人物。理学精神经过后代学人的经营和改造,逐渐变成“经世致用”。“经世致用”讲实事求是、践履、不蹈虚。这种传统直接催生出晚清及民国后灿若星辰的湖南人才群。这两种资源还不能截然分开,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作家动笔之前首先要解决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认识人的本质和结构,以及人与客观实在的联系,这个问题看起来大而空,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必然有一个落脚点。“原始之力”、“内感知”都强调人向内心探索的功能,理学精神也讲“反求诸己”,扩充自己内心固有的良知良能。二者其实最后都走到了一个方向。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一统天下的时代,湖南作家在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的同时,还意识到“情”与“理”其实就是水与流的关系,虽然大多数人不一定有理论自觉。在文学创作中两股力量并不一定要对等均衡,美学性趋向和思想性趋向并不是对立的,偏“情”的时候会更注重艺术,偏“理”的时候会更注重思想。沈从文、黄永玉、孙健忠以及湘西作家群,湘西神秘文化中巫诗传统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倾向于前者。周立波、丁玲、古华、莫应丰、唐浩明、王跃文、阎真等作家倾向不蹈虚的现实主义传统,跟他们教育背景和生活经验有关。韩少功、残雪、昌耀、张枣他们是兼而有之。无论是偏向艺术还是注重思想,文学在意识形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湖南作家的这种独特的诗学特征使得他们异常抢眼,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湖南作家为中国文学的“内部升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时在政治体制与文化政策的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中国作家开始对艺术本体有一种自觉性,湖南作家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头,甚至让人感觉不太费力的自然进入文学自觉状态,他们整体性地意识到要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一次深入挖掘,对传统文化资料重新认识和整合,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把握和理解本民族的基本情感。1985年韩少功在杭州西湖会议上一篇《文学的“根”》擎起“寻根文学”的大旗,这篇被认为纲领性的论文,以一个大的观察视角,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融合的范式转变,他的《爸爸爸》与寻根文学理论相互印证,适时登场,惊世骇俗。还有沈从文的文学价值的被重新评价,周立波、丁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史意义,古华、莫应丰的茅盾文学奖,残雪的实验文学,彭燕郊的“七月派”等。紧随其后的九十年代,唐浩明的历史小说,王跃文、阎真的官场小说,都是当代中国文坛的大事件。湖南作家除了文学现象和文学大事件方面的影响以外,还有一大群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列出来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未央、孙健忠、谭谈、张扬、谢璞、刘勇、于沙、叶蔚林、彭见明、何立伟、水运宪、彭见明、聂鑫森、叶梦、贺晓彤、李元洛、凌宇、任光椿、陈健秋、蒋子丹、弘征、石太瑞、萧育轩、王以平、吴雪恼、崔合美、彭学明、谭仲池、梁瑞郴、蔡测海、姜贻斌、汤素兰、欧阳友权、邓宏顺、陶少鸿、莫傲、刘舰平、匡国泰等,关于“文学湘军”的辉煌回顾起来是一篇大文章,以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为起点(当时六部获奖作品湖南占两部),2012年湖南文学界举办了“文学湘军三十年”的活动,相关学术文章和新闻报道对三十年来的作家和创作情况作了一个盘底。这三十年的头十几年,无论是作品还是人才,都可以用高质量和高密度来形容。
这几年,湖南文学活跃起来,无论是创作队伍还是刊物、网站,都显现出兴旺的势头。湖南文学的这种新气象与省委省政府对文学的重视和扶持分不开,与省作协强有力的领导分不开。有了财力上的保障,省作家协会就能办成一件件大事,作家的成果也得以摆在显眼的位置,市场和读者对文学的关注度在大幅度提高。在文学创作方面,长篇小说创作获得了大面积丰收,涌现出王跃文的《爱历元年》、阎真的《活着之上》、蔡测海的《家园万岁》、姜贻斌的《火鲤鱼》、何顿的《来生再见》、李怀荪的《湘西秘史》等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王跃文的《漫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年轻小说家不断形成新力量,老作家也在暗暗发力,志在冲顶。儿童文学在全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汤素兰、邓湘子、皮朝晖、牧铃等作家的作品多次获全国大奖。诗歌依然扮演最活跃的角色,各种诗歌创作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年轻诗人的热情参与,湖南的诗歌创作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散文也没有掉队,还常常弄出一点新气象。影视文学跑马圈地,地盘一天天扩大,一些艺术水准很高、市民反映良好的影视文学作品不断冒出来,影视文学需要与资本和传输平台联合才能实现,湖南恰好在这方面有优势。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假以时日,几位活跃的网络作家也将成为全国有影响的网络作家。还有其他新媒体艺术中也越来越多地夹杂一些迹象不明的文学元素。省作协还特别注重文学创作的引导和文学队伍建设。向名刊和评奖机构推介作品,到北京和外省开研讨会,鼓励和推动作家冲刺全国大奖,设置本省文学类各种奖项,对公开发表的优质作品进行奖励,常年不断地进行培训、讲座、进修,不惜代价培养和提携有潜力的作家。“2014年湖南文学纪事”列出来是一份长长的成绩单(见附录)。湖南的省作协会员目前是3326人,其中288人属中国作协会员,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为湖南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人才保障。毛泽东文学院,以及文学刊物、文学网站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各基层作协的工作业绩列出来也是一个长长的成绩单。
境况是越来越好,成绩在大幅度提升,实际上,对作家的要求更高,因为作家和文学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文学就是这么一个怪东西,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达并不一定能带来文学繁荣,拿钱堆出来的文学,也不见得就是好文学。就算个人奋斗和官方鼓励双管齐下,也并不一定就能逼出惊世之作和传世经典。当一个人带着强烈的追名逐利的企图去从事文学创作,挖空心思琢磨着如何才能打动读者,引起轰动,那么这样的作品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文学连赚得一时名气和实惠都不能做到,也是不现实的,人还有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荣誉感。作家,毫无疑问,它是一个职业,何况现代社会早已赋予了它职业的含义。作为职业它就应当还有养家糊口、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功能。这个职业跟其他大多数职业一样,需要丰富的生活积累,很好的教养,很高的智慧,但它又不同于别的职业,不能抱太大的“雄心壮志”,而精深的技艺和崇高的精神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这是世上最难的职业!为了保持行业活力,跟其他职业一样也有行规、定量、定级,也就难免庸俗化、市场化。排行榜、奖项、发行量、影响力,包括团队效应,文化艺术管理部门的成绩总结等。量化的结果是把艺术品与工业流水线产品划等号,所以很多作家抵触这种搞法,他们要拿出一些精力排除这些世俗的干扰,使自己处在流俗之外,尽量单纯、清高。邀宠心理是文学创作的天敌,一个优秀的作家有能力看清这个现象,也有能力穿透这个欲望,并且超越这个层次。好机会好前程谁不动心?历代伟大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他们并不是没有谋生的本领,他们只需把写作的智慧分出极小的一部分去谋一份职业,都不愁一辈子吃香喝辣。伟大的作家和清苦的生活两者并不是一对因果关系,也许有的人,他们有意要过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来达到精神上的纯粹,这些都因人而异,有的人觉得肉身的欢愉阻碍了精神的提升,为了文学,或者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抵达更高的精神层面,不得不有所放弃。湖南人是出了名的“霸得蛮”,是既懂得执着,也舍得放下,这一点似乎不用太担心的。当然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社会的文学功能发生了变化,作家的追求更个性化。但是,“杂多”的表象里一定有一个本质“一”。
文化风气处在变动之中都是常理,但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深埋着,是一种看不见的物质和意识,可能会在不同时代以不同形态表现出来。不管你的思想资源是出自哪一种文化传统,我相信,“美”、“善”、“真”是写作者永恒的追求。如今各行各业都比文学实惠,还有很多行业比从事文学更容易出名。经济学领域有一个热词叫“新常态”,文学是否也进入一种“新常态”?“常态”其实并不好玩,它意味平稳扎实,还意味着作家要更注重作品的质量,注重个人的修为和社会担当。位置、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也会相应地对作家增加新的期许。新常态的“新”意味着复杂性和一些不太好把握的新情况,以及必须面对的新困难。也好,安静下来,重新排列组合,挤掉一些水分,从被动卷入到主动介入,这个过程可能有点长。我一直认为现在还能坚持下来从事文学的人是出于对文学的真爱,漫长地准备和等待,死心踏地长相厮守。有爱,才会常怀敬意,才会想到要捍卫尊严。常态是处于一种相对放松状态,很多好文学都是在放松的状态玩出来的。放松意味着还有不那么好的一面,有时候要出丑,有时候很烂、很幼稚、不自量力、好高骛远,有时候松松垮垮,不够积极,不去为了奔奖项奔名气而写得吐血。马克斯·韦伯说“社会处于急剧变革的年代,一天相当于20年”。新事物与旧事物激烈碰撞,强的干掉弱的,重新洗牌,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同样,现在和平时期,一个人的人生一眼看到底,20年相当一天。少了大开大合的传奇故事,琐碎的日常更考验作家的笔力。其实,太刻意和太放松都不好,文艺腔、政治腔都是太过刻意的副产品,网络文学中大量的泡沫又是太放松的结果,松得太厉害就没有质量。
文学,除了给人奖项、荣誉、成功人生等世俗化的好处,它总有一种冲动,它要超乎凡俗,要追求卓越,要实现高层次的精神价值,有的甚至高得不切实际,高到肉身凡胎跟本做不到的那种程度,但是文学有必要树起这样的标杆,它使人性趋向完美。作家一方面要揭露停滞、庸俗、腐朽以及精神的萎顿,一方面有责任把光明和清澈引进来,照亮尘世间的昏暗和混乱。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热潮曾经让人们激情燃烧、尽情释放,那么现在正好冷静下来,思考一下过去没来得及思考的问题,锤炼一下写作之外的能力,比如反省的能力,独立于批评之外的能力,不受市场控制的能力。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8期)
责编:吴名慧
来源:创作与评论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