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
作者丨纪红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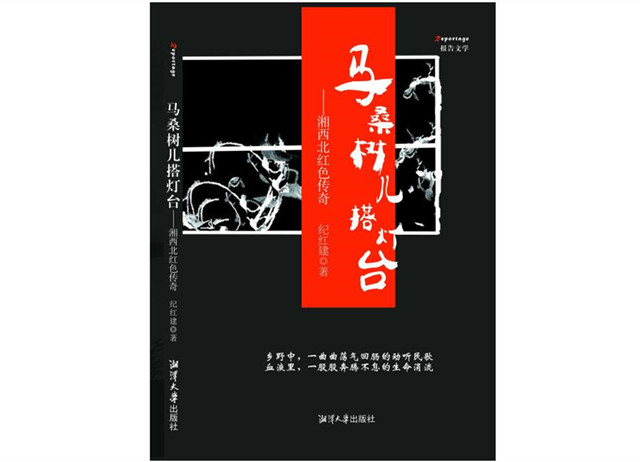
第二曲 : 不打胜仗不回乡
【第四章】寻找二爷爷
当红军去了,音讯全无,作为父母,作为兄弟姐妹,作为侄儿侄女等亲属,谁不牵挂,谁不担忧。或失散,或牺牲,这支踏上异乡的英雄队伍,他们的生死,他们的命运,就这样层层叠叠地、紧紧密密地、盘根错节地挽成了一个永不拆散的情结。
这样的故事,就像乡野中的小草,随处可见!
跟随朝阳地村支部书记庹文化,采访郑家凸组彭裕俊老人回来的路上,庹书记告诉我说,其实我娘家的二爷爷也当过红军,找他找了几十年了,从我爷爷他们那辈一直到我们这辈,都没有放弃寻找。
庹书记是个女的,在桑植,在张家界,在湘西这样的地方,虽然从不缺乏女中豪杰,但在刘家坪乡,她是唯一一个女支书。别看她是个70后的年轻女支书,但已经干过两届支书了,干支书之前,还干过两届村文书。朝阳地村,家家都在山上,她整天就是翻山越岭地往村民家里跑,家长里短的,与村民打成一片,年长的都是大爷大娘,同辈的都是兄弟姐妹,晚辈都是侄儿侄女。
庹书记说,我娘家是官地坪镇的。不知道你去过官地坪没有,对那里熟不熟。我说,去过,但不太熟。庹书记说,不熟,我就给你好好介绍。官地坪位于桑植县东北角,北与湖北鹤峰县相连,东与娄水相依。1958年前属慈利县管辖,之后划到了桑植。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加上人口多、山石多,那里的经济条件落后,算得上是桑植的贫困乡镇了。
官地坪也出了不少红军,向国登就是其中的典型。庹书记说,我们从小就听说向国登的故事。他是我们官地坪白竹溪人,土家族。他最开始也不是逮(干)的红军,而是在时为官地坪团总谷岸峭部下当兵。因为他身体魁梧,性格直爽,爱打抱不平,说话算数,一起当兵的战士都很敬畏他。后来,贺龙、卢冬生在鹤峰、走马坪、官地坪一带游击和收集失散部队时,经谷岸峭介绍,向国登参加了红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深得红军领导的赏识,职务不断得到升迁,先后当过班长、连长、营长,至1934年,已升任为红七师团长兼红七师参谋长。1935年4月,红二、六军团围攻龙山,向国登不幸在突击行动中牺牲,当时他才33岁,英年早逝啊!
庹书记说,在我娘家官地坪,像向国登这样的虽然不多,但普通红军却随处可找,我二爷爷就是红军。我爷爷有兄弟四个,我爷爷是老三,当过兵的是二爷爷和幺爷爷。
二爷爷去逮(当)红军时,还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没有成家,也没有逮对象。刚当兵那会,还经常跟家里有联系,或是通过战友和老乡逮(捎)信回家。后来二爷爷跟着红军长征了,就基本上没有信了,既没有活的消息,也没有死的消息,反正是没有丁点儿的消息。当时就有人跟我太太(曾祖母)说,你家二娃只怕死在了长征路上了。人家一说,我太太就生气,瞪着人家说,瞎说什么,死在了长征路上,部队上肯定会通知的,这是人民的军队,又不是土匪兵,怎么会不通知呢。我二娃没死,他没上学堂没念过书,不会写字,所以他才没写信回家的。
1947年左右,我幺爷爷也当兵去了,当的是解放军,专门逮(打)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的。幺爷爷当兵走的时候,我太太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他说,到了部队上,一定要打听打听你二哥的消息,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幺爷爷逮(打)过国民党军,参加过抗美援朝,逮过美国佬,逮死过三个敌人,他自己的耳朵也被逮穿了,但就是没打听到二爷爷的消息。
虽然幺爷爷在部队时没有打听到二爷爷的任何消息,但幺爷爷也有了自己的独到发现,并且这个发现得到了家里许多人的认可。幺爷爷认为,二爷爷跟着红军在长征路上,与国民党军逮了仗,并且被逮散了。后来,他就跑到国民党军队那边去了。再后来,很有可能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幺爷爷的推理有理,但没有据。但幺爷爷不这样认为,他不相信二爷爷已经死了,他始终相信二爷爷应该还活着。幺爷爷认为二爷爷可能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发现台湾有姓庹的。幺爷爷是1996年腊月去世的,去世的时候正是数九寒天。当时,他逮(拉)着我老儿的手说,和庆啊,我走了,你们兄弟几个一定要找到你二伯伯,他应该是去了台湾,你们要想办法到台湾逮(找)去。你们不能怪你二伯伯,他年轻的时候想回,是回不来,后来能回来,他又年纪大了,走不动了,所以一直没有回。我老儿叫庹和庆,是他们这一辈的老大。我们都知道,二爷爷可能早就牺牲了,但我们又都还抱着希望,希望台湾那边庹姓就是二爷爷的后代。
一天,我们姐妹几个在家看电视,哪个台,忘了,但我记得正在看电视剧《神探柯蓝》。看完一集时,片尾演员表上出现了一个亲切的名字——庹宗华,并且后面用括号注明了,是中国台湾人。我们姐妹几个几乎同时惊叫了起来。台湾怎么会有姓庹的?应该没有啊!会不会是从大陆去的?会不会就是二爷爷的后代呢?我们又接着看这个电视剧,紧盯着他饰演的秦天送看。我们越看越欣喜,庹宗华个头很高,至少在一米七五以上,这与二爷爷有相似之处,我们从小就听说二爷爷是个大高个;庹宗华与我爷爷他们兄弟几个的脸型,有几分相似,特别是眼神和眉毛,特别像。后来,我们又查了庹宗华的一些资料。1962年10月10日出生于台湾台北,祖籍湖北松滋,1971年首次触电拍摄电影《母亲三十岁》,1987年拍摄《报告班长》获得成功。于是,我们得出基本结论,庹宗华的老儿肯定是从大陆过去的,很有可能是个军人,说他的祖籍虽然是湖北松滋,但离湖南已经很近了,可能是记错了,也可能是弄错了。另外个头长相,与二爷爷特别相似。说庹宗华是二爷爷的后人,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和根据。
我老儿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也非常高兴,特别是我三幺,一口咬定庹宗华就是二爷爷的儿子。随后,他们兄弟几个就商量着如何跟台湾那边取得联系。有的说,组团去台湾,一来可以找二爷爷,二来可以顺便看看宝岛的日月潭和阿里山;有的说,找到庹宗华电话,直接问他。但说来说去,都不太现实。最后还是我老儿想了一个办法,他找到一家有当国民党军并去了台湾的,托他们的台湾亲戚去打听,并要了电话号码。电话是我老儿逮(打)的,但对方说,他老儿不是湖南的,更不是桑植的,而是湖北松滋的。我老儿说,你们是不是记错了。对方说,不可能记错。说完,对方就挂了电话。我老儿死心了,但我三幺心没死,他说,这个庹宗华很有可能就是二爷爷的儿子,只是他们混好了,当上明星了,有钱了,不承认,怕我们给他们添麻烦而已。
庹书记告诉我说,在她娘家,寻找二爷爷就一直没停过,直到现在。虽然我们都知道,随着时间的久远,希望会越来越渺茫,但从没放弃,也不会放弃。现在,我们又开始把重点放在了红二方面军当年长征走过的路线,像湖南湘西,云南昆明、丽江、香格里拉等地方。前两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不是将20万份国民党军队抗日阵亡将士人物档案对社会免费开放,查询者可以依据姓名、籍贯、工作单位或部队番号、阵亡时间及地点等线索进行查询吗?我们也开始在网上寻找了。一是在相关网站发布我二爷爷的相关信息,二是在网上寻找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战斗情况,以及相关书籍,想从这些书籍里找到一些烈士的名字。不过这会很难,毕竟当年红军的条件有限,有些红军牺牲了,就那样草草埋了,甚至红军自己都来不及埋,还是附近老百姓帮助埋的。被埋的烈士叫什么,是哪个部队的,籍贯哪里,都不知道,更没有登记。你说我们上哪儿找去呀!
我又问庹书记,你婆家有没有当红军的?
庹书记说,有啊,我老公的太公就当过红军,后来回到家后,为了逃避“剿共”大队的追杀,他也曾逃到湖北过。
我说,讲讲你太公的故事。
庹书记说,不讲了吧,我太公的故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讲不完,还是听其他红军后代逮故事吧!
在双元坪村大屋岗组,我碰到一个朴实的老人。他叫王焕松,今年68岁了。我问他听说过红军的故事没有。他说,他们王家没有红军,但他岳母的娘,也就是他老婆的戛戛是红军,是红军女儿队的。他岳母叫佘青芝,他岳母的娘叫李氏。佘青芝才二三岁,李氏就逮(干)红军去了。因为李氏走得早,佘青芝连自己是哪天生的都不清楚。更让佘青芝伤心的是,她一直没有找到自己那个当红军的母亲。她四处打听了,但没有找到任何信息。不仅没有任何信息,也没有任何待遇,更没有什么说法,即李氏既没有算上红军,更没算上烈士,政府和部队都没个定性。
虽然王焕松的岳母没有享受过烈属待遇,但他老婆的戛公,以及后来的戛戛享受过。这是为什么呢?王焕松说,我岳母有三姊妹,上头有两个哥哥,她是老幺。大舅也是红军,党部工作,是农协的。大舅是在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的部队杀掉的。那天,我大舅他们正在刘家坪的党部开会,国民党军先把岗哨摸(杀)了,再摸的他们,开会的人全被摸完了,一个也没逃出来。二舅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红军,但他也被杀了,被地头蛇杀的。地头蛇说,你大哥当过红军,你娘也是红军,留下你是个祸害。于是,地头蛇就把二舅给逮(杀)了。新中国成立后,我老婆的戛公,因为大儿子是红军烈士,所以享受烈属待遇。后来,我老婆的戛公又找了个老婆,我们这个后戛戛,也享受烈属待遇政策。
大舅二舅埋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没有成家,没有后代,每到清明,我岳母就去给他们上坟,一上坟就哭,一上坟就哭。每次上坟回来,眼睛都哭肿了。当时就有人对我岳母说,你娘肯定早就死了,死在了长征路上,现在骨头都能打鼓了,干脆就在你哥哥坟边再给你娘堆个坟,立个碑。我岳母很倔强,她说,没逮(找)到我娘的尸骨,我是不会给她立碑的,我一定要逮到我娘。可是还没逮到娘,我岳母就死了。大概是七几年,当时生产队缺水,她一个人扛着锄头,到山上找水,一不小心,掉到山上的天坑里摔死了。
王焕松说,我老婆有五姐妹,她是老大。虽然都是姑娘,但也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她们的戛戛。现在又有儿子辈和孙子辈共48口人,他们都加入到了寻找老戛戛的行列。
或许,这种寻找是徒劳,或许,这种寻找遥遥无期,但他们没有放弃。
在刘家坪村刘家坪组,我碰到了66岁的退休教师刘纪勋。他告诉我说,我家也一直在寻找大爷爷。我大爷爷叫刘开渭,在二几年就逮(干)了红军,至少当过营长。自从去当兵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大爷爷到底死在哪里,说法不一。有的说,死在了浠水,也有的说死在了洪湖,还有的说其实就死在了官地坪,谁都有理,又谁都没理,因为在这些地方,既没逮(找)到大爷爷的遗体,更没在牺牲的烈士名单里逮到大爷爷的名字。怎么死的,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战斗中牺牲的,有的说是行军途中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逮(砸)死的,还有的说是红军肃反时含冤而死。总之,最终什么也没逮清,没见到人,更没见到尸,烈士至今也没算上。算不算烈士,倒不重要了,主要是想知道大爷爷魂落何方,别让他一辈子都是孤魂野鬼。
刘纪勋老师说,唯一欣慰的是,我大爷爷是结婚生子后去当的红军,虽然他人没了,也逮(找)不着了,但他有后代,他的孙子现在都八十好几了。大爷爷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娃一个女娃,但都命运坎坷。女娃结了婚,但没有生育,最后在凄苦中度过一生。男娃是个瞎子,靠讨米(乞讨)为生,最后死在哪里都不知道。大爷爷的孙子,也就是他瞎子儿子的儿子,到处找自己的老儿,一直没找到,没办法了,他只好请来老师公。老师公施法,是湘西的一种迷信活动,在晚上进行,主要是想把大爷爷的瞎子儿子的魂逮(要)回来。施法的时候,老师公“化身”为大爷爷的瞎子儿子。你说神不神,老师公根本就没见过大爷爷的瞎子儿子,他却扮得很像,声音、动作、神态都很像,不光扮得很像,竟然他都知道我大爷爷家的事情。老师公“化身”的大爷爷的瞎子儿子,拄着拐杖,从外面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流着泪水,还唱着桑植民歌,唱的是红军时期的《农民协会歌》:
农民联合起来啊/黑地又昏天,压迫数千年/忍劳苦,耐饥寒,农民苦无边/年年扶锄犁,天天不空闲/熬过荒月苦,盼来打谷关/四六三七租课上齐,衣食不周全//农民联合起来呵/想起好伤悲,农民最吃亏/要吃饭,要穿衣,大家出主意/快快团结起,加入农协会/建立苏维埃,实行分土地/打倒土豪劣绅,我们才安逸。
唱完,老师公“化身”的大爷爷的瞎子儿子又哭了起来,诉说着旧社会的苦难,诉说着自己和老儿的可怜。这时大爷爷的孙子问道,我的老儿啊,你这些年都上哪里去了呀?家里人都急死了。老师公“化身”的大爷爷的瞎子儿子说,娃儿啊,老儿逮(逮)你爷爷去了呀!大爷爷的孙子说,老儿啊,你是个瞎子,怎么找得到爷爷呀!老师公“化身”的大爷爷的瞎子儿子说,老儿的眼睛是看不到,但老儿的心看得到啊!我总感觉你爷爷就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于是我就往前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去过湖北,也去过云南,还到过四川,但看着你爷爷在跟前,就是逮(抓)不到他。老儿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更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只知道离家很远了,走累了,于是坐下来休息。休息完了,一醒来,发现自己就回到家了。大爷爷的孙子说,老儿啊,你走那么远,难道你就不想我们吗?老师公“化身”的大爷爷的瞎子儿子说,怎么不想啊,你们都是老儿的娃儿,都是老儿的心头肉呀!但我也是你爷爷的娃儿,是你爷爷的心头肉啊,不找到他,我死了也闭不上眼呀!
刘纪勋老师说,他们“父子俩”的对话,让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感动得全都哭了,好像大爷爷的瞎子儿子真的回家了一样。
……
我想说的是,寻找二爷爷,寻找戛戛,寻找大爷爷,只是一个代名词,在桑植,在苏区,所有期待英雄回家的亲人,都在寻找。红军长征前寻找过,红军长征后还在寻找;新中国成立之前寻找过,新中国成立之后还在寻找;二十世纪寻找过,二十一世纪还在寻找;英雄的父母寻找过,英雄的兄弟姐妹寻找过,英雄的侄儿侄女寻找过,现在他们的侄孙侄孙女,甚至侄曾孙侄曾孙女还在寻找。
我把采访中看到的这些情况跟一个朋友说起,这个朋友竟然嗤之以鼻,说道,几十年过去了,早已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物是人非,还有寻找的价值与意义吗?向现实低头吧!
我听了很无语。
我告诉他,他们不是没有找到吗,找到了,他们的心也早就落地了。其实他们寻找,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物质上的补偿之类的,而只是想知道他们的亲人何年何月,死在何处,魂守何方。而事实上,他们的寻找,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才去寻找,而是上一代向下一代的嘱托,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我在想,难道这样的寻找只是某一个亲人、某一个家庭、某一群家庭、某一个时代的家庭的事情吗?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的共同义务与责任吗?
这种寻找,没有过时,永远也不会过时!
【由《中国作家》(2016年第11期)首发,湘潭大学出版社单行出版(2016年10月)】
责编:吴名慧
来源:蓄势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