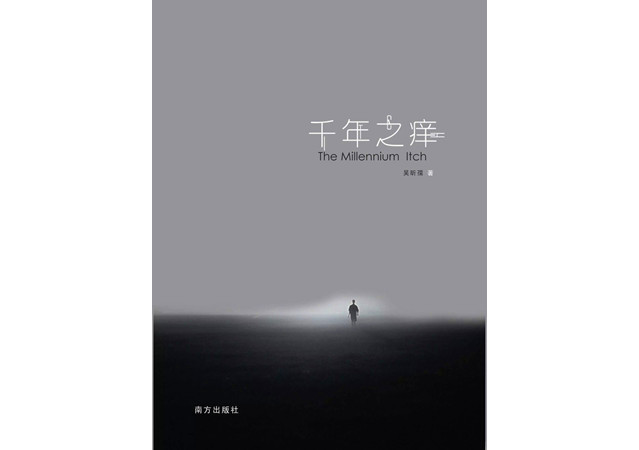
千年之痒
作者丨吴昕孺
第十三章 未曾消失的地平线
昌茜一直在深圳工作。她做的是什么工作,乌去纱始终没弄清楚。偶尔昌茜回脱甲家里,在橘洲中转,住在姐姐、姐夫家,他曾经表示关切地问过。昌茜总是一脸顽皮的笑,一忽儿说做餐饮,一忽儿说推销啤酒,一忽儿说当售楼小姐,上次回来说在学习美容。没有一次答案是相同的。乌去纱喜欢这个姨妹子,他自己没有妹妹,他和昌静加起来才这一个妹妹,当然看得重。而且,昌茜性格上比昌静活泼,脾气却温存些,他和昌静几次大吵多亏了昌茜从中斡旋,足可见其心细懂事。乌去纱和昌茜说话不多,他感觉得到姨妹子对他这个姐夫也比较满意。她曾表露,要找个像姐夫这样的男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乌去纱心里美滋滋的。
昌茜每次来橘洲住几天,乌去纱都会买最好吃的菜,带着她和全家一起游公园、看电影,陪姐妹俩逛商场,亮亮更是对昌茜特别念想,每次听说小姨要来,就兴奋得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上次昌茜回来,还是去年,他们一家三口和她一起去烈士公园。亮亮一进游乐场就出不来,昌静追着儿子跑上跑下,生怕他被人潮卷得不见了,乌去纱陪着昌茜在后面说话。乌去纱好玩地说:“在深圳做了这么多年,回橘洲来吧,可以帮你姐姐打点理发店。”昌茜照例顽皮地笑笑:“我没有学过理发,帮不上啊。再说深圳的钱好赚些,再赚个两三年,回来找个男人结婚就不出去了。”乌去纱笑着说:“找个有钱的老公就不需要自己去赚了。”昌茜努努嘴说:“有钱人靠不住,得自己有钱。像姐夫这样实诚的人最适合做老公,可惜找不到哦。”乌去纱正美滋滋的时候,昌静怒气冲冲地喊道:“你在这里悠什么悠,快去看你崽跑到哪里去了!”乌去纱急忙小跑到前面,立即被昌静喝住:“往那个方向去了呢!”乌去纱又向昌静指的方向跑去。跑了十来米,没看见儿子,乌去纱急了,使劲喊了两声,没人应,一些游人回过头来望着他。他侧转身子,对另一个方向再喊两声,一双小手从后面抱住他的腿。他紧紧抓住那双小手,将它们直直地往前面扯,让儿子的脸贴着他的臀部,一边高声叫道:“爸爸打屁了!爸爸打屁了!”儿子在后面,脸别来扭去,努力躲着爸爸嘴里说的那个屁。他拼命躲闪,看上去却像是一个劲地往爸爸的屁眼里钻,弄得乌去纱挺着肚子,仰起身子,煞是滑稽,逗得附近的游客都笑起来。
1999年中秋,25岁的昌茜要做新娘了。新郎是邻村一位武姓小伙子,比昌茜还小一岁,据说家里比较富裕,有一栋威武的红砖楼房。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排行最末,三个姐姐都出嫁了。乌去纱纳闷地说:“昌茜很少回来,小伙子不在深圳,他们是怎么谈成恋爱的?”昌静抢白道:“你管得宽,那是人家的私事。他们是小学同学,小时候就玩得好,你以为非得黏在一起才能谈恋爱啊。”乌去纱说:“我随便问问,你急成这样子干什么,又不是我在谈恋爱!”
昌静一听,眼里喷得出火来,把脖子都烧红了。“瞧你那德行,还有谁看得上你!昌茜嫁出去我们大家高兴,你好像蛮伤心,是不是不想她出嫁啊?”乌去纱气得想上去掴昌静一巴掌。他忍住了,他没有忍住的是在心里掴了她一巴掌,又狠又准,差点把她脑袋掴成高尔夫球了。上个月,橘洲市一家私立医院为做个软文广告,请编辑部到银洲娱乐城打了半天一杆高尔夫,汤仕宏、李美超、单洪涛、骆明明,连邓大姐都去玩了。汤仕宏成绩最好,动作最标准。乌去纱进步最快,得到了教练的表扬。回来好几天,他还在温习教练教的动作要领。这次平白无故被昌静抢白一顿,他就在心里虚构的高尔夫场上,把昌静的脑袋当球,狠狠击打了一把。既出了一口鸟气,又不会伤害到人,乌去纱为自己找到这样一种阿Q式方法感到悲哀,又庆幸。
为这次吵嘴,直到国庆临近,两口子还像一对冤家,爱理不理。要回脱甲的前一天中午,乌去纱回来,看见冷清了一向的饭桌上摆着几道新做的菜。昌静虽然不说话,但家里的气氛轻松很多。他不管,坐下来就吃。过一会,昌静端了碗在旁边坐下,随意地问了句:“明天,你会去吧?”乌去纱把口里的饭嚼完,答道:“姨妹子结婚,姐夫哪能不去!”昌静把碗放到桌上,伏在乌去纱膝头呜呜哭将起来。乌去纱一时无措,他也把碗放到桌上,搂着昌静的肩,拍着她的头,温柔地说:“傻,哭什么。”
昌静坐起来,抹一把泪水,倾诉着委屈:“每次吵架,你都不理我,总是我先放让来求你,你是男子汉哩!”乌去纱没有作声,他不好怎么说,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他放让去求她的次数要多得多,但无论如何,这一次是昌静先放下架子。他拿不准要不要道歉。最终,他说:“你是个好老婆,下次我一定先放让。不过,最好不要有下次了。”昌静甩了甩头,斩截地说:“不,这次你就要跟我道歉。”乌去纱摸摸她的脸,顺势揩下一掌泪水,说:“好,对不起,不哭了。”
第二天,乌去纱和昌静带着亮亮回脱甲。路过罗岭,亮亮隔着玻璃叫道:“奶奶家里,我奶奶家里!”乌去纱问亮亮:“想不想去奶奶家?”亮亮点点头。乌去纱说:“过年我们回奶奶家,这次没时间了,我们要赶小姨的婚礼。”亮亮问:“爸爸,小姨跟谁结婚?”乌去纱说:“一个叔叔。”亮亮问:“小姨为什么要和那个叔叔结婚?”乌去纱说:“他们相亲相爱啊,就像爸爸和妈妈一样。”亮亮说:“我也要和小姨相亲相爱,我也要和小姨结婚。”乌去纱说:“你还没长大,等你长大了,自然会有相亲相爱的对象。”亮亮若有所思地说:“哦,那我的对象会是谁呢?”乌去纱说:“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很想知道呢,亮亮快点长大吧。不过,你可得认真找,要找个像小姨那样漂亮的。”昌静冷眼瞟着乌去纱,很不理解地说:“你实在是个文化人,哪里有这样教儿子的!”乌去纱答道:“这就是文化人的教法,未必你教他找个丑的?”
昌静把儿子抱了过去,仿佛要让他远离污染源。乌去纱对着车窗玻璃上模糊不清的自己,做出一个挤眉弄眼的鬼脸,吓得玻璃里那个模糊的影子逃之夭夭。田野、树木、山峦、房屋、电线杆……不知道那个影子躲到哪里去了,也许在某个草垛后面,也许被一只饥饿的山鹰叼走了,也许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昌家一派喜庆气氛。门窗上贴着大红的喜字剪纸,有方形的、圆形的,还有和牡丹、鲤鱼、娃娃等一起构成图案的。家里人忙上忙下,特别是昌妈妈,难得看见她那样开心的笑,却忙个没停,越是忙她越是开心。昌爸爸拄着拐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会讲,待客是一把好手。乌去纱看着满屋子人,好像是一屋子活动的“喜”字。如果每一天都是这样高兴,还需要钱干什么?还需要职位干什么?乌去纱想。晚饭后,他看见昌静要帮妈妈和妹妹的忙,怕儿子捣蛋影响她们正在筹划、准备的大事,便带着他出去玩。
他们来到屋左侧的一片田野,由好几丘处于同一水平面的稻田组成,中间有一条三四尺宽的水渠,因为过了收获季节,渠里没什么水,长满了草,草茂盛得让水渠变了形,更像是一道小峡谷。连接水渠两边稻田的,是一块窄窄的水泥板。大人作下准备,做个深呼吸,跳过水渠去都不难,但对于孩子,它就是天堑变通途的唯一桥梁。所以,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长水渠上仅有这么一块窄窄的水泥板,它显得非常骄傲,想过去的人得小心伺候它,低眉俯首,怀着一种敬畏感,它才不会生事。
乌去纱开始想抱着亮亮过去,但儿子不肯,硬要自己过。他便牵着亮亮的手,小心翼翼地过去了。那边草垛多,好捉迷藏,儿子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捉迷藏。家里那么一巴掌大的地方,他也要和爸爸妈妈捉迷藏。有时,乌去纱故意装作找不到的样子,满屋子转悠,亮亮就会在门背后或者床底下放声大叫:“我在这里!”有天晚上,亮亮躲到黑乎乎的厨房里,乌去纱装作找不到,又故意不作声,屋子里顿时一片静寂。没过两分钟,儿子慌忙从厨房里跑出来,像火箭一样钻进爸爸怀里。乌去纱知道,儿子被黑暗吓着了。寂静的黑暗尤其吓人。他紧紧抱着儿子,通过肢体向他源源不断地传输着父爱。乌去纱对“父爱”的理解就是这样——告诉他黑暗的所在,并让他知道,那不可怕。
亮亮躲在一个草垛后面,乌去纱正要抄过去,忽然听到他喊:“爸爸,快来看,这只虫子着火啦。”乌去纱说:“这不是着火,是发光,看上去像着火了,所以我们叫它萤火虫。”亮亮问:“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乌去纱说:“它的肚子里藏着一只灯笼。”亮亮问:“它的肚子里为什么要藏一只灯笼?为什么蜜蜂的肚子里没藏着灯笼?”乌去纱说:“因为,因为萤火虫喜欢晚上出来玩,它怕看不见,碰到电线杆子或者大树,会被撞死去。你看,带着灯笼照明,就可以玩得很开心了。”亮亮问:“蜜蜂为什么不喜欢晚上出来玩?”乌去纱说:“蜜蜂特别乖,晚上要在家里做作业,所以蜜蜂成绩好,它酿出来的蜜多甜,你没听说过萤火虫会酿蜜吧?”亮亮摇摇头。乌去纱接着说:“是的,萤火虫只知道玩,白天玩了,晚上还要带个灯笼出来玩,它能酿出蜜来才怪呢。”
月近中天,更衬托出夜的深度。乌去纱在想着法子把玩疯了的儿子弄回去。聪明的亮亮一听萤火虫贪玩酿不出蜜,立刻答道:“那我要回家做作业。”乌去纱高兴地说:“好,真乖。”他话音未落,亮亮一溜烟向外婆家的方向跑。乌去纱刚反应过来,两个大跨步,已经晚了,眼睁睁看着儿子从水泥板上掉进水渠里,旋即传来儿子呕心吐肺的嚎叫声。乌去纱纵身跳进渠里,把亮亮抱起来。渠里没水,草深渠不深,亮亮是被吓着了,背上粘了很大一块淤泥。
他一边哄,一边把儿子抱回家里。哭声渐止,但背上那块淤泥就像战败国的旗帜。昌静厉声问:“怎么了?”没等乌去纱开口,亮亮看见妈妈,一股娇气上来,又哭着说:“我掉到水沟里了。”乌去纱说:“没事,渠里是干的。”昌静指着乌去纱的鼻子吼道:“没事是因为渠里没水,要是有水不就有事了!”乌去纱不示弱地打着反口:“要是有水我就不会让他掉下去。”昌静愤怒地把手抡了一个圈,怒斥自己的老公:“掉下去了才知道没水,好意思讲有水的时候你不会让他掉下去,胡说八道!”这时,昌茜过来拖走姐夫,用一双企盼的眼神望着他。昌妈妈也在那边批评大女儿不懂事:“明天你妹妹结婚,你们吵也捡个日子好不好?”昌静的脸倏地一沉,好像一处大规模的塌方,她推着儿子到屋里换衣服去了。
乌去纱对昌茜说:“对不起。”昌茜说:“没事,姐夫你辛苦了,早点休息。”乌去纱说:“还早,你们没忙完,我再出去走会儿。”昌茜说:“那好,姐夫你不要走远了,早点回来,我们马上好了。”
乌去纱出门,走右边的小路,二三十米远处有一口池塘。蛙鸣传入他的耳际。青蛙独有的气囊让它小小的身体能发出极大的聒噪,鼓凸的眼珠、滚圆的肚腹、肥硕的大腿、碧绿的肤色、轻盈的跳跃……它周身都是热闹的,仿佛它润滑、细薄的皮肤里装着取之不竭的声音,它是一面跳动的鼓。
一口池塘里有着无数面跳动的鼓,你在村庄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可能躲开它们。但如果没有走近池塘,没有进入或者面临这一场景,对蛙声便会置若罔闻,它像天上的云朵、地上的蚂蚁一样,自然而然地成为山村生活背景的一部分。乌去纱不想惊动那些天才的音乐爱好者,他知道它们唱的都是求爱歌曲,它们是天生的爱情理想主义者,浪漫得求爱都要采取团体的方式,大张旗鼓地歌颂本能和欲望。
他在塘沿扯起一根狗尾巴草,含在嘴里。不料那极微弱的草被扯断的声音,竟被青蛙捕捉到,刹那间,它们全体整齐地安静下来,像有一个指挥打出了猛烈的手势。乌去纱满怀歉疚——他和昌静的吵架惊扰了昌茜的婚事,他随手一个动作又打断了正在求偶的蛙群的合唱——他咬断嘴里的狗尾巴草,嘴里呼出一股淡淡的青气,回到了家里。
昌茜和她妈妈在客厅等着。昌茜告诉他:“姐带亮亮上楼睡了,她要你睡楼下。床铺已经整好,你洗了脸就好好休息吧。”昌茜把楼下西厢房的门打开,一个小房间里,一张不算小的床,看得出被褥铺盖都是刚换上的。乌去纱躺到床上,十分舒适,山村的夜晚渐生凉意,这是他熟悉的。一床薄被盖着自己的身体,把白天发生的一切轻轻抹去,明天起来将是崭新的一天。
乌去纱久久不能入睡。他的耳朵里灌满了外面池塘的蛙鸣,虽然偶尔想起儿子掉落水渠和晚上与昌静吵架的事,也是一闪而过,就被隆重的青蛙合唱团驱逐得无影无踪。越到深夜,那支队伍似乎越加庞大了,声音是那么整齐划一,像一刀刀削过的、胖嘟嘟的米豆腐。乌去纱最喜欢吃妈妈做的米豆腐,里面放些剁辣椒,撒几片葱叶,爽口得不行。姐姐学着做,一模一样的佐料,一模一样的火候,一模一样的动作,做出来的味道还是不一样。姐姐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她问妈妈,妈妈说:“你的手工不够,要做上二十年饭菜,才有那个感觉。”姐姐不信,她又问乌去纱。乌去纱说:“你做一辈子也不可能有妈妈那种感觉。”气得姐姐嘴巴撅了半天,像弯月牙。现在,乌去纱躺在床上,倾听满池蛙鸣,仿佛置身于一台音乐会现场,心里充满着轻快与愉悦。罗岭当然不乏蛙鸣,但这么多年来,他从未这样欣赏过。他发觉青蛙合唱团还真是训练有素、非常专业的一支队伍,它们有声部,有领唱,有重唱,全是雄性嗓门。高昂处如惊雷滚滚,震动天地;低沉处如回涛叩岸,撞击肺腑。乌去纱双手搭过头顶,薄被疏离,劲臂斜露,起伏的胸腔有如一个膨大的中空共鸣体,与屋外的蛙鸣互相应和。此起彼伏,此起彼伏,此起彼伏……
他起的时候,她伏了下来,伏在他的胸腔上。她也发出一阵响亮的叫声,似蛙鸣,非蛙鸣。床铺在下陷,他们一齐陷入水中。她继续叫着,头发像水草一样竖立、飘浮,看得到她红润的腮帮像充满气的气囊。在水下,还能听到她的叫声,由粗放转成尖细,形成一股一股波浪,抵达他的耳膜。乌去纱被她奇妙的叫声撩拨得无比激奋,他随着波浪的节奏不断起伏。突然,她坐在他身上直起身子,头发向后一甩。啊!是……
她朝他诡秘地一笑,像只肥硕的雌蛙身子一缩。乌去纱已经没有了起伏,他不知道是在上升,还是在沉溺。他时而像一艘乘风破浪的舰艇,时而像一只风雨飘摇的破船。直到雨停、风住,船帆悄无声息地降落。蛙鸣销声匿迹了。一只手轻轻爱抚着他的脸,手上金黄的戒指隐隐一亮,仿佛黑夜里擦一根受潮的火柴,火星一迸,却没燃得起来。
第二天,亮亮跑到房里喊爸爸,乌去纱在朦胧中醒来。“爸爸,外婆说新娘子要出阁了,你快起床!”睁开眼,他想起昨晚的梦,觉得对不住昌茜……幸好是一个梦,只有他心里知道,就在心里跟她说声抱歉吧。起床的时候,乌去纱觉得下身潮乎乎的,四处摸索,并没有遗精,但那玩意像在酸水里浸泡过的黄瓜,皱巴巴、软塌塌的。
他穿戴好,出了房门。昌静和她妈妈正在客厅给昌茜化妆。昌茜穿着一件长长的粉红色连衣裙,长发盘在头顶,脚上是黑得发亮的高跟皮鞋。乌去纱呆呆地看了会。昌茜脸上红红的、粉粉的,是昌静涂上去的,还有连衣裙映上去的。但乌去纱分明看见她额头上都红了,耳根也红了。那不是一种简单的红,乌去纱说不出所以然来。让他难堪的是,昌茜直直地望着他,从她眼光里,似乎知道姐夫昨晚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那眼光里没有丝毫责怪,反而跳跃着快乐。
“姐夫,昨晚没睡好吧?就怪我姐,姐夫是客人,还吵架,要不得。”
“他算哪门子客人。要是客,我早下逐客令了。”昌静接过话头。昌茜用高跟鞋踩了姐姐一脚。
“你多亏嫁了小乌。我和你爸都不是这样。你那张嘴刻薄得像把刀子,伤的会是自己。”昌妈妈数落起大女儿来。
“我姐是刀子嘴,豆腐心。姐夫不会放在心上的。姐夫你看,我今天漂亮不?”
乌去纱舌头像打了个结,总算吐出两个字:“漂亮!”
上午十点,新郎小武来接亲。昌家把前门、后门关得紧紧的,要新郎从门缝和窗户丢红包进来。昌静带着亮亮占据了窗前一个有利地形,不停地伸手向新郎要红包,拿一个拆一个。如果里面只有一元、两元的票子,就骂他小气,直至要到一个里面塞着两张十元的,才罢休。
新郎小武个头不算矮,约有一米七二,眉目还清秀,但瘦得可怜,两只裤筒空荡荡的,好像里面没有脚。乌去纱暗暗吃惊,昌茜怎么找个这样的小伙子,难道看上他家富裕?唉,小伙子人好就行,犯不着替别人操空心。昌静找了我,不明就里的人也会这样看呢。
婚礼在男方家里摆了三十多桌,吃了两轮。乌去纱怕鞭炮伤着儿子,大部分时间守着他,漫不经心地边走边看。他估计,男方家里也富裕不到哪里去,昌茜选择这个小伙子也许是因为自己大龄,怕嫁不出去了。女孩子过了25岁开始滞销,很多好女孩急于嫁人,一不小心就遇人不淑。祝昌茜好运!
在婚宴上竟然碰到周万年。原来,小武是他的远房侄子。周万年以此取笑,说从此辈分高他一级。周万年没在《环境保护报》干了,自己下海开了一家文化公司。他递给乌去纱一张名片,名字后面写着“总经理”。他们坐在一桌,儿子去上亲席昌静那了。乌去纱想图个轻松,就坐在这一桌和周万年聊天。
周万年说他上个月刚赞助了他们高中同学的聚会,这是人来得最齐的一次,全年级只缺了七八个人。乌去纱说:“吴盈盈肯定是其中一个。”周万年说:“她从不参加同学聚会,同学们都认为她铁定不会来,上次她倒来了。她说,你没去找她啊!”乌去纱喝了口水,淡淡地答道:“是的,事情多,忘了。”周万年说:“难怪,我跟她打赌,说你一定去找过她。她一口咬定我赌输了,看来我是真的输了。”乌去纱心里说,其实你赌赢了,我去找过,只是没找到她。他问周万年:“吴盈盈还在有机化工厂?”周万年说:“她不在有机化工厂能去哪里?我还告诉你,她在有机化工厂的树脂实验室,你不信当我没讲。”乌去纱有口无心地说:“不是不信,确实忙,找她又没什么事,就搁下了。”周万年压低声音说:“你别蒙我,找吴盈盈不要有由头,吴盈盈本身就是由头。说有什么事去找吴盈盈,那些事都是假的,找她才是真的……”
乌去纱听得一愣一愣,正好新人过来敬酒。一桌子人站起,领着新人过来的那位大伯笑吟吟地致谢,他声音高亢,像长着气囊的青蛙,毫不费力地发出轰鸣。昌茜直直地看着乌去纱,把半杯红酒递过来,要跟姐夫碰杯。乌去纱把酒杯递过去,咣当一声。没料到昌茜递过来时藏着力气,两个杯子里的红酒霎时波涛翻涌,跃然于空中,昌茜杯子里的一些红酒掉进乌去纱的杯子里,乌去纱杯子里的一些红酒飞到昌茜的杯子里。青蛙大伯张开气囊说:“昌茜,跟姐夫可以这样碰杯,可不能这样碰身子哦。”满桌大笑。乌去纱尴尬地笑着,昌茜在青蛙大伯背上拍了一掌,笑吟吟地骂道:“死不正经!”
乌去纱找到了有机化工厂的厂址,还是在新开铺那边。从橘洲地图上看,离76路终点站和动力机械厂都很近。他自己都不明白,当初毫不犹豫跑到新开铺去找内衣厂,不惜南辕北辙,急得连内衣厂究竟在哪个位置都没去证实,后来从周万年那里得知吴盈盈在有机化工厂,却始终按兵不动。说心里话,他没有因为内衣厂不在新开铺而泄气,否则他不会再去黑石渡找内衣厂;他也没有因为吴盈盈不在内衣厂而沮丧,他认为那只是生活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橘洲城并不大,吴盈盈那么大一个人,能藏到哪儿去?他一个人在街上走的时候,比如在采访途中,比如去新华书店,比如送某位客人到车站回来,常常想,要是在街上遇见吴盈盈,那该是多么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我们还认识吗?她会是什么表情?她会跟我说话吗?以至于当乌去纱现在从周万年那里得知有关吴盈盈的新信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激动和兴奋,而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这是又一个玩笑的开始吗?
他不急于去找有机化工厂,是对上帝把生活当作游戏的不严肃态度的抗议,有点印度人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意思。同时,他隐隐意识到,或许上帝从来没让吴盈盈进入过他的现实世界,她根本就是梦想中的一个人物。上帝开的玩笑还不是内衣厂不在新开铺,而是吴盈盈不在现代,弄不好她只是古代传奇中的一个普通女子……一想就有些远了,很不切实际,但乌去纱无法按捺自己不这样想。如果昌静知道他真实的内心图景,肯定会从嘴里扔出两枚硬硬的石子:德性!
他试图说服甚至迫使自己摒弃妄想,进入他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妻子、儿子、单位,他拥有过好日常生活的所有要素,他不能贪图更多的东西。这么多年来,吴盈盈始终是他脑海里一道最为绚丽的风景线——有时是很大一片原野,广袤无边;有时像一堵墙,阻隔了喧嚣和烦扰;有时只是细细的一线,仿佛随时会飘走,却坚韧地维系着一缕缥缈的梦幻。昌静曾经是他的女神,如今早已在柴米油盐、争吵勃谿中堕入滚滚红尘,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主宰。亮亮出生后,他除了工作,几乎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他,儿子就是他的王,他一切的一切。然而,儿子在他心灵所占领的高地,与吴盈盈那道绚丽的风景线,不搭界,也不重叠,不相冲突,更不相抵消。生活中最大的忧伤,便来源于这种念兹在兹的不可替代,因为不可替代所产生的强大张力,既丰富又撕裂着乌去纱敏感的内心。你可以拒绝丰富,却无法拒绝撕裂。
蔡锷北路公交站,2路车一天要开无数趟。同理,东塘去新开铺的76路车每天也要开无数趟,像流水线。它们每天无数次抵达终点,回到起点,说明它们从来就没有终点和起点。所谓终点,对于与那个地址不相干的人来说,永远没有意义。公交站依然吵闹不堪。公交车、中巴和的士,绞成一团。分贝大部分来自中巴车上的售票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无一例外地扯起喉咙。谁喉咙大,谁招到的客就多。若同时来两三台同一线路的中巴,售票员得跳下车,张开两臂,像傍晚招呼鸡鸭进埘那样,把乘客圈进车里。公交车最霸道,因为这里叫公交站,本是它的根据地,到自己家里自然可以大大咧咧,横冲直撞,说停就停,说走就走。中巴车也不是吃素的,虽然比公交车小一号,却机动灵活,你挤我我就走一点,你让我我就靠一点,只此一招便赚走公交车不少人脉。的士则显得清高,从很远的地方极快地驶来,到了公交站放慢速度,边看边走,鸣几下喇叭,半招呼,半炫示,一副才不指望你们这些抠鬼穷人上车的样子,看看的确无人动心,又一脚油门极快地驶远,似乎在告诉用目光追随着它的那些人:“哼,你再想坐,我都不会回来了。”这三种车把公交站弄得像黏在一起又烧煳了的糍粑,扯不开,咬不烂,这是城管和交警最头疼的地方。不过交通确实方便了许多,乌去纱上的是走2路线的中巴,比公交车贵一块钱,但它有位子,比公交车快。
在东塘下车,又看见那个邮政报刊亭,一间戴着绿帽子的白屋子,白色染黄了不少,绿却仍是那么耀眼。乌去纱走过去,站在里面的不是上次那位大爷,而是一个长着两道剑眉的妇女。她站在里面清点刚到的日报,乌去纱拿出一块钱买了份《南方卫生报》(报纸是去年涨的价),顺口问一句:“这报纸好卖吗?”中年妇女恼怒地望他一眼,一副扬眉剑出鞘的样子,大概是责怪来人打断了她数报纸,她把右手食指往嘴里沾些唾液,又开始从头数起。乌去纱没再问,拿着报纸走人。
76路也有中巴。那辆中巴全身伤痕累累,到处贴着膏药,有一扇窗户没有玻璃,里面世事洞明。有人在催司机快点走,司机的头还伸在窗外,望着匆匆行人,不停地喊着:“新开铺,新开铺,马上走了!”乌去纱观察着车子的情况,发现中巴上坐得比较满了,公交车人却不多,正想去上公交车,一个满脸横肉的男子上来拽住他,说:“中巴快些,上车就走。”乌去纱说:“没位子了,我坐公交车。”男子脸一板,手上加了力,说:“兄弟,给我个面子,上车就走!”乌去纱就这样被他捉上了中巴,尽处劣势的乌去纱想挽回些面子,大声讨价还价:“你车上这么多人,总不能让我站到新开铺吧。”男子说:“没问题,保证你有位子。”他往车上一站,对着坐在发动机顶盖上的几个妇女吼道:“这里还要坐个人,挤紧点。”妇女们嘴里一边嘟囔着,一边把各自的屁股往两边移,中间果真腾出邮票大一块地方。乌去纱勉强坐下去,开始只放了一个屁股尖,车子启动,一颠一簸,不久就把整个屁股安置在上面了。
开到井湾子,中巴车停了。被另一辆76路中巴招停的,原来那个车上只剩下四名乘客,那辆中巴的司机赶着他们拼到这辆车上来,他则打转开回东塘去。四人中有两个不愿意下车,因为到这辆车上来就没有座位了。司机做了很久的工作,那两个客人纹丝不动。这边车上的人急起来,渐渐骂声四起,有的骂那个车的司机,有的骂坐在那个车上的两个固执的人,有的把所有中巴都骂了个遍,有的骂管理中巴的市政府机构,有的索性骂起贪污腐败来了。僵持了好几分钟,这边车上满脸横肉的男子一口唾沫吐到手心,说:“等老子来!”他龙行虎步地上了那辆车,果然把那两个人赶到这边来了。他们低着头,像是绑在一辆牛车前面的两头磨洋工的牛。
其中,有一个个子较高的女子,刚好站在乌去纱前面。如果两个人都站着,他们应该是面对面。但她站着,乌去纱坐着,乌去纱面对的便是她的下半身。女子穿着有点过时的喇叭裤,裤头和裆部很紧,下半身各个部位的轮廓分明可见。这对乌去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他曾偏过头去看别的东西,比如透过人的缝隙看窗外的风景,看一对抱着坐在一起的恋人,看一个老汉提上来的不知是烂了去修还是修好了拿回去的电风扇。但这些东西太乏味,让偏着头的乌去纱感觉很辛苦,他只好摆正自己脑袋的位置,那个女子的喇叭裤和她不错的身材是他疲惫目光最好的寄托之所。他抬头瞅过那女子一眼,头发烫成个大爆炸,模样不赖,在这车里最为打眼。她似乎有些感觉,也低头盯了乌去纱一眼,那种冷漠、警惕的眼光,像是审视,告诫乌去纱不要图谋不轨。但审视归审视,她不能动弹,乌去纱也不能动弹。
到新开铺下车的时候,乌去纱腰酸脚麻,腿间裹着一团沉沉的胀疼。好不容易站起,内裤里有点湿湿的感觉,走起路来横七竖八不那么利索,像老倌子一样伛着腰。女子先下车,目不斜视,急蹬蹬地走了。乌去纱望着她的背影,心里漾起丝丝涟漪。
乌去纱想起上次到这里找内衣厂,恍如昨日。这里毫无改变,连公交车站前面那堆垃圾看上去都像是原封没动,动力机械厂门口还是那几个流动摊点,买凉粉、臭豆腐以及即将腐烂的水果。乌去纱站到一个花坛边,上次他在这里碰见一对神仙眷侣般的老年夫妇,两位老人面容上那明湛祥和的光华,此后他再没在其他地方、其他人身上见过。站了好一会,没见着那两位老人,他问凉粉摊的女摊主:“有机化工厂怎么走?”女摊主朝南边努努嘴,说:“往前走300米可以看到有机化工厂的后门。”
真近啊,上次来要是直接去有机化工厂该多好!是不是一定要有阴差阳错,才算是生活呢。
往前走到一两百米时,空气中渗进了一种特别的气味。然后每往前走一步,气味就浓一点。一直走到约300米处,在一堵长长的墙上很突兀地开出一扇小门。看那扇门的样子,好像是去一间偏房或者密室。它旁边写着几个很不好看的毛笔字:有机化工厂。
乌去纱推门而入,里边一个声音问他:“你找谁?”他听到声音后,循声望去,右侧有间小房,房里摆着一张单人床,一个喉咙里发出痰音的人坐在床上。“我找吴盈盈。”乌去纱说。好一会,只听见痰响,没听到回答,乌去纱再加上一句:“她在树脂实验室,我是她同学。”又是一阵像火车在远方驶动的痰音,没有回答。乌去纱估摸着他是默许了,慢慢地走过去,果然没见阻拦。他呼出一口气,搅动了这里长期以来集结成团的浑浊空气,它们遇到从乌去纱口里呼出的清新之气的挑衅,悍然发动反击。一时间,乌去纱从未见识过的浓烈、刺鼻异味,像一大群马蜂围着他叮螫。乌去纱撒腿就跑,不知跑了多久,好像翻过一道坡,穿过一片树林,气味才疏淡下来,不是叮螫而像是一种抚摸。乌去纱跑不动了,只好停下来接受这种令人恶心的抚摸,他感觉到身体内部胃的狂躁,仿佛一条饥饿的鳄鱼在泥水里扑打。
厂区内看不到人,只看到树林那边有栋乳白色的楼房。他走过去,绕到楼房的正面一看,挂着“树脂实验室”的木牌,得来全不费工夫。奇怪的是,他一转到楼房的正面,空气中那股异味就消失了,跟外面正常的空气没有两样。
走进楼房,一楼过道右边还有一个传达室。有人问他:“你找谁?”乌去纱答道:“我找吴盈盈。”那个人在打毛衣,她停下手里的活计,问道:“你是她什么人?”乌去纱说:“我是她高中同学。”那个人继续打毛衣了,一针针挑起来、戳进去,挑起来、戳进去,循环往复。她说:“你来得不是时候,吴盈盈辞职了。”
乌去纱大吃一惊:“辞职了!不会吧?上个月同学聚会,我还见到她。”他心有不甘地撒了一个谎。那个人放下手上的毛衣,从抽屉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红头纸,是橘洲有机化工厂对下属部门发出的通知,上面写道:
同意厂工会陶渊铭、三车间杜子梅、实验室吴盈盈三位同志的辞职申请,请各部门妥善安排、布置,以不影响生产进度和工作指标为务。
“吴盈盈!”这回没错。
三个字,一个个像探照灯照进乌去纱心里。乌去纱感受到了灯光的刺眼和晃动,但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它在哪里。
(未完待续)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