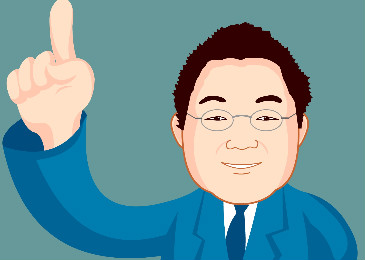
孙麟先生
文丨刘永学
见人,动辄冠以先生的称谓,眼下着实是不太多见了。以前,似乎不是这样。比方说在上海,在北平,那些得洋气之先的布尔乔亚们就专门批发“先生”的帽子,满天飞。这还犹自可。读鲁迅的《两地书》,大师亦有一段时间称许广平为先生,我纳闷了许久,这不是抹杀了男女之间称谓的区别么?不过,很快释然了。大师所表达的是对广平女士的一种认可度,既然“先生”这顶帽子合适,那就戴戴无妨。老派的中国人没有这份潇洒和随意,他们还习惯地叫“老爷”,很奴性的。
世事如棋。几十年过去了,不少事物已成为明日黄花。就拿“先生”的称谓来说,似乎也蜕化成一个极老派的词语,古色古香的。时下,时髦的称呼是“老板”、“帅哥”。最有韵味的是把丹田之气压迫得尖尖细细的,托着长腔,嗲声嗲气地喊一声“哥哥”,其功效更是妙不可言。见过几多略有点姿色的女子,操此利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无坚不摧。
那么,我为什么还称呼孙麟作先生呢?这是掂量、斟酌了许久的结果。孙麟是在做实业,且规模不小,可他为人儒雅,不见铜臭气,叫他老板,似乎有点词不达意。叫“帅哥”,亦非我辈张口就来的事,这里面有不少分寸和讲究,和他的身份,也实不相称。那么,叫“哥哥”便更不合适了,一是孙某人不是花花公子,二是我辈缺乏先决条件,根本不值得考虑。有人建议,称他为孙麟同志,当即遭到否决,谓:“他又不是政治局委员,太严肃了。”故,只好叫他先生。老派是老派了点,仔细研究,尚与他的气质相当,也就将就了。
我和他认识的时间不长。之所以要写写他,缘于这个人很值得一写:不俗。在一个流俗泛滥的时间段里,不媚俗,特立而独行,要的是赤子之心。这,是一般人极难做到的。我见过一些政治上、经济上的暴发户,满脸油光,瞪着眼睛,张牙舞爪的,实在令人悲痛欲绝。有点势,有点钱,完全是你自己的事,非要像放屁一样排泄出来,污染大众的空气,挺不道德的。
孙麟不这样。有君子风,有儒生气,有骑士味。和他接触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个有见识的人。所谓见识,该是对已知事物内涵精确而独到的把握。说直白一点,就是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个名叫孙麟的先生正在研究庄子,还颇有心得。这,很令我肃然起敬。我以为,在美学家的眼里,庄子是一种美学传统的开辟者,他给我们所展示的,是一种大美,至美。孙麟从事的事业似乎与美学无关,那么,他从庄子的学说里,享受得更多的,可能是自由之风的吹拂,是那种对人生大境界纯理性的精确思辨。我想,一个正在从事实业的人,在创造价值的时候,不唯利是图,能够跳出三界外,注视着另一个深邃的领域,与那只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扶遥而上九万里的大鹏对话;听庄子与惠子流传千年的濠粱之辩,该是十分惬意的事。又想,在红尘滚滚的今天,将自己的思想放射出去,敢于与远古的智者对接,亦应该算得一个现代版的庄子。我只是这么想,可能没有很多道理。
和孙麟交往之后,才知道,他知道的东西还真多。可以说,上了研究那个层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话是老人家说的,对极了。但践行者稀,不少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一盆浆糊。孙麟不同,他从礼仪、读书、休闲,到生活、工作都有自己的方式,随心所欲不逾距。就拿喝茶这点事来说,孙先生能够从陆羽的《茶经》说起,细论红茶、绿茶、普洱、铁观音之别,上午茶与下午茶之异,楚之水与晋之水之高下,非得让你找到点两腋生风的感觉。这于我,却极难做到。我原本是粗人一个,食茶如草,只善牛饮,着实辜负了孙麟先生那套循循善诱的茶理。
这并不是说,孙麟干什么事都是如此精细。如果是那样,也就不是孙麟了。他是个有些经历的人,对什么八大菜系、法国大餐、日本料理等等,知道的肯定不少。但在非正式场合,他于此道并不刻意讲究。一次,我们一起在某个宾馆吃饭,点主食,孙麟要了一份大馒头,并要求服务员煮熟几个鸡蛋。把馒头掰开,夹入鸡蛋,双手发力,压扁,送进口中食之,极尽大快朵颐之态。我等观之,皆惊骇不已。试着吃了一回,以后竟成了保留节目。
没有去写孙麟事业上的事儿,他很敬业,也很投入。写出来,会是一本流水帐。要记,该是他自己的事。我于他所经营实业完全是门外汉,听他说起过,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只配把眼睛鼓起老大。不久后,他会在他工作的场所外开设一间茶座,取名“熬吧”。这很有些意味。熬在字典里的解释,是忍受的意思。而一个人铁心地要熬下去,就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气度和毅力。这是一种象征,有着深刻的寓意。有句话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孙麟的“熬吧”理念,无疑是他精神世界的展示。当然,我并不排斥在打熬的过程中产生的疑惑以及困惑。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无论从事业上,还是从年龄上,比较孙麟与我,这句诗尺寸恰好。这么说,给他戴顶先生的帽子,尺寸亦差不到哪里去。那就双手奉上。见笑,见笑。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