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唐纳蒂契:我们渴望纯朴原始的作品
作者丨卓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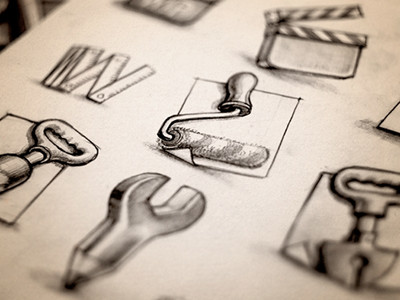

约翰·唐纳蒂契2016年9月来中国参加“残雪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这个人就是运气好,一来就有故事。那天半夜我去机场接他,阴差阳错没有碰上面。后来他都不知该怎样形容当时的心情,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银行卡被ATM机吞掉,站在黑暗中,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幸好机场工作人员给他找了个顺风车。他汉语只会说“你好”、“谢谢”,司机也只会Hello、Thank you,两个人鸡同鸭讲,结果他被送到麓山通程(会议是通程国际酒店)。我在河西找到他时,他像看到了救星——他的钱包丢失了。过程复杂,说来话长。那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第二天一大早我同他一起到机场,费了一些周折,打听到了昨晚的司机,司机正在自家小区门口吃米粉,听说老外钱包可能落在他车上,丢下碗筷一路小跑就去停车场,一只杏黄色的皮夹子还躺在后座上。约翰说要好好感谢司机,我说司机已经走了,他捧着心爱的钱包捂在胸口感慨不已:“这要是在纽约,根本不可能。”
约翰是耶鲁大学出版社社长,同时他还是一位作家,他出版了两本著作,长篇小说《变奏曲》和《镜子里的婚姻》。近年来他开始关注中国文学,中国作家残雪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情人》201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约翰是这本书的编辑,《最后的情人》获奖与约翰的推动有关。目前,中国文学在英语国家的影响还没有人们预期的那样好,中美文化交流较过去更加频繁,但文学的传播和沟通却不如其他热闹,中国读者对美国当代文学知之甚少,除了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等作家,美国新文学离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远。同样,中国文学对美国读者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从约翰那里得知,美国文学现状也并不乐观,新生代作家的创作缺乏生命力,随笔和非小说类写作成为潮流。读者和市场特别渴望纯朴原始的作品。
他对中国文学的期待但愿像他的中国之旅那样传奇精彩。以下是笔者对约翰·唐纳蒂契的访谈。
卓今:残雪在美国一共出版了7部作品,早在1989年,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她的《苍老的浮云》,之后,又有很多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书,像新方向出版社,鲁尔大学出版社,霍特出版社,罗切斯特大学出版社。除了日本,美国是出版残雪作品最多的国家。美国读者喜欢这种纯文学作品吗?
约翰:这个问题好。我认为残雪十分注重原创,所以她和世界上其他作家不一样。我们懂得其作品的纯洁、原创与新鲜,所以知道它们与其他任何作品完全不同。美国读者中有人喜欢先锋作品或者说实验性作品,但是有趣的是你刚才提到的出版社都是大学出版社和规模很小的独立出版社。大的商业出版社是不碰这类作品的。你说的出版社真的很小或者是敢于冒险的大学出版社和独立出版社。
卓今:2009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了她的《五香街》,当时你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吗?
约翰:是的,当时我在。有意思的是,关于出版这本书,确切地说不是在1999年,我们是后来才决定的。大约是2003年或者04年。05年没有出版,我有印象了,应该是2003年。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因为美国不擅长出版来自其他国家的翻译作品。通常我们出版的都是我们美国人自己写的书。过去我国一直做出口的,不太做进口。我记得我到耶鲁来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可以募集到一些资金用来做点有益的事和做点一些好书。当时我就想可以出版一些其他国家的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们出版了阿拉伯语的翻译作品,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9种不同语言的作品译过来了。残雪是我们翻译的第一个中国作家,也是唯一的一个,我出版了她的两本书《五香街》和《最后的情人》。我们还有她的另一本书,也会在耶鲁出版,现在在等我们的翻译完稿。对于我们来说,要确认美国人是否比过去更具全球化、世界性眼光,这一点很重要。尽管我们是个移民国,但是你知道我们基本上只出版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个说法是美国每年出版的翻译文学不到出版总额的百分之三。那是很可怕的。
卓今:《五香街》的编辑是你吗?
约翰:那本书的编辑是乔纳森·布莱特。新书《最后的情人》的编辑是我。
卓今:你为什么想到要出版《最后的情人》?
约翰:我发现那本书华丽,充满野性。刚开始,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入它。好像之前我们谈到过一点点关于她的书很难读。我发现《最后的情人》是这样一本书,我一开始就抗拒它,是关于我自己的某种东西不想让我进入那个世界。我发现读起来确实不容易,但是到了最后我认为原来是自己的思想太封闭了,心没有打得开。我开始读,读着读着,突然就进入了那个世界。我不得不牺牲掉自己原来那些个正常的关于阅读的假设。我不得不放弃自己那些有关文学的正常不过的条条框框。我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英语教师、一个教文学的人所接受过的那些训练,去接受一种新的美学。我承认自己当时很兴奋,非常兴奋。因为我想,为了到达那里,我得成长。大约读了一百页到两百页的时候,我决定顺着她走了,我获得了与她的某种关联。我没有做梦因为我知道我当时很清醒。人们说读书有时候像是在做梦,但是我当时很清醒,没有做梦那种感觉。我感觉自己很轻,很清醒,很激动,对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有感觉。所有你知道自己努力要做的就是要创建这么一个世界,这很有意思。有个声音在说:过来,到我这儿来,你的思想就向她走了过去,然后就有了这种令人惊奇的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流,读者与作者的交流。我认为这就是她在写爱情的时候想要表达的东西。爱就是对某个人的呼唤,是要伸出手去,去改变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在另一个不同层面对存在感的觉知和对不同层面的事物的理解。这很刺激。
卓今:残雪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得美国最佳翻译图书翻译奖的中国作家,我知道,你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有一个很严格的评价系统,所以,这个奖在美国影响很大,很多作家和出版机构都想角逐这个奖项。残雪又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想一下她在美国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约翰:已经有影响了。我认为美国的年度最佳翻译图书奖有影响力,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读她的书。谈她的作品的批评家也更多了。在美国和英国都有很多批评家关注她。去年春天我在伦敦的时候和博伊·托金谈残雪。他是有名的文学批评家,他说他也很喜欢她的作品,还说也许我们需要引导英语读者读残雪,他们怎么读残雪也需要培训。她还入围了2016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在美国这是一个声誉很高的奖项。因为《最后的情人》,所有的事情的发生了,就在一年之内,实在令人激动。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这种能量,知道她的事业正在成长。
卓今:她今年在英国伦敦也拿了一个奖,叫?
约翰:英国独立外国小说奖。
卓今:对。您如何评价这本小说?《最后的情人》看上去描写的是爱情故事,但实际上它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爱情故事。她作为一个中国小说家去触摸西方人的灵魂,然而,对中国读者来说它看上去又像一个令人费解的梦。基于这个原因,美国的读者是否会感到更亲切?这部小说塑造了很多人物,乔,乔的妻子玛丽亚,乔是玫瑰服装公司老板,这家公司看上去好像是开在西方的叫做“A”国的某个地方,还有其他人,像橡胶种植园的老板里根,东方女性埃达。您如何评价这些人物?
约翰:这个问题问的好。因为现在有很多评论家不喜欢有些作家原本不是用英语写作,可是爱假装自己的写作是面向全球市场的。所以在他们的头脑中,要么是美国的某个的地方,要么是加拿大、英国,世界上所有说英语的地方。我相信文学本身应当对它的本土文化保持一种真实。我认为残雪在这一点上很聪明,因为她写的既是A国也是B国。到底是什么国?没人知道,这是一个虚构的国家。不过请记住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她谈的不是具有中国人特质的,而是人性的,全世界全人类都具有的一种人性的冲动。我认为她的那种方式很成功。
卓今:另外,刚才你谈到残雪已经入围2016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并且已经进入最后一个环节,排名靠前。这个奖在全球享有盛誉,被称为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诗人多多曾经在2010年获过此奖,时隔5年,您认为这个奖会颁给中国作家残雪吗?
约翰:希望如此。显然我没有办法掌控这件事,不过,如果我是评委,我会投赞成票。但是确实,你说得对,这件事很令人激动。照他们的说法,“纽斯塔特奖”是另一个“美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它与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有大比例的对应。这两个奖的得奖者有很多是相同的。所以说这是个好消息。
卓今:她入围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终审环节与之前获得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有内在关联吗?我的意思是,是否有可能,她获得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后受到更多批评家的关注?
约翰:我想因为这个奖,所以这些评论家,还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读她的书,认识她。更多的人有了这种意识。你知道一个人事业之所以变成了事业是因为其他人注意到了它,所以它本身具有一种动能。我很高兴这些事一年内都发生了。这特别好。
卓今:你能预测一下吗?
约翰:很快了。我想是十一月份或者是明年春天,或者是接下来的六个月之内。我不知道具体的日期,我可以查到,但是现在不知道。
卓今:曾经有很多美国作家的作品传播到中国来,很著名的作家像马克·吐温,威廉·福克纳,艾米莉·狄金森,厄内斯特·海明威等,但是现在,近二十年来有哪些优秀的美国作家?中国读者不了解他们,你能介绍一下吗?
约翰:好的,我可以说说我喜欢的作家。我最喜欢的小说家是唐·德里罗。他是一个极出色的作家,写的是妄想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他的作品特别精彩。当然也有作家和他完全不同,玛里琳·鲁滨逊写温柔的作品,都是在19世纪的故事。还有一些随笔作家,我认为他们都写得很好,例如莱斯利·詹姆士、玛吉·尼尔森。乔·弗朗茨很受欢迎,他写很现实主义的文章,不是实验性写作。
卓今:唐·德里罗,他写哪一类型的题材?有爱情吗?(约翰的大会发言题目是“残雪,爱的难度”。)
约翰:我认为唐·德里罗写的不是爱情故事。在小说中,他更多的是采用文化批评的手法。不过爱情依然是个很有意思的尺度,这个问题好,我过去没想过:还有谁还在写爱情故事?
卓今:你能谈一谈美国的文学现状吗? 跟二十世纪比它是更有活力了还是也在衰退?
约翰:很有意思。我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大量的作家走进了大学甚至研究生院攻读艺术硕士学位,这对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现在这些小说家不论是写长篇的还是写短篇的,都以小工作室的形式进行紧密的合作,以确保作品的纯朴原始。你知道,现在所有的文章写得很好,而且经过了很挑剔的审查,但是你感觉不到其中生命力,生命力是缺失的。这是因为这些都是年轻人没有太多的经历,他们用很漂亮的散文写自己的空间。在此之前的那一代当中,有很多其他畅销小说家,例如梅洛、贝罗、布罗特。他们让沮丧的情绪、战争、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历史时刻在小说形式中穿行。有时候,我觉得现代的小说里压力太多了,太伤感了。不是基于现实世界,而是以作家自己的感受即他们自己那个小小的世界为基础的。还有就是,现在很多文学写作者更加倾向于写一些随笔和非小说类作品。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一些最好的小说家,作品里包含了很多哲学、历史等等非小说的元素。我认为人们喜欢W.G.赛波特,他是个好作家,他所有的作品里都有大量的研究和图片,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会感觉自己在读一本自传、一本回忆录,同时也是小说,也是历史。
卓今:哪些外国小说在美国比较受欢迎?
约翰:很有趣,去年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蒂亚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出版了他的作品,今年出版了他最新的三本书。因为他获得了诺奖,所以大家都来买,销量特别大,所以很好。我仍然认为美国人读得最多的还是美国人自己写的书,第二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再就可能是法国、德国、欧洲中部国家、意大利。现在还有一位很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艾拉·叶莲娜·弗朗蒂,她是意大利人,写系列小说,她的书很受欢迎。
卓今:有亚洲作家吗?
约翰: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也受读者喜爱,很受欢迎。
卓今:你既是出版家又是作家,我曾经想买一本你的小说《变化》(Variations),但是亚马逊网站显示“该商品暂时缺货”。所以我没有读到这本小说。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约翰:我在想是残雪鼓舞了我。她告诉我她每天集中精力写作一到两个小时。我想我也能做到,所以现在我开始写了。你知道我要工作,很忙,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以上。现在我每天早上五点钟醒来,五点到七点半我就写,写两页,只写两页,然后就停下来,给自己留点点东西,以便第二天接着写。这实际上是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主意,他说别写完,在你要写完之前停下来,给你自己留下点东西明天再吃。这就是我的做法。我完成了一本,是对婚姻生活的一本回忆录。第二本是个有趣的实验,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是要写一本关于音乐的书,不是小说。我最喜欢的音乐中有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是一支优美的钢琴曲。传说18世纪,巴赫在德国莱比锡城的一个教堂里当作曲家,一天晚上,一个著名的伯爵,想睡又睡不着,所以他让巴赫为他写一首曲子。巴赫就写下了这首曲子,交由哥德堡为伯爵演奏。这 就有了《哥德堡变奏曲》。我当时想,历史是这样有意思,因为现在,很多年以后,小小的催眠曲风靡全世界,成为了每个钢琴专业的学生的必学曲目。这就是音乐理性主义中的极大极小的象征。这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所以写写沉寂在历史中的过去的迷,介绍音乐作品的来历是很好的事。我就是那样的想法。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研究,我要做的就是虚构一位钢琴师去学习去思考这些问题。有一天一位钢琴师为了在合唱团谋得一个职位,走进了一座教堂。他们需要一位牧师,从那一天开始,牧师主导了这本书。我并不打算写这个牧师,我不想写牧师。这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想象力掌控了这本书。从那天起,我的书变了样,整个儿就是重写了一遍。
卓今:听起来特别有意思,有点实验性的味道,一定要买一本来看看。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多亿人的大国,有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你有没有打算将你的小说在中国出版?
约翰:如果有人愿意出版它的话,我很乐意接受。我很高兴它能在中国出版。
卓今:中国读者在二十世纪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很大,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包括美国文学。你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主要是诗歌、散文,这个现状在四百多年前有所改变,一部叫做《金瓶梅》的长篇章回小说打破了这个传统,中国的叙事小说开始发展。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的引入,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中国作家丰富了小说这个文体。中国读者一直热爱阅读外国文学,也愿意学习外来文化。美国人目前也有强烈的愿望了解中国文化,你们出版社之间多一些互动应该会促进两国文学的交流。
约翰:是的,希望如此。
卓今:中国文学在美国的情况怎样?
约翰:很遗憾,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的并不多,包括像《红楼梦》这样的中国经典。确实我们有很多不错的华裔作家。但是对于我来说,要了解中国的当代文学,途径很有限,其中残雪是最引人关注的一位。
卓今:哪些中国作家在美国比较有影响?
约翰:我想现在是莫言,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几年前,人们也读艾未未,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他的书。还有一位姓刘的诗人。
卓今:耶鲁大学出版社是美国著名的出版社,听说在伦敦还有分公司。自从残雪在美国受一到关注,有没有考虑更多地引进中国作家的作品?
约翰:我想,因为新近的这几个大奖,还有新的翻译作品和更多的评论文章,残雪的事业会 上升。当然,我还想认识其他中国作家,并翻译他们的作品。如果你认为有好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值得在美国出版的话,请一定为我推荐,我会一直等待。
卓今:好的,中国有许多优秀作品,我回头给你推荐一些。美国读者更倾向于阅读哪种类型的作品?
约翰:美国读者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家?这个问题,我想美国读者的阅读口味,区别很大。因为我们有很商业化的作家群,他们写很感性的作品。从事这种商业化写作的公司很多很多。现在最畅销的是非裔美国作家科茨的书,这些书表达了一种愤怒,这种愤怒源自非裔美国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有黑人总统奥巴马,可是美国的种族关系依然问题很大。所以例如托尼·莫里森这样的作家,很多书都是写美国的种族关系。我们是这样一个多样性的国家,由很多不同的人组成,有很多书在谈拉美人、墨西哥人和黑人。我们是一个国家,但是有很多不同的人。这是一件需要我们考虑的有趣的事。
卓今: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最敏感最尖锐的话题,这类题材令人感到兴奋,但对写作者来说也有许多雷区,要格外小心。也就是说,除了热点社会问题,实际上关注纯文学的人并不多。
约翰:是的,读的人很少。只有小出版社在做。
卓今:中国古典文学在美国的传播怎么样?据我所知,《红楼梦》的英文版本现在很多,过去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在他们之前和之后也有无数的译本,很多译本都是采取“归化策略”进行翻译,生怕接受语方看不懂,通俗化、漏译、改译的情况是有的,美国对这类经典的翻译和出版是个什么情况?
约翰:有趣的是,我并不认为《红楼梦》有很好的译本在美国出版,因为这是一本巨著。我想即使是这样的巨著,只要是真的好译本的话,公众也能够接受。因为到现在能懂经典的话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们最了解的经典应该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现在我们开始转向翻译南部印度的经典了。所以我要做的就是集中注意力进行经典著作的保护。
卓今:经典都内涵丰富,信息密集,构词复杂,语言具有多义性,翻译起来很难,这一点加大了传播的难度。
约翰:是的。经典著作翻译起来非常难。
(本文原载《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4期)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