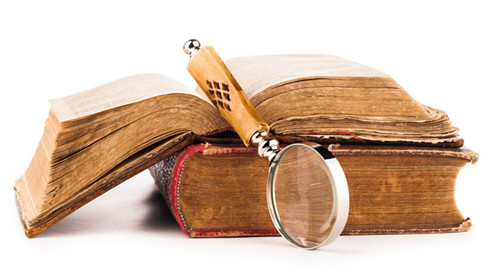
作 家 之 谓
文丨刘永学
我一位朋友,在一家企业谋饭,事业风生水起,人们均称之为企业家,每当呼声响起,此公便笑靥如花。想想,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为过从甚密,彼此间交流口无遮拦,我随行就市,亦以企业家称之,朋友并不谦让,一并欣然笑纳。只不过他是来而不往,对我这个以码字为业的人从不投桃报李:“我是企业家不假,但你不是作家,顶多是个作者。”这个观点虽说掷地有声,确实还存在着语病,因为谁只要动笔,都是当然的作者,“顶多”二字显然是蛇足。尽管如此,若干年来他一以贯之地秉持着略带瑕疵的理念,无论外边是风霜雨雪抑或柳绿桃红,从未影响过他对确定我顶多是个作者地位的坚定信心。
我并不想与他争论,一则没有意义,二则他说的也确实无大错。作家的称谓,至少在中国一度曾经炙手可热。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是一拨高潮,到了文革期间反对成名成家,热度降下来了。物极必反,八十年代随之迎来了一轮强劲的反弹,各类顶着作家头衔的人物如过江之鲫,洋洋大观,至今还让不少人难于释怀。只不过,三月桃花汛,毕竟会随波而去,随着国人价值取向的多元与分流,明星歌手、达贵显要逐渐占据要津,时代的聚光灯不仅仅在作家这个群体聚焦,不少人梦醒时分,摸摸昏沉沉的脑袋,头上的光环不翼而飞,眼前的一切顿时显得空空荡荡。
这种对貌似神圣的稀释是一次拨乱反正,也是一次正本清源。作家之谓,指的是以写作为业的人,其核心要义特指文学创作上有成就的人。相对于"作者"而言,"作家"一词的有着更为丰富与厚重的内涵。阿城才出道的时候,一篇稿件被《作家》刊登,接下来就有不少人称其为作家。阿城惶恐,云:“成家极难。首先,要是一种劳动;再能将劳动的量变为质,通规律,成系统,有独创,方能成家。”这话讲得很透彻,给什么是作家作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这么多年以来,自己虽然写下了一些文字,亦有飘忽其然、云里雾里、犯犯迷糊的时候,但夜深人静之际,对照着阿城的话参照参照,醍醐灌顶,自会保持一份冷静和清醒。还是那位朋友说得好,我就是个作者,以消遣文字为乐,至于刻意成为什么“家”的事,于我无涉,那是另外一个江湖。
至于什么人能称之为作家,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会心中有数。吴承恩、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当年写作的时候,无论是庙堂还是民间,都没有作家的称谓,但是,伟大的作品都是有神性的,神性的力量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它是永恒的光源,会给一代代人予恒久的抚慰与温暖。故而,当作家的称谓在中国甫一落地生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这四个杰出的文人,并且在作家的前面还冠予了“伟大”的副词。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写作就是写作,绝对不是为了这个数百上千年之后才出现的“家”的称谓而呕心沥血。近代如一大批民国才子,还有我们熟悉的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等,都把笔下的文字当做一项温暖的事业来经营,专注于倾诉和表达,以此来养活一团春意思,至于头顶上作家的桂冠,似乎是由作品而衍生的附加值,他们本人,对此是并不以为意的。
照理说,这一切顺理成章,所谓作家,必须以作品来昭示自己的存在。不过,我们切不可忽略一枚硬币存在着两面,亦不可小觑了因变异而导致了变种的出现。如今,作家这个词很多时候被用作为一种客套敬称,或被当作了一种提高某人身价的标签,其厚重的内涵逐渐被蛀空,蜕变成一只艳丽的气球,随风轻飏,让人们难于承受其分量如此之轻。我还是要提到前面所说的那位朋友,每年都有一些自称作家的各色人等向他推销那些注水猪肉似的小说以及如快板书一般无二的诗作,这令他得了作家恐惧症,一听到有什么“家”前来拜访,恨不得多生出几条腿来,落荒而去,退避三舍。
很费了一些时日,我仍然想不清楚那些火候不足而一心一意偏要成“家”的人到底是逐名还是逐利。若是为利而来,真犯不着去当作家,放眼看去,真正指望着当作家能发财的概率小而又小。那么便是为了成名无疑了,可选择的这条路去求名几乎与缘木求鱼无异,误己误人不说,百分之一百还会把笑柄留在世上。还是阿城通透练达:“人们常常说的成名成家,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成名很容易。去卧一次轨;飞起一砖,击碎商店玻璃。总之,造成社会同情或搅扰乱治安以及产生种种社会影响,你便成了名,令人挂在嘴上。”这主意虽说一试就灵,深究起来还是有些后顾之忧,一是没有必要为了虚名去慷慨献身;二是有点涉嫌违法的嫌疑。如此一来,阿城的办法只能仅供参考。确实,参考参考而已。
(写于2016年5月15日)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