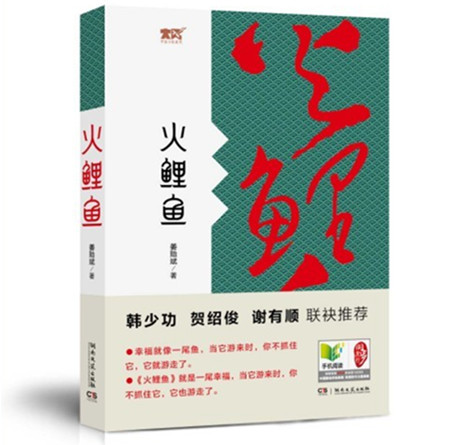
火鲤鱼(长篇小说)
作者丨姜贻斌
春 分
草鞋烂了四根索,耳子坏了不跟脚。
情妹死了不闭眼,挂牵情哥打赤脚。
——情歌
一
雪妹子曾经想过,去找找水仙和银仙,毕竟都是渔鼓庙的人,在这遥远的地方乡情还在,凡事也有个商量。而茫茫人海何处寻觅?她很想找到她们,然后,把痛苦一页一页地翻给她们看,细细地向她们诉说,请她们出主意帮帮她,寻找那个叫张一民的狗男人。当然,这个念头只在她头脑里闪一下就过去了,像狂风把纸无情地刮走,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她为什么打消这个念头呢?难道她不准备找她们吗?
是的,雪妹子不准备找她们,即使找到她们,又怎么说呢?难道说自己还没有嫁人就是为了报仇吗?她们如果不理解,会瞪着眼睛惊讶地看着她,然后,张开嘴巴大笑,哎呀,你这么大了,还没有嫁人呀?你看我们的崽女多大了?如果理解她的,她们会劝道,不要再生杀人的念头了,那是要偿命的,何苦呢?再说,女人谁没有吃过一点苦头呢?——那么,自己多年来的苦苦等待和寻找不是一场空么?
在遥远的新疆,雪妹子觉得最亲近的人并不是邓之来,而是湛之中,虽说他俩并没有多少交谈。她觉得湛之中的眼睛很厉害,似乎一眼看穿她内心的秘密。仅仅凭着这一点,雪妹子觉得跟湛之中有一种亲近感。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很像二哥。
她见过湛之中的婆娘,那是一个乖态的女人,鼻子高高,颧骨高高,像新疆女人。究竟是不是,她不敢肯定,却肯定不是南方女人。他们有个四岁的崽,叫文军,虎头虎脑的,第一次见面,就清甜地叫她阿姨。湛之中的婆娘姓任,水色很好,也笑笑地跟雪妹子打招呼。雪妹子叫一声任姐,然后,就分手了。
那次,雪妹子是在大街上偶然看见他一家人的。他们已经走远,雪妹子还呆呆地未动,很羡慕他们。她想,如果跟二哥成了家,恐怕也有这么大的崽了,也会全家人高高兴兴地上街。想到这里,雪妹子的心情低落起来。
她很想去他家坐坐,感受家庭的温暖。对于一个飘在他乡的人来说,那种温暖能够冲淡人的孤独。油盐酱醋茶,锅盆瓢碗勺,床柜箱桌椅,衣帽裤被毯,温暖的火炉,呛人的油烟,亲人的细语,会让她想起渔鼓庙。
她没有去过湛之中的家,来到新疆,还没有到任何人的家里坐过,除非帮人家操办婚事时才去人家的洞房,以后就不再去了。不像在渔鼓庙,你如果想去谁家,双脚随时一尺,就能够跨进谁家的门槛。在这里,一切都不像在渔鼓庙那样随便。别人没有邀请你,你去是什么意思呢?肯定会引起别人的误会。即使某个男人欢迎你去,人家的女人就不见得欢迎你。比如说,湛之中的女人就没有邀请她去。况且,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稍不注意,就会有大祸临头,谁愿意自寻麻烦呢?
雪妹子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她不明白那个家伙躲在什么地方?她几乎把乌鲁木齐大街小巷的人都看熟了,也没有见到那个家伙。她还到郊区找过,虽然离城里不远,郊区的荒凉却令她目瞪口呆。好像觉得自己莽撞地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影子也没有,说不定就有野兽突然冲过来,把她撕个粉碎。她打了个哆嗦,匆忙往回走。
难道张一民是个流窜犯吗?如果不是,他是不是故意在跟自己捉迷藏呢?如果是,那么,这个家伙真是害人不浅,睡过她一回,却害了她一辈子。
也许他就躲藏在她的房子附近,一个她无法看见的地方,他却能够看到她,看到她在枉费心机地寻找,看到她在哭泣,看到她的焦虑和烦躁。看着她满怀仇恨地寻找,说不定他在偷偷地窃笑呢。也许,还有很多次他就从她身边走过去,她却没有注意。她不晓得这不可多得的机会,就这样从她身边溜走了。
雪妹子还在住房的四周查看过,周围有许多房子,那些窗子一律沉默地对着她的房子,她决心把窗子里的人全部查清楚,以消除心中那个长久的疑虑。所以,那一向她没有去大街小巷寻找,希望在身边的那些房子里把那个禽兽不如的家伙找出来。所以,从那天起,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她都耐心地守着那些门洞,若无其事地远远站着,不让别人看出她的真实用意,她要看看到底是哪些人住在这里。为了避免重复,她还在纸上做记号,落实一家,记下一家。这个工作花费了她不少的时间,等到她把全部的人员查对之后,却没有张一民。
雪妹子怎么也想不通,张一民为什么不出现呢?他到底哪里去了?还在这个城市吗?难道她这些年来的苦苦寻找是白费工夫吗?
她做过无数的梦,在梦中她总是胜利者,她的报复行动都得以实现。她梦见在大街上商店里小巷中,以及电影院这些不同的地点,突然碰到张一民。张一民的确很狡猾,没有穿以前的衣服,有意地装扮自己,为了防备雪妹子。如果是冬天,他穿的是淡黄色的长大衣,戴着黑色的皮帽子,还戴上白色的大口罩,皮帽子和口罩的距离相当贴近,只给眼睛留下一条小小的缝隙,这的确很难让人发现。如果是热天,他戴着宽大的墨镜,掩盖脸上的那条刀痕,嘴唇上还粘着假胡子,一时也看不出来。
当然,这一切拙劣的伪装,都无一例外地被雪妹子看出来,她非常佩服自己尖锐的眼睛,一眼就看出他是张一民。她气愤地冲上去,把他脸上的伪装撕下来——包括皮帽子口罩墨镜或假胡子——然后,对着木然的张一民冷笑说,你还认识我吗?不等他说话,她唰地抽出刀子,一刀刺进他的胸膛,血顿时流出来,那是黑色的血液。张一民倒在地上,血液慢慢地流开,像一桶墨水涂在地上,令人们惊骇不已。谁也没有上前阻止她,或来抓她。人们听说他是个坏人,纷纷说,哎呀,该杀,该杀。听说雪妹子多年来在寻找这个家伙,人们流露出无限的钦佩。然后,雪妹子收回血淋淋的刀子,在他的衣服上擦了擦,从容地离开。
睡梦中的刺杀,只有一次很不顺利。
那是在大街上,张一民远远地走来,没有发现雪妹子就在自己身边。她突然喊张一民,张一民还以为是哪个熟人,当雪妹子撕下他脸上的伪装时,张一民大惊失色,慌乱地拔腿就跑。
她哪能放掉这个难得的机会呢?她拼命地追赶。他们从大街上钻进小巷,又从商店窜过,然后,又钻进公园,雪妹子紧追不舍。张一民像狡猾的野兔子溜得飞快,他大概明白报应终于到来,今天小命已经保不住,万分恐慌地奔跑着。雪妹子在后面紧紧追赶,同时,也惊讶自己的力气和速度。她跑得十分轻松,一点也不吃力,却老是追不上他,心里暗暗着急。又想,自己既然跑得不吃力,那么,就让他跑吧,不管他跑到哪里,跑多远,她都有把握让他死于刀下的。
他们从上午跑到下午,又从下午跑到太阳落山。这时,城里的人几乎都出来了,看着他们发疯似的奔跑。有些人还不停地喊加油,也不知是给张一民加油,还是给她加油。总之,那些喊声的态度非常含糊。
后来,他们跑到荒凉的郊区。这时,晚霞满天,天空高远,那是一幅令人感动而温暖的图画。在这幅美丽的图画里,却发生一场激烈的生死追杀。雪妹子手中不断晃动的刀子,反射出晚霞的斑斓。
跑着跑着,张一民终于没有了力气,一下子瘫倒在地,像一只疲倦的狗,似乎连喘气声也没有。一身汗水的雪妹子匆匆地跑上来,一脚踩在他胸脯上,愤怒地说,你也有今天?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今天,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追上你,你这是罪有应得,明白吗?
然后,弯下腰,刀子在张一民憔悴苍白的脸上刮了刮,说,你怎么不说话?你躲得过昨天能躲过今天吗?你明白不,老娘寻你好几年了。
张一民闭着眼睛,不吱声,脸上充满着恐惧,脸皮在不停地颤动,明白今天已是死到临头。所以,放弃了抵抗和努力,让死神来光顾他。雪妹子吼叫着,你睁开眼睛看看老娘。张一民的眼睛总不睁开,也许不愿意看到愤恨的雪妹子,也许很惭愧,不愿意面对自己败在一个女人手里。
雪妹子拿刀子轻轻地挑了挑他的眼皮,眼皮害怕地眨了眨,又闭上。你害怕了吧?你那年睡我的胆量哪里去了?雪妹子心中积压的痛苦和仇恨全部涌了出来,举起雪亮的刀子,一刀刺进他的喉管。鲜血突地喷射出来,那血也是黑的,跟黑色的荒凉大地融为一体。
这个梦时间最长,也最惊险刺激和担心,她担心张一民跑着跑着突然不见了。梦醒之后,雪妹子满身大汗,手里竟然拿着刀子。
雪妹子来到新疆之后,没有向家里写过一封信。写什么呢?难道写自己在这里混得不错吗?难道写自己到这里遭遇了强奸?难道写自己一直在寻找那个强暴她的仇人?难道写自己最终要杀死那个男人?
她觉得,信终究有一天要写的,却不是现在,现在还为时过早。
二
寻找四年之后,雪妹子终于绝望了,明白这个仇已经无法可报。
这些年来,湛之中仍然跟她保持着一种不亲不近的关系,有时候,仍然对她说那句话——我晓得你有心事。每次听到这句话,她就想抱着他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想让他搂住自己睡觉。
那天,雪妹子被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念头所惊讶。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念头,为什么以前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呢?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呢?而现在,却突然有了呢?她没有自责。自从有了这个想法,她反而平静下来,她的确想跟湛之中睡觉,这是她心甘情愿的,她要尝尝人间的快乐。以前,张一民使她尝到的只是痛苦,只是仇恨,只是泪水。现在,她要好好地品尝品尝,也不枉在人世间走一趟。
她终于放弃寻找。
现在,她开始注意跟踪湛之中,发现他住在离厂里不远的一栋平房。从厂门往左手走两百米,然后,拐进一条小街,再进去五十米,就到了他的家。那是一排陈旧的房子,像老人脸上粗糙的皱纹,她甚至闻到旧房子散发出来的衰老气息。她本来是想约他出来的,只是哪有合适的地方呢?再说,如果人家不愿意去呢?
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他的妻儿回老家探亲。这是她亲眼所见,看见他送妻儿到火车站,一个人就回家了。
那天晚上,湛之中回到家里刚洗完脸,门就轻轻地被人敲响,打开一看,怔住了,是你?
雪妹子微微地点点头,也不等他说话,大方地走进来,然后,小心地把门关上。
她站着看了看屋子,那是一室一厅,屋里的摆设相当简陋,普通的桌椅床铺,连漆也没有刷,白水货。桌上黑色的小闹钟,在单调地嗒嗒地走着。旁边还摆着一个特大的瓷器像章,起码有半个脸盆大。
湛之中惊愕地请她坐下,泡茶,然后,说,你有事么?
雪妹子摇摇头,又点点头,那是叫人捉摸不定的含糊复杂的动作,湛之中搞不清她的来意。
很快,湛之中冷静下来,坦荡地说,我一直说你有心事,不知说对了没有?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雪妹子抬起头,定定地看着对方,说,你说对了,我是有心事,你想了解吗?
湛之中坐下来,急切地说,那当然。
雪妹子微笑着说,不瞒你说,你很像我的第一个恋人,虽然他不爱我,而我为了爱他,把一切都抛弃了。没想到,在这里又碰上一个像他的男人。她看着湛之中,话说得很简洁,却没有说出苦楚的内心和报仇的秘密——她觉得这些年太痛苦太疲惫,她不想今晚让自己过于痛苦和疲惫。
哦……湛之中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原来如此,我还是猜对了,是不是?他显然有点得意。
是。雪妹子喝口茶,觉得茶很香,口腔里充盈着浓郁的香味。
湛之中也想喝茶,准备起身拿茶杯。
雪妹子却说,你不要拿杯子了,喝我这杯吧,不是一样吗?来,让我喂你。
没有等到湛之中回过神来,她就把茶杯送到他嘴边,他扭开脸想躲避,雪妹子却把茶杯贴住他的嘴唇,他很被动地张开嘴巴,慌乱地喝一口,紧张地朝窗子看一眼。
雪妹子收回杯子,笑着说,你不要这么紧张,没有谁注意我们。
湛之中这才似乎明白雪妹子的来意,自嘲地说,我不紧张,不紧张。
雪妹子挑逗说,我问你,你还记得我们认识的那天是什么日子?
湛之中想了想,说,我记得,3月20号,春分。
雪妹子高兴地说,说得对。哎,你真的不紧张吗?那你把灯关掉。
湛之中怔了怔,然后,啪地关掉灯。
那个晚上,雪妹子简直像一只饿坏的母老虎,一次不够,再来第二次,接着第三次。她不断地怂恿湛之中,让他不停地威风。她也没有想到,这个看来懦弱的男人在床上竟然这样厉害。这是她真正尝到的人间快乐,她的呻吟,她的快乐,她的泪水,她的扭动,好像在品尝一道肉欲大餐。湛之中却不晓得,她在心里呼喊的却是二哥,呼喊那个没有接受她爱情的男人。
那个晚上,湛之中叫雪妹子在这里过夜,她没有答应。她说,她并不是害怕。她说,她如果害怕的话就不会来了。她躺了躺,让疲软的身体恢复过来,然后,离开温暖的床铺,临走时,还在湛之中脸上打了个啵。
趁着夜色,雪妹子回到自己屋里,打开灯光,坐在桌子前,铺开信纸,拿起钢笔,开始给家里写信。她的脸上非常平静,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鼻子还在嗅着残存的男人气味,觉得那种气味很刺激,跟二哥身上的气味大体相同,能够让她毫不疲倦地写信。
这是她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她写得很快,思路像千里江河一泻而下,她没有给二哥写信。写罢,她看一遍,把信放在桌子上,用钢笔压住,然后,安静地上床。
她闭着眼睛静静地躺着,等待天亮。
没多久,天渐渐地亮起来,她已经习惯这里的天气,黑得晚,又早早天亮。她起了床,安静地洗漱和打扮,穿上当年去看二哥的蓝卡叽上衣,披领子,酒盖子般大的有机玻璃扣子。来到新疆后她就再没有穿过,把它压在箱底。
那天,她连头发也梳成当年去看二哥的那种发式,用橡皮筋把头发扎成两个翘翘。她在做这一切时,慢条斯理,一丝不苟。打扮之后,她看看这间住了几年的小屋子,又把那些熟悉的东西——床铺,桌子,凳子,脸盆,毛巾,镜子,梳子,等等——扫视一遍,眼里流露出深深的留恋,然后,毅然地走出房门。
街上已是吵吵闹闹,武斗的人们在喊着高音喇叭,嘈杂的声音冲击着人的耳膜,时而,还有枪声嗖地划过天空。雪妹子一点也不害怕,走过一条街,看到路边停着一辆农六师的汽车,那个粗壮的司机正准备出发。雪妹子紧步上前说,请他带她一截路。司机说,你去哪里?雪妹子没有说具体的地方,只说她想出城看看向日葵。司机微微惊讶地说,你就是想去看向日葵?雪妹子点点头。司机笑了笑,答应了。
有个女子坐在车上,司机的情绪显然高涨,说他是江西人,到这里十五年只回了老家一次。当他晓得雪妹子是湖南人,更加兴奋起来,说你们湖南有很多人是从江西过去的,当年湖南被血洗,地盘都空了,所以,江西人去了你们那里,你们喊我们江西人叫老表。
雪妹子只是听着,不太说话,眼睛看着窗外,望着茫茫无际的戈壁滩。
司机好像记起什么,说,你不是说去看向日葵吗?你如果到我们那里,向日葵才好看呢,一望无际。他说,他不怎么喜欢看,看多了,厌了。又问,你看了向日葵又怎么回来,她说拦车子吧。司机说,你要小心点,这个年月太乱。雪妹子感激地点点头。
车子开了很久,这时,窗外出现一片无边无际的向日葵,天哪,满世界生动的黄花,像在呼唤着她的到来。雪妹子非常激动,连声叫司机停车,她很感谢这位江西老表把她带到这里。
车子开走了,雪妹子望望连着天边的向日葵,想起家乡亲手栽培的向日葵。她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泪水突地流了出来。
她好像回到家乡。
整个世界似乎就她一个人。
她置身在无边无际的向日葵丛中。
然后,她慢慢地朝它们走去。太阳安静地照耀着这片美丽的土地,向日葵花也显得更加富有光泽。阵风吹来,向日葵跌宕起伏,像黄色的大海波浪汹涌。她没有走在向日葵中的小路上,径直往向日葵丛中走去,一股浓郁的熟悉的清香钻入她的心肺。
她不停地走。
终于,她站住了。
这时,她攀弯一棵高大的向日葵,摘下一盘,然后,平静地躺下来,把向日葵放在自己的脸边。
她的眼睛仰望着纯净的蓝天,白云偶尔飘过,她觉得蓝天白云离她这么近,似乎伸手可及。这时,她情不自禁地伸出一只手,朝天上摸一下,然后,抽出刀子。
刀子在阳光下闪烁着雪亮的光芒,甚至有点刺眼。她眯起眼睛,似乎在抵挡刀子耀眼的光芒。大约三分钟之后,她咬咬牙,刀子朝手腕上重重一割,鲜血顿时汩汩地流出来。一只手仍然拿着沾染鲜血的刀子,另一只流血的手平放在胸部上。她闻到鲜血的腥味,感觉到鲜血的热气和呼啸而来的奔腾。她还感觉到热血里饱含着的仇恨和绝望,这时随着鲜血流出来,铺满土地上,像黄色大海的向日葵中,充满着浓烈的血腥味。
她的嘴唇微微地动了动,轻轻地喊一声,二哥……
二哥,你听到吗?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