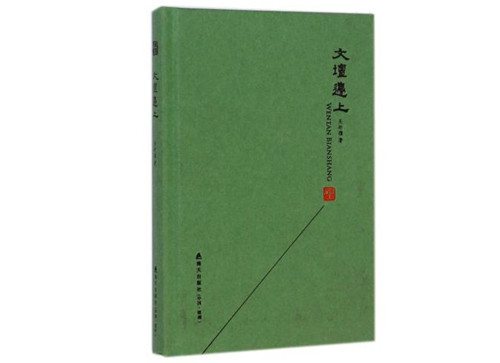
文坛边上·2012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12月1日 雨 星期六
今天是极其平常的一天,又是我人生中的一条重要分水岭。从今以后,从年龄上来说,我就无论如何不能算是“青年”了。但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把青年的那股激情和干劲保持下去,无论如何也要让青春的热血继续沸腾。
最近非常忙碌,大家都知道,“年关”到了。我算了下,上个星期,没有一天没开会。开会当然有必要,但开会带来的后遗症是很多工作积累起来了,一时难以消化。再加上我那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无论如何忙,书总要翻上几页,字总要写上几个。因为读书写字,看上去是让自己更忙了,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忙里偷闲呢。
青岛诗人沅茵寄来了她主编的《诗春秋》杂志2012年秋季版。我以前介绍过,这是一本办得很精致的袖珍杂志。那天我和沅茵在网上聊天,她说,杂志组稿正好是最后一天了,问我有何新作。我就一股脑寄了七首《古风》给她,她也一股脑将它们全部发了出来。《古风》是我今年诗歌创作的一个新尝试。每首诗取一句古诗,将古意翻新,其主题直指现实,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意义,或许会让诗歌更别致也更厚重些。
12月3日 阴 星期一
东莞第十届读书年会的盛况犹在眼前,又收到徐玉福先生寄来的《悦读时代》2012年第3期,其中有拙作《文友扫描(四)》。让人伤感的是,这一组“文友”全是在今年去世的,计有《见萧金鉴老师最后一面》《在这个春天,和两位诗人告别》《你我之间,莲花开过——纪念兴玲》。
本期写人的几篇,李树德写叶非英透露出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而林伟光写王金魁、朱艳坤写崔文川、汪应泽写李传新、董国和写曾纪鑫、陈巧莉写安武林,都有一种真切的在场意识,以“我”知人,写我知之“人”,让人知“我”。
其中,我对巧莉最为熟悉,因为她写诗,是诗屋的主要女诗人之一;她的散文诗和散文也写得细腻而优美。几年前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文字还显得稚嫩,可现在就当刮目相看了。她写的安武林先生是知名儿童文学作家、读书人,也曾是我们《初中生》的作者。
传新兄算是老朋友了,我和他直接交道并不多,只是在年会上见到,他寄过几册《崇文》杂志给我。他似乎抽烟比说话多,在东莞我们是交流得最多的一次,在玉福兄的房间,临别的最后一晚。他批评我没带萧金鉴老师的遗著去,我说我也在等萧老师遗著的消息,却至今杳无音信。他说,他会寄书给我,果然,今天就收到了他的大著《初版本》。
与西安的崔文川也相交有年,一直未见过面,他最近主编的《艺文志》乃民刊新贵。纪鑫和金魁,我都是在东莞年会上才结识的。金魁豪迈,喝酒牛气冲天;纪鑫儒雅,说话有条不紊。但他们都是智商情商双高的活跃分子。金魁创办的《书简》选点极好,据说他与国内五百多名各界知名人士有来往,收藏近万封书信和两千多册签名本,好生了得。纪鑫主编的《厦门文艺》我读过,文学性很强,纪鑫自己即是写作文化散文与报告文学的高手。
本期《悦读时代》另有袁滨、杨栋、夏春锦、易卫东、阿福的大作,特别是张阿泉采访民间出版家贺雄飞的《学习是一种信仰》,值得一读。贺雄飞先生研究犹太文化二十余年,一些犹太人的价值观深深烙进了他的心灵与行动之中。他掷地有声地说:“无论如何,我绝不能苟活,也绝不能浪费生命。”
12月5日 多云 星期三
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赢得一片叫好,加上刘震云又是我喜欢的作家,今天便抽空去看了这个电影。看了以后,微微点头,然后轻轻摇头。怎么说呢,不能说不好,也不算很好。《一九四二》比不过冯导自己拍的《唐山大地震》,也比不上艺谋兄弟去年拍的《金陵十三钗》。
首先,这部电影的演员都没有问题,无论是张国立、陈道明、徐帆,还是外国友人、获得过奥斯卡影帝称号的阿德里安·布洛迪,他们都表现出了不俗的演技。问题还是出在编剧和导演身上。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我没有读过,如果从电影反过来揣测,可能不会太好。线索复杂,枝蔓太多,贪大求全,以至于莫衷一是。刘震云在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就出现过同样的毛病。《一句顶一万句》上部神完气足,有诺贝尔奖的水准;下半突然松弛,赘肉明显增多,不知是怎么回事。
电影《一九四二》就是一身赘肉,虽然它讲的是一个饥饿的故事。张国立演的老百姓悲剧,与陈道明表现的帝王心结,这两条主线隔得太远,几乎不搭界,没办法就让一个外国记者两头跑。外国记者本是一个极好的观察点,是故事展开的最佳视角,编剧和导演却让他成了一名跑龙套的“联络员”。
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根本不要出现蒋介石、宋美龄、宋庆龄这些人,领导干部就到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打止。如果电影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为见证者,将重心全部放在1942年那场致三百万人于死地的饥饿上,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会儿想表现一场惊天动地的饥饿,一会儿想表现政府的无能,一会儿想表现日军的残暴,一会儿想表现军人的伟大,一会儿想表现中国人的内讧……如此多的主题,最终也削弱了电影中“饥饿”所产生的悲剧力量。
冯小刚说,《一九四二》是他拍得最好的电影。我觉得不是,但我对他还有信心,希望他最好的电影还在后面。
12月6日 晴 星期四
岁末,《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第6期隆重推出“散文专号”,向跌跌撞撞的2012年告别。“散文中国”专栏刊发了拙作《带你去见一个人》。
这是我今年夏天两次游历湘西北的实录,当然它不是一篇游记,而是岁月的回溯、情感的漫漶和灵魂的洗礼。很多人写过沈从文,但都不如他写他自己。“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一名作家的孤独让常人几乎难以理解,那是一处极难抵达的风景。但如果你能抵达,或者有幸窥其一斑,一定能感受到那种奇妙与瑰丽。我并不想写沈从文,我是把自己当作年轻的沈从文,或者另一个时代的沈从文,我是想重走那一段旅程,回到那个不算很远也不很近的年代。
责任编辑杨献平读到这篇散文时说:“你的文字有自己的东西了。”这句话当时让我怦然心动,它抵得过一篇万言论文。当然,正如沈从文所说:“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散文评论家王冰在《本期作品述评:燃起散文的灯火》说道:“吴昕孺《带你去见一个人》中写了神秘的湘西,写了在向西方行进中对于沈从文的迷恋与追寻,文字就如同他的行程,缓慢却充满意味和色彩。”
王冰说得很好,写作其实是一个虚化的过程——将一段实实在在的旅程虚化为意味和色彩,虚化为迷恋与追寻,虚化为另一个人与另一种生活。
12月7日 晴 星期五
网上介绍杨耕身是十个字:资深媒体人,知名评论员。应当是很精准的,他的具体身份是《潇湘晨报》副总编辑。上周,耀红跟我说,想请杨耕身来我社做个讲座。我就找复生搭这个桥,复生当然把这个桥搭得很好。于是,今天上午9点到11点,耕身兄便现身湖南教育报刊社,做了一场主题为“评论作为一种能力”的讲座。
越是现代社会,评论越加重要。评论,尤其是时政评论水准的高低,可以衡量那个时代的开放程度与文明程度。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评论,就不会有质疑和追问,社会的纠错能力与是非辨识度就会非常之低,低到只会盲从,甘于堕落,甚至不得不接受崩溃的命运。
评论是民众洞察力的体现,是社会良知的体现。我欣赏耕身先生温和而坚定的评论风格。温和是一种态度,一种自信同时也信任他人的态度;坚定则是一种意志力,一种向着常识与良知的方向不屈前行的姿态。其实,评论不只是媒体的事情,每一个公民都应有评论的能力,都应将评论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能力。温和而坚定地,站在这个时代的队列里。
中午,与名辉、新军、耀红、志华、敏华等一起,在留芳宾馆衡岳厅请耕身先生吃饭,复生因出差不能前来凑兴。闲聊才发觉,耕身真是一个极为温和的人。
12月8日 晴 星期六
自从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就一直在期待他的获奖演讲。今日凌晨,莫言终于走上了瑞典文学院的讲台,他演讲的题目是《讲故事的人》。
我没有看现场直播,通读莫言的演讲全文,我觉得文章还是不错的,比2000年高行健演讲词中那种急于表达不同政见的姿态要好得多。我看到网上有评论,说莫言演讲稿的文字不好。这不公允,莫言演讲的文字是很好的,很文学的。
问题恰恰在这里。如果要我说对莫言的演讲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就是过于文学了。当然,我这里的文学是指狭义上的文学,是指作为一种作品的文学。第一个代表中国获奖的作家莫言,显得在这篇演讲稿上用心与用力过度。他把一篇本来应该是表现自己文学思想或者文学理想的演讲,写成了一个长篇的励志散文。
演讲从母亲说起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入口。将母亲比喻为大地也没什么不好。但紧接着莫言讲的有关母亲的故事,不像大地本身,而是大地上奇特的美景。第一个打碎热水瓶的故事,很好。第二个关于母亲与看守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母亲的话“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有些文学化和励志化了,还有卖白菜的故事也是。
这篇演讲稿的“文学病”还表现在,用了大量篇幅来一一诠释自己的长篇小说,而且没有给予听众和读者更多的信息量。 这种急于推销自己作品的做法,让获奖作家不得不挑起评论家的重担,骨子里显出中国作家的不自信来。
低调到自卑,或许是莫言应该正视的问题。自从获奖之后,听得最多的是莫言谈及自己童年的苦难,他像一个会写小说的祥林嫂,不断强行让别人接受一个从苦水里泡大的孩子。也许,莫言将自己的苦难转化成了独特的文学,但他似乎并未将那些苦难转化成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
在小说王国具有王者风范的莫言,如果不能在精神领域成为睨视一切的王者,他在获奖之后能否再突破自己,再突破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一个大大的疑问了。
我喜欢莫言最后讲的那个故事,其实莫言要说的是,他就是那个被另外七个人扔到庙外去的人。他成了第一个看到庙外世界、经历了风雨雷电,而不是被雷电殛死的人——但我更希望看到的结局是,在他被扔出之后,那座破庙没有轰然倒塌,而是外面的暴风雨骤然停止——莫言啊,不要再对过去的苦难耿耿于怀!
12月12日 阴 星期三
半个月前,上海作家张定浩给我寄来两本《上海文化》杂志,2012年第5期和第6期,定浩是这本杂志的编辑。孤陋寡闻的我,很少读文艺理论杂志,真想不到理论性杂志还可以做得这样精致,这样好读。我想,我以前碰到的所谓理论杂志,大多是捧场应景评职称式的拉杂文字,我让“伪理论”给弄坏了胃口,所以对之退避三舍。《上海文化》的清雅精致,不仅悦目,而且一洗肠胃;它的犀利与深厚,更是提振了我的食欲。
两期的头条都是定浩的:一篇是评马原《牛鬼蛇神》的《徘徊在零公里处的幽灵》,一篇是评西川《大河拐大弯》的《你到底要拐向哪里》。定浩在文章中所展示出的细腻、坦诚与识见,令我佩服。比如他在《徘徊在零公里处的幽灵》中说:“某种程度上,写作就是重新编织生活,但首先重要的是拆散,是真正彻底地一次次回到那些动人的、充满可能性的原点。”“因此,真正的好作家,他们的重复并非固步自封,而是有能力向着未来的,他们不断回到原点只是为了不断地重新开始,并不断地修正自己。”
定浩对西川的批评更让我重视,因为西川算得上中国当代诗人的一个代表,他创作上的探索与思想上的滞固,乃至书面表达有如口头表达一般的混乱,都是诗人中的代表。定浩在文中提到,当代诗人的一个毛病:“在要诗还是要思想之间左右徘徊”。我接触的很多诗人也是这样,西川还喜欢读书,他们连书都不读,认为读书会使自己有更多的思想,而思想是戕害诗歌的。这种论调不知由来何自,我想,中国伟大的诗歌传统绝没有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还有对词语理解,我十分认同定浩的观点:
“每一个词,本身的大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词语的生命力,以及词语能够承载的丰富性和它自身的弹性,都依赖于诗人对它的使用。”
12月15日 阴 星期六
前天,中南传媒新媒体新技术部林峰给我送来“中南传媒第二届优质数字资源奖评选”邀请函。邀请函漂亮得好像授予我一份获奖证书。当然,能去中南传媒考察和学习,无异于获得一枚大奖。昨天上午九点,八名评委汇聚出版集团四楼会议室,在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彭兆平女士和新媒体新技术部贺正举部长的主持下,评选开始。除我外,评委还有湖南省图书馆馆长张勇、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副总经理茅硕、长沙晚报副刊部任波、中南大学教授孟泽、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坛”制片人柳理、湖南商学院中文系主任陈书良以及年轻的著名书评人袁复生。
第一届评比我也有幸参加,那时数字阅读刚刚开始,没有什么可参照的。一年之后,我们欣喜地看到,所有上榜图书均是在数字资源各渠道中有销售收入的。我们的任务是,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以及作品的市场潜力,给96本上榜图书打分。在打分之前的评委发言上,我谈了两个基本点和两个核心点。两个基本点是:作品必须适合数字阅读;作家给出了他们最好的作品。两个核心点是:第一,作品有没有独特性?比如星云的日记、丰子恺的漫画、杨德豫的译诗,我觉得这都是有独特性的。第二,作品有没有成长性?有些作品一时阅读量颇大,但读完之后就成为印刷垃圾或者数字垃圾了,而有的图书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还有人读,这就是成长性,它是长销的。像陈蒲清的寓言著作、袁伟时的历史随笔以及邵燕祥的书等,就属于高成长性的。
评完后,午饭前,随复生和孟泽去念楼拜访钟叔河老先生。很惭愧,我这是第一次去钟老先生家。复生介绍,钟老站起来和我握手。老人年过八旬,面色红润,声若金鸣,看见三位晚辈,高兴得紧。他的书桌就摆在客厅,书桌旁是一张桌球台。他说很少打,摆看的。他对住所周围的环境不是很满意,烈士公园近在咫尺,却要横过三条马路才能到,院子里连个散步的地方都没有。但老人生性达观,充满斗志。书桌上摆着即将出版的新书《念楼小抄》的封面清样,他说,他现在的书都是出版商跟他谈,与出版社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其实是出版业的一个好现象,它更有效率,也更能让作者和读者满意。
聊了约半个小时,老人要吃饭了,我们告辞,老人执意把我们送到门口。我们就去和其他评委会合了。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