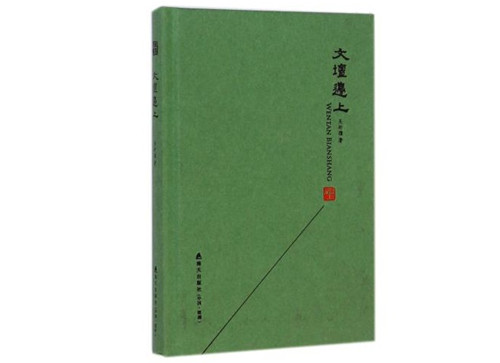
文坛边上·2012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11月3日 晴 星期六
湖湘文化学者柳理,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担任“湘湘讲堂”栏目制片人,他的这个栏目也是湖湘文化在21世纪最为全面、最为厚重,也最富有创新精神的一次呈现。今天,他请来著名历史学家傅国涌先生讲宋教仁。
20多年前,本来身兼教职的傅国涌因故成为了“自由学者”。后来,环境渐渐宽松,他开始在《南方周末》《随笔》《东方》《炎黄春秋》《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作品,开设专栏。我曾读过他不少随笔,钦服其文风与人格。原以为他年纪较大,不料上网一查,竟与我同年,益增其敬慕之情。今天下午2点半,我和敏华赶到教育电视台演播厅。十多年前,应好友续文邀约,我曾在这里与主持人姜丰进行过一场有关学习方法的对谈,后来续文还将它出了书,大约叫“书山有路”之类,记不太清了。
傅先生个头偏高,略显秃顶,普通话虽不十分标准,但吐词十分清楚,不愧是教书匠出身。他讲得非常好,我们对他的演讲给予了一个“四有”的评价:有思想,有勇气,有文采,还有体力——因为他站着讲了整整一天。
傅先生告诉我们,整整一百年前,在宋教仁几乎只手之力的推动下,中国曾经有过极好的进入宪政民主社会的机会,然而,至今未明幕后真凶的暗杀,让中国露出曙光的民主政治陷入黑暗的渊薮。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看上去是宋教仁过于张扬的性格,其实是中国政治对于专制的超强欲望。傅先生说,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任何一个人的追悼会有宋教仁那样的悲壮,上海主会场有两万多人,全国各地的分会场无数,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悼唁挽联。孙中山的挽联是:“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也就是传说中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所在地,少年时就读于桃源漳江书院,17岁离开故土,走上报效国家的喋血之旅。清丽山水奉献奇伟之士,乃湖湘之幸也!
11月7日 小雨转阴 星期三
《温州读书报》2012年第10期,头版有雷雨的大作《为什么是莫言》,文中提到中国文坛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纠结心理:没有中国作家获奖的时候,梦寐以求;终于有一个获奖了,又质疑不断。还有人认为,莫言获奖是因为他的作品暴露了中国乡村的落后而博得外国人的青睐;还有人说,那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打开中国市场的战略考量……这些想法,究其实质都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是酸葡萄心理的绝妙反映。当然,雷雨在文中也提到,莫言在人民日报发过一些所谓的报告文学,比如为张艺谋唱赞歌的,还有写山东高密什么开发区之类的,“看过之后,大失所望,甚至有要呕吐的感觉。难道说,其他大师级作家也会炮制这样的垃圾吗”?
我个人的意思是:一,并非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都是大师级的经典作家,大师级作家不由是否获奖来界定;二,即便是经典作家,包括没有获这个奖也可能跻身经典行列的作家,主要看他们最好作品所能达到的标高,不要对他们的所有作品过于苛求,评论家和读者都不要有洁癖;三,莫言毕竟是一名中国作家,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像人民日报那样的文章,不过应景应酬而已,我相信,即便出版莫言全集,莫言也不会将那两个东西塞进去的。
第四版有夏海豹先生的《文学的理想与失落》,写著名散文家峻青和诗人洛雨的一段交往,其中有一封峻青1996年2月22日写给洛雨的一封信,我们来看看一位老作家是如何看待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
“……这年头出书不易,但又太易,问题是什么人易,什么人不易。如我辈穷书生无钱出书者太不易;而目不识丁或粗通文墨者只要有钱,哪怕是找人代笔或错漏百出文法不通根本不够出版条件的照出不误,而且出了一本又一本,真是钱可通神也……”
在这个钱可通神的时代,即便擅写如莫言,又何能免俗?
11月14日 阴 星期三
前不久,客居深圳的湖南邵阳诗人袁叙田与我联系,说他正在创办《邵阳诗歌》报,嘱我多关照。昨天,即收到《邵阳诗歌》报的创刊号。
我一直认为,湖南诗歌如果按地域而论,邵阳诗人绝对是第一大群体,其诗歌氛围之好、诗人数量之多、作品质量之上乘、写作传承之紧密,一时无二。与湘西北的常德多女诗人相映成趣的是,邵阳基本上是男诗人一统天下。我想,酿成这一局面的地理原因可能是:常德在洞庭湖边,近水;而邵阳在雪峰山下,靠山。
我认识的邵阳(籍)诗人一大堆:匡国泰、谭克修、马萧萧、马笑泉、梦天岚、李晃、李傻傻、陈静、李跃、李青松、袁叙田、魏斌、刘羊、刘定光、汤文培、罗松明、江冬、马迟迟、小古、一番、尘子等等,感觉是邵阳的诗人,数都数不过来。可见,办一份《邵阳诗歌》报是多么必要。
11月15日 阴雨 星期四
《开卷》第9期分两部分,后一部分是常规文章,前一部分则是已故作家黄裳的纪念小辑。黄裳于今年9月5日因病去世,享年93岁,他被不少粉丝誉为“当代散文大家”。我在报刊上接触过黄裳的一些作品,但始终没能很接受他。
印象中,黄裳老先生用一种颇为古雅的文字写散文,这种风格不容易引人共鸣。在同类散文作家中,他清淡悠远不如孙犁,深幽宏阔不如张中行,生动浏丽不如董桥,唯坦荡似有过之。所以,他被那些喜欢掉书袋的读书人捧得很高,一般读者如我等,往往望而却步。严格地说来,孙犁、张中行、董桥可能都算不上“当代散文大家”,不是他们的文章不好(其中以张中行的散文最好),而是他们延续明清散文一路,对散文现代性的贡献并不大。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贻笑于大方之家。
《开卷》第9、10两期,我喜欢的文章是刘绪源的《悲怀中的印象——简说黄裳》、林伟光的《裳翁虽去书魂在》、何频的《画谭新钞》、理洵的《追寻古文化的足迹》、白水的《画说汪曾祺》和子聪的《开卷闲话》。纪念黄裳的多篇文章中,我之所以最喜欢刘绪源和林伟光的,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写得比较客观,对黄裳的定位比较准确。比如林伟光写的一段:
“我们封裳翁的种种头衔,无非什么什么家,也不能说错,他的多方面成就,一大套数百万字的《黄裳文集》,也足够支撑起这些。不过,我想裳翁如果有所选择的话,他更愿意人们把他看作一个读书人,读书是他人生的主要内容,给他带来快乐,也带来了思考。其实,他的写作在某些层面上,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读书的延伸。”
11月19日 雨 星期四
十多年前,我陪戴海老师,带着河南郑州电视台张书琴女士去岳麓书院找诗人江堤,正好江堤那里也来了一个衡阳的朋友。于是,他便将我们两批客人归拢到一块,给我们讲解书院的历史和文化。那位衡阳朋友叫甘建华,是一位作文、画画、写字的三栖全才。昨天,接到建华兄的一封信。他说:
“您是湖南新乡土诗派的重要成员,也是我们衡阳诗友江堤、吕宗林的好友,我在青海师范大学的学长唐燎原对您的评价也颇高。像《掌中泥土》《乡土境界》《姐姐的村庄》等,我都还有印象,感觉您的诗歌里面乡情因素较少,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理性。我虽然不写诗,也不做诗评,但我与吕宗林、吕叶等人相聚时,经常谈起新乡土诗派和你们那一拨人,感叹这样的时代已经很难产生那样优秀的诗歌和优秀的诗人了。”
谢谢燎原先生的高评。以前习诗时,我认真学习过燎原先生的诗歌评论,但并无任何直接交往。他的鼓励也给我更大的信心。建华兄对我的新乡土诗风格的把握也是准确的,在那个农具农业、乡村乡土满天飞的年代,我的触角是想更深层地挖掘乡村的命运,探讨乡村的历史与文化。当然,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相应的优秀诗歌与优秀诗人,只是那个时代对诗歌追求的纯粹与执著,现在已成空谷足音。
接下来,建华写道:“今天,湘潭楚子给我发来短信:‘甘兄,建议您策划一个湖南新乡土诗为题材的书画展,我和长沙的吴新宇(现已改名吴昕孺)都能书画,可多创作些作品,可与湖南日报陈惠芳联手,报展实展同行。’我才知道您于书画一道,也已经有很大的成就了。”
我呵呵一笑,只好给建华回复道:“读完兄的长信后,我感到非常汗颜,因为我于书画一途,确是一窍不通,楚子兄说我能书画,如果不是对我的鼓励,可能就是道听而来,当不得真。我幼年曾习画,草草收兵。青年曾习书,收兵更加草草。主要是俗务过多,加上精力大多在读书作文上,不像洛夫、浩明等大师,满身才华,干什么都手到擒来。说起来兄可能不相信,电脑打多了,写几个钢笔字都不成形了,架子都搭不稳。本来准备给兄手写回信,最后还是决定回封邮件来得方便踏实。”
感谢建华兄的来信,让我回到十多年前在岳麓书院的那一幕,我依然记忆犹新,可江堤兄墓木已拱,令人唏嘘。刘禹锡说:“人事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我每回遥望麓山,总是低声问它:你还记得那位诗人否?
11月30日 阴雨 星期五
我先想说的一句话是:老头子不简单!老头子不是别人,是大家很熟悉的戴海老师。为什么说他不简单呢?
昨天上午九点半,是他的“爱学生”(徐特立语)、湖南师大音乐学院年仅37岁的教授、博士喻意志的追悼会。我因开会没能前往,前天打电话给老师,关照他不要去。白发人送黑发人,内心之悲怆可想而知。虽然没去,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老师内心的悲怆也不会因此而减轻。在这样的情况下,晚上七点,他还要到师大图书馆给两百多名学子做以“书里书外”为主题的演讲。
我将几位书友给《戴海村语》写的评论打印下来,六点从单位出发,五十分钟后到师大图书馆,一进门就看见老两口搀扶着,在边走边聊。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一边向报告厅走去。松松、进跃带着读大二的叶子来了,叶子来听听爷爷的讲座是很好的,她可以从另外一个向度来认识和了解爷爷。随后,看到诗人刘羊、柔止带着妈妈来了,我想起2009年,戴老师带着鹏飞、郑艳和我一同来师大演讲,刘妈妈也来了。妈妈如此好学,难怪儿子会成为诗人。
七点,在鄢朝晖馆长的主持下,讲座正式开始。自称“奔八”的戴老师先讲述了自己的阅读史,比如,他启蒙时读到的第一课:“来来来,来上学。”第二课:“去去去,去游戏。”多有趣。再谈到他对读书的理解:“读书是永不过时的时尚。”“读书需要记性、悟性与韧性的完美结合。”再谈到如何读书,蔡元培送了刘海粟四个字:宏、约、深、美。宏是面要广,约是要突出重点,深是思考要有深度,美是通过读书要能领略自然与生活的美。最后,他叮嘱同学们,要多读耐读的书,读书一定要过笔。同学们不时发出会心一笑,或者爆出热烈的掌声。
外面下起小雨。讲座,我们陪着老师在雨中走了一段。他觉得现在的孩子被所谓教育死死束缚住了,他一连说了几个“非常值得同情”,话语里透出深重的忧虑。我问一旁在湖南大学金融系读书的苏叶子,是不是真的没时间读点闲书。叶子说:“我读高三还能抽出时间读小说,上大学后反而不行了,科目太多,压力很大,没有办法。”我也只有长声一叹。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