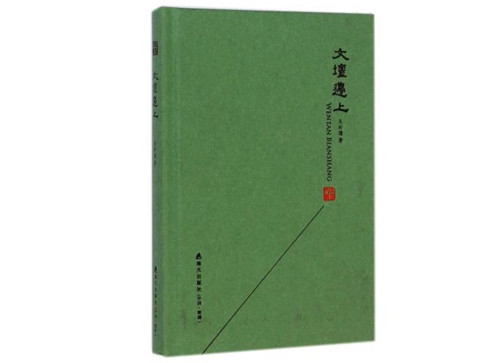
文坛边上·2012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9月28日 晴 星期五
我现在一年写诗较少,大概不到三十首吧,发得就更少了,尤其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所谓“官方杂志”上。杂志分民间与官方,这也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暂且不去管他。但有一本杂志我基本上每年还能亮亮相,那就是中国西部最有影响的诗歌刊物《绿风》了。
《绿风》的主编曲近,是一名优秀的边塞诗人。上世纪末,我和我的同事李正军去新疆出差,因我的老师戴海在石河子生活、工作了17年,我们特意跑到石河子,带了那里的一瓶泥土回来送给老师做纪念。在石河子,我见到了曲近兄,他像西部一样质朴、宽厚和热情,但身形瘦弱,寡言少语。他请我们吃饭,然后带我们到刚落成不久的艾青博物馆参观,《绿风》编辑部就在馆内,那时它的主编是一名叫石河的老诗人。此后,曲近兄每当出了诗集,就送给我学习。而我发现,不仅他的诗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近些年散文也写得相当棒。厚积而薄发,曲近兄是一个榜样。
前几天,收到《绿风》第五期,刊发了拙作三首:《一面镜子从天而降》《蝴蝶》《秋天的原野》。这一期头条“三弦琴”推出的是现居北京的重庆诗人唐力,早一向在常德诗人节上刚认识他,同样的质朴、宽厚和热情。从《绿风》上得知,唐力是重庆大足人,大足我不仅去过,而且还认识那里一名很不错的女诗人红线女,还认识那里一位同样很不错的散文家吴佳骏。大足以古代石刻著称于世,我想,只要有了唐力、红线女、佳骏,那里的现代文化便足可称得上一片耀眼的绿洲。
9月29日 晴 星期六
时序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大的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小的有家长里短诸多日常物事。其实,这些事几千来一直在发生,并不是现在独有的,但哪怕是同样的事,发生在千年前和千年后肯定会有不同的内涵。
于是,几年前,我生发了以词典的形式,为21世纪建立一份档案的想法,陆陆续续写了两三万字,着重探究这个世纪以来人类行为背后的文化特征与心理变化。这样的文字不太可能泛泛而谈,因此很难找到知音。因为难写,所以更难读。因为难写,我写到两三万字的时候就停下了。然后,试探着想为这些篇章找个地方发表一下,听听读者们的意见。毫不意外的是,很少有刊物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倒是我将它们贴在天涯社区的“散文天下”之后,有一本命名为《心潮》的书,将其收录进去,我在江南雪儿的博客上看到目录,但至今没收到样书,也不知道那书最终出版没有。
还是要感谢《青年文学》,他们在今年第9期“现代笔记”栏目刊发了《世纪词典》中的八个词条,计有:《界限》《疾病》《譬喻》《抑郁》《死亡》《病人》《宽恕》《速度》。好像一头母猪一窝下了八个崽子,内心有一种丰收的喜悦。该刊执行主编唐朝晖在谈到这组随笔时,只说了两个字:“很好。”我不知道这次发表,能否激励我继续将这个系列写下去,但愿有一天,从我的内心能生发这样的力量。
10月11日 晴 星期四
半个小时前,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中国作家莫言,授奖词为:“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现代融为一体。”
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和高兴的事情。莫言获奖的意义,不言自明。虽然这个奖只是莫言个人的,它只是一个纯个人性的奖项,但它的世界意义与顶级水平依然赢得最为广泛的关注。依仗所谓十多亿读者的民族主义心理,漠视甚至贬损诺贝尔奖的诸公,散发出来的无非是极其浓烈的酸味与戾气。
应该说,莫言这次获奖实至名归。这不是说莫言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至少我认为世界上比莫言更好而尚未获奖的作家还有奥兹、石黑一雄、卡达莱等。但莫言无疑可以跻身世界优秀作家的行列,它比前几年获奖的高行健、勒克莱其奥、凯尔泰斯·伊姆雷都要好,至少可以与莱辛、戈尔丁之流比肩。
莫言获奖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位置和尊严,但这不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了中国作家莫言的天才与勤奋,并没有奖励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国内文学界或许很多人都会对莫言获奖不以为然,我希望这种“不以为然”,不是体现为一己的失落,而是真正认识到文学探索的永无止境,真正认识到文学对当代世界不可或缺的作用,真正认识到文学本身的奇妙与沉重。
10月13日 阴 星期六
莫言获奖之后,一时成为中国文坛和社会的热点。看到有记者采访莫言,得到奖金要做什么?莫言说,想在北京买房,买大房子。记者提醒他,750万奖金在北京也只能买个120来平米。这时,地产大佬潘石屹还不忘插科打诨地问道:“有北京户口吗?”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段子。看上去似乎不是,是新闻报道。
既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中国最优秀的当代作家莫言在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前,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状况。
我在想,那么大的北京,北京那么多大房子,究竟是些什么人住在里面?写了11部长篇小说、出版著作数十部的一位著名作家,竟然至今委屈在首都的一个蜗居里,中国对待文学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看看我们文学报刊的稿费标准吧,看看出版商对作家版税的威胁与挤压吧,看看那么多优秀作家对权位的贪婪和嗜好吧……
获奖的毕竟只有一个莫言,诺奖毕竟不可能年年来照顾可怜的中国作家。北京的大房子,或许永远只是众多北漂作家的一个黄粱梦。
笑贫不笑娼,这个古老国度的传统力量是多么强大啊!难怪,莫言在家中接到获奖电话时,他是那么“狂喜而惶恐”。或许,他狂喜的是,终于有钱买大房子了;而惶惑的是,自己一跃而为中国作家圈中的富人,会不会同时也成为“房子梦想者”的众矢之的呢?
在为莫言获奖庆贺之余,也为僻处陋室、辛勤耕耘的众多中国作家喟然一叹。
10月19日 晴 星期五
《桃花源诗季》2012年秋季刊,有关于第六届常德诗人节的特稿,那个诗人节我有幸亲身参与,一睹盛况。“诗空璀璨”栏目刊发了娜夜、田禾、韩文戈、俞昌雄、离离五位诗人的作品,我最喜欢娜夜和俞昌雄的,其余三位作品一般。
我个人认为,娜夜与路也无疑是当代女诗人中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其他无论80后、90后,或者打工派、新生代,目前都不能出其右。她俩正好一东一西,如果再加上南北,广东有郑小琼,北京有安琪;如果再加上中部,那就是湖南今年去世的唐兴玲了。娜夜与路也,娜夜诗歌气质更好,路也写作才情更足,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诗人。
“每季之星”栏目推出的是常德本土诗人杨拓夫。拓夫的诗干净、清新,有如池塘春草。但他时常一不小心就回到陈旧的套路上,影响其作品的质地。比如《行走的村庄》,后面都写得很好,感情深厚而又节制地引领着诗行,但没想到他是这样的开头:“你何时开始了行走/日夜兼程 在漫长的旅途/你在李白的《静夜思》里走/走不出唐朝辽阔的疆土。”这一段,既与后面的风格不合拍,表现手法又很老套,应当“咔嚓”。还有一首《空荡的打麦场》,前面两段很漂亮,第三段突然松懈下来:“步入五月的阳光/回归那一场乡村的交响/捉住那美妙之音/人在当下 让时光汩汩倒流。”如此,诗意便流失大半。
“三湘俊彦”专栏终于找到了一位长得帅、诗也越写越帅的小伙子——欧阳白。我和欧阳白的交情绝不是我在这里推重他的理由,因为我们的交情也不是一两年了,我写诗表扬过他车开得好、人做得好,我写博文表扬过他诗屋办得好,但我不得不说,欧阳白这两年诗歌技艺的突飞猛进,可谓一日千里。这和他潜心于哲学、宗教(佛学)有关,这和他一直与洛夫这样的杰出诗人“教学相长”有关,当然这也和他长期以来车开得好、人做得好有关;最为重要的是,欧阳白对诗歌那种单纯而深切的热爱,让他身上散发出罕见的极为纯粹的诗人气息。
他写《姑苏月》:“钟被那个年轻人用狼毫点了一下/声音不大,但颜色很深,很艺术。”他在《心经》中写道:“所有的苦都从曲折开始,做条直性子的牛吧/厄运到做牛处终止,做了牛,不再言语,冲着山谷喊一声:哞。”他写《鱼吻》:“湖面上明明没有任何/可以叮到的食物,你那瘪瘪的/嘴不停地张合,未必是在/扇动空气,好让这宁静的/水域有波浪的样子?”
这些诗句一读就让人心动,因为它们是诗人独有的,别人从没有这样写过,但读者一出声念出来,就会觉得,它写到了我们的心坎里面。
10月31日 阴 星期三
继莫言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作品进教材又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实,单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是为进入教材而写作的。毫无疑问,教材是一个国家发行量最大的作品选本,但由于它面对的特殊对象以及它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并不是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一定都要进入教材,或者说,一本教材一定要囊括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教材做不到,作家也做不到。教材为全国所有适龄儿童与青少年而设,作家却永远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文学创作本身是极为私人化的活动。所以,莫言获奖之前,他的作品没有进入教材,仅从这一点来说,既不是教材的错,更不是莫言的错。
谁也没想到的是,莫言竟然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对于长期以来“诺贝尔情结”顽固得近乎变态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消息无异于划破长空的闪电。于是,此前“新时期当代小说全体缺席”的中学语文教材立马前倨而后恭,人民教育出版社称将考虑在教材中选用莫言作品,语文出版社则拟直接将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选入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读本。
窃以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态度是可取的,不失敏捷而又审慎。敏捷在于,作为国家教材出版重地,能对莫言获奖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审慎在于,不是盲目追风,而是一方面承认此前对莫言有所忽略,另一方面也不说莫言作品就一定入选,“考虑”一词用得智慧。相较之下,语文出版社则显得急功近利,直想借莫言获奖炒作一把,却不自觉地暴露出商人的势利。
我个人认为,《透明的红萝卜》不宜选入教材读本。原因有二:一、《透明的红萝卜》是一部篇幅达数万字的中篇小说,进入教材只能截取其中一部分,与其这样,何不去选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呢?莫言的好作品很多,我相信有更适合选进教材的短篇小说;或者,教材编写组专门邀约莫言为中学教材写一个小说,也未尝不可。二、《透明的红萝卜》讲述的是一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农村少年的故事。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中学教材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以前教材中假、大、空盛行,僵化的意识形态让孩子们与美隔膜,与爱远离,很少有拨动孩子心弦的文字。这些年来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对教材提出质疑,我担心教材编写将落得个方向模糊、无所适从的境地。任何一件事情,有争论是好事,但奇怪的是,我们总是在争论中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不是越来越明了。其实一本好教材的标准非常简单:孩子们喜不喜欢,是否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这里我还是要举一个鲁迅的例子。上世纪30年代,鲁迅的《呐喊》被列为中小学教科书走进了课堂,鲁迅根本不是为之而欣喜,而是“十分沉痛”。他对他的弟子、著名副刊编辑孙伏园说,他后来一看到那本书就感到厌恶,因为他很不愿意孩子们读到那些凌厉寒凉的作品,不愿孩子们读到描写处处“吃人”的《狂人日记》。他甚至偏激地说,这本书应该绝版。鲁迅认为,课堂是展示光明、传授善念、启发爱心、激励理想的地方,怎么能宣讲那些充满凶狠、仇恨、冲突、暴力的东西呢?这些都“少儿不宜”啊!从鲁迅拒绝诺贝尔奖提名,到他对自己作品选入教材的态度,我们能看到真正的文学大师的风范。
最后,寄语教材编写者们:世界上优秀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适合各个年龄段孩子们阅读、学习的优秀作品同样有如繁星灿烂。只要你们心里装着孩子,而不是狭隘的政治与民族意识,不是世故成人的一厢情愿,不是坐在办公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想当然,你们一定能编出让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好教材来。苟如此,则莫言能否入选教材,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11月2日 晴 星期五
西藏诗人陈跃军寄来《西藏情缘》,由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封面上“陈跃军、刘昕主编”的旁边,还写着“杨从彪、吴昕孺审订”,让我觉得很惭愧。当然,我了解这部书稿出版的全过程,从面向全国征稿,到筛选、审阅、校对以及封面设计,跃军和刘昕都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西藏情缘》是跃军和刘昕“兄弟俩”有关西藏文集的第二次成功合作,第一次他们的产品是《相约西藏去放牧》,赢得一片叫好。我看《西藏情缘》从整体质量上更好,设计也更精美大气,虽然我刚刚拿到书,但我知道这本书出版后,在西藏引发了一股文学热,在西藏之外的地方则引起了一股西藏热。西藏商报,中国新闻出版网、中国图书对外交流中心、中国西藏网、中国民族宗教网、为先在线等先后以“西藏散文又一次吹响‘集结号’”为主题,对之进行深度报道。为此,跃军还亲自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读书频道做了一期专题节目。
此前我通读过全书。有些文章我是记忆深刻且非常喜欢的,比如跃军的那个序言《我和西藏有个约定》,他写得极为诚恳而生动,是跃军最漂亮的散文之一。他说:“在西藏,面对蓝得让人觉得不真实的天空,面对冰清玉洁的雪山,面对辽阔的苍茫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觉自己渺小,伟大的渺小。在内地,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总觉得自己是一只孤独的蚂蚁,微不足道,一种被忽视的感觉,卑微的渺小。”
是的,人无不是渺小的,但却有“伟大的渺小”与“卑微的渺小”之分。跃军热爱西藏,并成为西藏的一员,乃是他对属于自己“渺小”的选择,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的选择呢!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