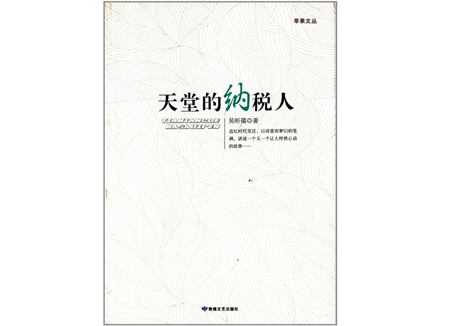
天堂的纳税人(小说集)
作者丨吴昕孺
薛 涛
乌去纱先生是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书生。他买了很多很多书,他买书可不像某些藏书家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凡他买的书差不多他都要读一遍,甚至连那些砖头厚的工具书他也要一页页把它们翻过去,至少不能让它们看上去还是一本新书。对于乌去纱先生来说,书就是一条源源不断的流水线,他人生的使命就是在这条流水线上作业——先是买,买了读,读了之后写读后感送到报社,或者把好几本书的内容重新编排一下送到出版社,发表和出版之后拿到稿费又去买书……他对自己人生的这种运行轨迹非常自得,这种自得表现在他那一小把连腮胡子总是向前面翘起,好像佛庙里大雄宝殿的一个檐角。看上去,他那方形的脑袋就颇有大雄宝殿的威严,他所在报社的那些小编辑们都尊称他为乌老师。乌老师望着这些小青年,嘻嘻哈哈、红男绿女的,好半天才答应一声。小编辑们说,这是从大雄宝殿里发出的梵音。他们表面上尊敬这位年纪比他们大十多二十岁的老师,心里其实把他当作一个笑柄。
乌去纱先生或许明白这一点,或许不明白。
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与他共事的人都这样认为,这也是敢于把他当作笑柄的原因之一。从没有看见他和同事、领导、作者、街头混混各色人等吵过架。碰到别人吵架的场合,他只是笑笑,绕道走开,连腮胡子在下巴那里明显翘得更起,仿佛一只鸟要飞起来的样子。
乌去纱先生还是一个执拗的人。只有三五好友和他夫人了解这一点。他视书如命就是执拗性格的典型症状。于是,他的夫人在一年半之前果断离开了他,她知道,她努力伺候他一辈子也不可能在他心中占据比书更重要的位置。乌去纱先生时常开玩笑说,书是他的情人,常看常新;老婆嘛,是衣服,越穿越旧。他可不管夫人在旁边听了心里难受。因为他一直认为,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会有什么改变,何况是嫁给他这样一位小有名气的书生呢?她总不至于真的和书争风吃醋吧。
但乌去纱先生碰巧找了一位这样的夫人。当他发现,为时已晚。夫人去意已定,而且把他们刚满七岁的可爱女儿与存折、金银首饰一并带走了。
乌去纱先生很是伤感。本来热热闹闹的家里突然人去楼空,最难受的是他每天下班回来,打开门,习惯性地对着屋里喊“春分”“小雪”,却没一个人应,有时还感觉得到灰尘从窗台或装饰灯上落下来,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更显得屋子里的枯寂与空洞。
春分是夫人的大名,姓什么他一时想不起了。小雪是女儿的乳名,他从来没有喊过她的大名。这两个名字现在都成了符号,成了从他胡子上滑落的两个音符。他是一个光杆司令了,除了书。没有一个家的氛围,连书也没精打采,他每次翻开一本书的时候,那些书总是不耐烦地、迫不及待地合上。有时他好不容易把一本书看到一半,那本书猛然从书桌上跳起来,或者使劲挣脱他的手,严丝密缝地合拢着,像刚出厂的、装模作样包着塑料纸的新书一样。他霸蛮再去打开,就怎么也找不到刚才看到的那一页了,仿佛他刚才看的完全是另一本书。
他下决心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便以便宜的价格卖掉这套房子,在浏阳河边一个叫金色屋顶的小区买了一套小很多的商品房。他想,只要放进书和他就可以了。他把新房的大部分地方都做成书房,当然放饭桌和单人床的地方除外。
以前,他怕夫人生气他买书太多,用稿费之类私房钱买的书基本上都堆在办公室,不敢拿回去。书放在办公室一直让他很不安心,好比把自己的情人寄存在朋友家里,尽管是信得过的朋友,也总担心偶然事件的发生,比如情人溜一跤朋友立即伸手去扶,就可能发生四目相对、含情脉脉的状况。书放在办公室也是这样,一年365天可能有364天是安全的,但有一天如果哪个同事不对劲,或者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不知趣的客人,从乌去纱先生的书架上悄悄带走一本《性的孤独史》《内衣揭秘》之类,无异于抽去乌去纱先生一根肋骨。
这下好了。新房子是自己的,只有自己一个人住,随你放多少书,随你怎么放,没人管了。真是因祸得福呵。乌去纱先生兴高采烈地想。
乌去纱先生现在的任务是把办公室的书一批批搬回新家去。他不想太急,办公室的书很多,他找了一个不知什么时候用过的黄色挎包,一次能装十来本,他每天下班后就挎一包书步行回家。之所以步行,不是因为乌去纱先生小气,而是下班时的士们正好要交接班,招不到;公交车站则人山人海,每来一辆,车门还没打开,车站就变成了古战场,分不清敌我。他挎着这么大一包书,差不多占了两个人的空间,还要往车上挤,立马会成为所有上车者的公敌。他索性安步当车,走回去只要四十多分钟。
“这么好一个锻炼项目,放弃了可惜呢;节省下来的钱又可以买书,这不是一石两鸟吗?”他心里说了这么一句,嘴巴上惬意地笑开了,胡子翘出一个更为夸张的角度。旁边的行人看了都觉得好笑,但他们只把眼睛的余光瞟着他,笑的时候要不掩着口,要不望向别的地方,这样就不会让自己的笑惊动他,从而让那意外得到的快乐延续得久一些。
但这一天,乌去纱先生挎着一包书走下办公楼的时候,看到外面雨夹着雪,天气恶劣得很。他像被人戳了背,浑身一个激灵,本想再回办公室把书放下,等天气转好以后再拿算了。这个想法只在他脑海里一闪便过去了。既然把书拿下了楼,说明我和书之间已经有了契约,怎么能随便悔约呢?乌去纱先生再没有丝毫迟疑,一脚迈进了雨中。
偏偏这次书还放得特别多,因为明天是星期六,双休日有两天不能运书,所以这次就多塞了几本,弄得挎包的拉链都拉不上,最上面一本露出了大半边封面,看得出是一本《薛涛诗选》,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字样。
雨比想象的要大,风裹挟着雪粒,横冲直闯,像一群受到某种威胁的无头苍蝇。乌去纱先生越走越觉得自己这回太冒失了。他有一个不知是好还是不好的习惯,无论多大的雨都不带伞,宁愿被淋湿也不愿意撑一把伞在外面走。他觉得不打伞在雨里面走,有一种与天斗的无穷乐趣;要是雨实在大得不像话了,他就找一个屋檐把自己盖起来;倘若正好有一家书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保准他到书店里转一圈,雨就偃旗息鼓了。当然,这些都只是乌去纱先生为不打伞炮制的诗意的理由,其实他不带伞出门最现实的原因是,他带一把丢一把,家里的伞早被这个书呆子丢得精光了。他夫人以前责问他:“你把书带出去怎么不会丢掉,伞一带出去就丢掉了?”他想了半天,没有得出答案来。不带伞是最好的,无伞一身轻,反正家里再丢伞都与我无关了。
这回糟糕!拦了好几辆的士都不停;有的停一下,司机探出头来问到哪里去,与他交班的方向不合,他摇摇头,一脚油门就跑掉了。乌去纱先生见势不妙,又走到附近一家公交车站,指望能搭上一辆不太拥挤的车。但不知怎地,明明街上没几个人,公交车站却像等着发钱一样,拍满拍满的人。这下轮到他摇摇头,抬起脚还是走了起来。
有一把伞该多好啊。他的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然后马上予以否决。那是不可能的。他看着路上打伞行走的人们,第一次涌起了羡慕之情。
由于怕滑,他把步子剪得碎碎的,微微弯着腰,以降低自己的重心。天冷得厉害,路上已经有结冰的迹象了。这在南方,可真是一件稀罕事。就像朋友们听说他离婚一样,都感到不可思议。看来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都有着同样的机制,所谓不可思议只是一种假象,其实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便是生活的一种常态,除了引起人们用表示惊讶的神态来对当事人进行安抚外,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所有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将发生,那不可思议便构成一种悬念,不知道哪一天会落到哪一个人的头上。乌去纱先生离婚了,南方今年下雪了,这都是某一种悬念的终结。悬念一旦终结,人们就不再感兴趣,他们会把注意力迅即转移到另一个悬念上。生活的意义就像春天的花树,变得摇曳多姿起来。
乌去纱先生的皮鞋有点大,尽管里面垫了两双鞋底。他走到芙蓉路喜来登酒店门前的地下通道口时,不小心吱溜滑了,好在他反应快,右手及时抓住一根路灯柱,才稳住了身子。他的左手在去扯住挎包的带子以防它滑落肩膀时,碰到了挂在胸前的公文包,明显感到里面有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记得,他的公文包里面只有一份下期的校样和一张上面还有48.5元钱的存折,校样是晚上要在家里加班看的,存折是为突然来了朋友要请客或者有好书要寄钱以备不时之需。那个硬邦邦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站定后,把公文包打开,里面没有别的,只有一份校样和一本存折,存折上面的数字并没有改变。他一捏公交包,那硬硬的还在,他把手再伸进去,从夹层里掏出那硬东西,竟然是一把伞。
我的包里怎么会钻出一把伞呢?我几百年不用伞了呵。这个有关伞之来历的重大问题,乌去纱先生已经来不及想了,他赶紧把伞撑开,不禁哑然失笑。这是一把烂伞,整整有一边的弦子都断了,伞面像软骨症患者一样耷拉下来。乌去纱先生灵机一动,他把黄色挎包挪到胸前,把挂在胸前的公文包移到身子右侧,再把那半边好伞搁在挎包上,正好护住了露出封面的《薛涛诗选》。
他心满意足了。虽然雨和雪下得很大,他反而更有一种满足感,把这些书拥在怀里,用伞保护着她们,在雨雪中不受丝毫侵犯。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书生的价值,他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前进,能阻止他护送这些美好的书籍回家。他为自己的英雄气概感到自豪,他甚至希望雨和雪下得再大些,更加衬托自己这一奋不顾身的壮举。
终于到家了。他换好鞋子,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挎包,看看里面书的情况。其他都安然无恙,但最上面那本《薛涛诗选》的封面还是有点弄湿了。乌去纱先生很心疼,赶忙扯出几张餐巾纸轻轻地摁擦着,以期吸掉封面上的水分;然后打开电吹风,对着它扫来扫去,只几个回合,《薛涛诗选》的封面就差不多恢复旧貌了。
他随手翻开这张封面,扉页是一张图,上面的女子明眸皓齿,白面长身,正在一张粉红色的信笺上写字。当是薛涛无疑。乌去纱先生松了一口气,对着图片调皮地说:“只要没把你弄湿就行。”说完,将书合上,插进了书架第二层中间那格,最显眼的地方。
处理《薛涛诗选》花了不少时间,乌去纱先生没有及时换下身上的湿衣服,没有及时擦干已经湿如水草的头发,他吃了一盒方便面之后,忽然头疼发昏,眉眼生热,喉咙干结,全身乏力。重感冒向他发起猛攻,并迅速占领了健康和清醒的地盘。他赶紧支撑着自己去翻抽屉,这些抽屉都是从老房子那边原封不动搬过来的,里面乱七八糟全是笔套、笔芯、空白留言条,还有女儿留下来的动漫书的残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一张被揉皱的“大吉大利”的空红包下面,发现一板只剩下了四粒的快克。他喜出望外地抠出一粒,扔进嘴里,举出餐桌上的热水瓶,却倒不出一滴水来,他只好把那粒早已在嘴里等着热水护送下肚的快克硬生生吞了下去。
过一会,头越发疼,沉得脖子都举不起了。他趁着自己仅有的一点清醒,先是打电话到编辑部,请几天假;然后看那板快克的反面,上面的有效期是2000年5月,现在已经是2002年1月了呢。过了有效期,肯定没那么有效,他一不做,二不休,又抠出一粒放进嘴里。那粒快克在他嘴里转了几个圈,硬不肯下去,每次到了喉咙口,它就拼命折回来。最后一个回合,乌去纱先生拼了老命,他直起脖子,动用牙齿、舌头、喉结、唾液等全部武装力量,才把它强行镇压了下去。那粒胶囊在他的食道里痛苦地打着滚,滚了好几滚,纵身落入黑暗的无底深渊。
几乎与此同时,黑暗来到了乌去纱先生眼前。他感到自己像那粒胶囊一样,在时间的食道里痛苦地打着滚,他无法控制自己,他像滚下山坡的碾子,自己身体的重量反而成为助推的帮凶。他发出惶恐的叫喊。但这种发自本能的叫喊只有他自己听得见,这是一种向内的叫喊,他只能向自己求救,可自己已无能为力,眼看就是深不可测的无底之渊……
谁都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很久很久,也许又只有一瞬间。乌去纱先生宛如皮蛋壳的眼皮翕动了,仿佛里面有一张小喙在啄着。妇人好奇地看着这一幕,她真希望这张蛋壳被啄破,从里面跑出一只小鸡来。她以前在成都就喂过好多小鸡,她喜欢那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叽叽喳喳、无忧无虑的一群,啄碎了她多少伤悲。一俟鸡长大,她就举手送人,自己再到附近农家去买刚孵出的小鸡。她害怕小鸡长大,就像害怕自己年老一样。但小鸡总是要长大的,就像她总是会老一样。年老而色衰,女人的宿命。小鸡长大了可以送给别人,自己老了可以托付给谁呢?
与其说乌去纱先生睁开眼睛,不如说他打开了眼皮。自然没有小鸡欢快地跑出来,黄褐色的瞳仁被大片眼白看管着,转动一下都很艰难。但他还是看见了妇人;或者说,他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妇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看见了一个妇人的美丽。因为,他不得不承认,首先是妇人的美丽让他吃惊,而不是一个妇人的出现使然。
他躺在单人床上。妇人望着他笑,说了一句:“你醒了。”口音怪怪的,却出奇地好听。她上前把他扶起来,靠在后面竖立的枕头上。她到厨房端了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散发着生姜和红糖混合的香味。他对这种味道有一种久违的熟悉,小时候感冒了,母亲就是给他熬的这种汤呢。咕隆咕隆几大口喝下去,全身立刻汗如泉涌。妇人拿着一块干毛巾,不停地给他擦,额头、颈部、背上,她没有丝毫生分和犹疑,仿佛他们是一对老夫老妻,妻子在精心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情。乌去纱先生渐渐松弛下来,何况他的健康状况恢复得不错。
“你怎么进来的?”
乌去纱先生思考良久,终于决定第一个问题问这个,而不是“你是谁”。这么问有两个理由,第一显得他们之间已经很熟了,不需要问“你是谁”这样愚蠢的问题。其实他第一眼见到她就觉得面熟,马上又认定他根本不认识她,他的朋友圈子尤其是女性朋友的圈子实在太小了,她肯定与这个圈子没有任何关系,面熟只是缘于她超凡脱俗的美丽;第二因为这个问题才是最让乌去纱先生感到困惑的,买了这个房子以后,连他在乡下的老母亲都没有钥匙,装修公司那里的钥匙早已收回,难道她会是神话中的“田螺姑娘”不成?
“先生先养好身体。等身体康复了,再慢慢聊。”
她的声音太好听了,像是四川话,夹着陕西口音。乌去纱先生经常到全国各地开会、讲学,对各地方言颇有了解,反正她不会是湖南人。
“你是外地人?”
疑团太多了。乌去纱先生忍不住又抛出一个。妇人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娇嗔地说:“叫你不要打听呵,老打听就是赶我走呢。”
乌去纱先生当然舍不得她走,只好不再问,乖乖地听她的话,吃饭的时候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第二天,乌去纱先生可以靠在床上看书了,妇人就到书房帮他把书搬过来。乌去纱先生想,有这样的老婆陪伴一辈子,真是一种福气。我乌某哪里修来的福分,能得见如此貌美贤惠的妇人?
这天晚上,乌去纱先生半夜醒来。他在被子里伸伸手,踢踢腿,感觉好多了。他悄悄起床,开门,朦胧中,看见妇人蜷缩在客厅的旧沙发上,薄被横斜,楚楚可怜。外面清冷的月光映射进来,正好把她秀美的面孔渲染得如同梦境。他在沙发前蹲下来,拾着妇人露出被外的一段手腕,正准备放进被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把玩着。
妇人醒了。她并没有受惊,倒是乌去纱先生满脸尴尬,仿佛偷东西的时候被人逮了个正着。“先生,快去休息,你还没有复原,天冷,不要再感冒了。”妇人像带孩子一样,把乌去纱先生带到房里,让他躺在床上,帮他掖好被子,叮嘱他不要乱动,才出去。乌去纱先生听着她轻盈的足音,心儿蹑手蹑脚跟着她去了客厅,蜷缩进旧沙发上那床氤氲的薄被里。
等乌去纱先生睡过一觉,已经是大白天了,妇人下好鸡蛋排骨面在床边等着他。他的胃口越来越好,那么大一碗面吃下去,肚子竟然不是十分饱,但他很满足地抹了一把嘴巴,表示吃得很饱很过瘾,妇人绽开一脸灿烂的笑。昨晚的事,乌去纱先生心里还长着一个疙瘩,但看妇人的样子,静如止水,毫无芥蒂。
一晃又到了晚上。乌去纱先生躺在床上,想尽办法也睡不着。他回想以前在杂志上看到的如何催眠的文章,比如数数,从1数到100,他反复数了好几十遍都无济于事;比如想象自己到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他想象自己到了西藏、俄罗斯或者乞力马扎罗山,甚至想象自己到了唐代的长安,也只是徒添其扰,无法让身心安顿下来。夜晚愈益深邃、寂静,虽然并不是那么黑,但那偶然掺杂在黑暗里的微弱白光更使他像一艘在碧波中激荡的小船,它必须划到岸边去,到那里停靠下来。
他蹲在客厅的旧沙发前,妇人曼妙无方的身姿在薄被里起伏。这才是风景最优美的地方呢。他也成了这个地方的一处风景,他用欲望和激情衬托着这里的美丽与宁静。从他的血脉里跑出一头狮子,而不是小鸡。狮子四处逡巡,周围的花草虫鱼都能感受到它威猛的雄风。这都是乌去纱先生脑海中出现的图景。而现实状况是,他的一只手抓住旧沙发的边缘,就像上次搬书时怕滑倒抓住一根路灯柱一样,只不过上次抓住路灯柱的是右手,而这次抓住旧沙发边缘的是左手;此刻,他的右手像狮子钻进森林般钻进了薄被里。
狮子是森林之王,它在森林中总是能得到它想要得到的。乌去纱先生的手同样在薄被里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他深深陶醉在他的游历里,当偶然想到要去找一找这些优美风景的源头时,他蓦地看到妇人的眼角凝聚着一滴晶莹的泪水,那泪水以踊跃的姿势正待要滑向脸颊下去。他的手像遭到电击,慌忙抽了出来。
泪水滑落下去了。妇人坐起身子,她没有生气,依旧一脸平和。乌去纱先生像意识到做了坏事那样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妇人问道:
“你真的很想要,是吗?”
乌去纱先生的双手从脸上松开,就势抹了一把乌去纱先生的面孔,似乎是想让他更清醒一点。乌去纱先生红着脸大胆正视妇人的眼睛,以此表示自己的真诚,他嗫嚅道:“请原谅,你太美了!你知道,我有一年半……”
“我理解你。如果你真想要,我可以给你,但是当我给你之后,你将永远见不到我了。如果我不把身体给你,也许我们可以像现在这样相伴一辈子。你选择哪一种呢?我的先生。”
乌去纱先生怔住了。他没有料到会是这么难以回答的问题。
“先生,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天,明天这个时候给我答案好吗?”
接下来的一天,他们都很少说话。乌去纱先生表情严肃,但看不出他在深入思考问题的样子。他的连腮胡子时而翘得老高,时而耷拉下来,时而显得激情澎湃,时而显得老成持重。妇人仍然做着她的分内事,把家务一件件打理得井井有条。
乌去纱先生真正思考妇人提出的问题,是在晚上上床之后。他可能从内心觉得,任何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都不需要超过一个小时的思考时间。下面,他开始集中精力来解剖问题的每一个内核。
首先,如果选择前者,做一次爱之后再也见不到妇人了,相当于一次性消费,对于想搞一夜情的红男绿女来说,求之不得,既享受鱼水之欢,又不要承担责任,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可我乌去纱不是这样的人呵,如此貌美贤惠的妇人,做老婆多好,何况还是她自己送上门来的,免去了很多追求成本,于情合理,于利合算,乌去纱虽是个书呆子,也不至于蠢到现成的好东西都不要的地步吧。
如果选择后者,她愿意做老婆,但不愿意做爱。不过夫妻生活那还叫什么夫妻呢?即使我答应她,问题是,她那么漂亮,朝夕相处,我怎么忍得住?要是先答应,等她做了自己的老婆再动她,我乌去纱岂不成了寡信虚伪之徒!这样好的妇人,绝不能欺骗她,让她的心灵受到伤害。
哎,话说回来。也许根本没有这样复杂。她肯定是爱上我才来照顾我啊,她提出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想考验我而已,并不会当真。昨晚流泪?那也许是一种喜悦的泪水,她很可能同样很久很久没人爱抚了。西方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一致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渴望爱抚。乌去纱,要相信自己,更要相信她。你完全有能力让她快乐和幸福。你的资源闲置一年半了,你应该把这些优质资源在今天晚上统统利用起来,让她神魂颠倒,乐不可支。她哪里还会永远不见你呢?说不定三天不见就不行了呢。
乌去纱先生得意于自己的缜密分析,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漫布全身,把他武装得像一个雄心勃勃的圣斗士。他蹲在客厅的旧沙发前,没有过多犹豫,温热的手伸进了薄被的波浪里。顷刻,他又像被电击了一样——里面的妇人竟一丝不挂!他认为,这恰恰证实了他刚才的分析和判断。一缕得胜的、诡秘的笑跃上他的嘴角,他要尽情享受自己的战利品了。
妇人没有抵拒,甚至连羞怯都没有。而且她能够体会乌去纱先生的每一个意图,尽量迎合和奉承着他,让他在所有细节上都得到满足。乌去纱先生从来没有领略过如此美妙的胴体,从来没有沉迷于如此纵浪的欢爱。但他大脑的某一个角落,某一根迟钝的神经,却在告诫他:“我的主人,你在透支,这辈子全部的欢情和爱欲都被这一晚透支完了。”乌去纱先生隐隐听到它细如蚊蚁的声音,但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在潮涨潮落中跌宕起伏,他感觉自己快要粉身碎骨了,却依然在披荆斩棘,奋勇前行。
与其说乌去纱先生睁开眼睛,不如说他打开了眼皮。自然没有小鸡欢快地跑出来,黄褐色的瞳仁被大片眼白看管着,但它绕着眼眶使劲轮了几圈,周围的眼白便落荒而逃。他没有看见妇人。每天醒来,妇人都在他的视线之内,今天却没有看见。他霍然起身,客厅的旧沙发上空无一人,只有叠得整整齐齐的那床薄被。他走过去,薄被上放着一张粉红色的信笺,上面写着:
先生:
我走了,而且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永远不会再相见。我被你那天护书的行为所感动,你因此感冒了,我就决定出来照顾你。我承认,在照顾你的这几天里,我喜欢上了你,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陪你度过终生。但因为过去的不幸经历,自被小我九岁的元稹大人抛弃之后,在我心中,爱情和欲望早已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信任爱情,也不反感欲望,但我坚决不会再涉足混淆着欲望的爱情。
你肯定看过唐朝的诗歌史,认识元稹这个人。元稹在得到我的身体之前是真心爱我的,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那种虔诚和深挚能让山河变色。一旦我的身体在他面前一览无遗,我们之间便是欲望高涨,情爱淡薄,直至他喜新厌旧,掉头而去。我当初是很自信的,我想以我的柔情、才气和美艳,绝不会让男人从我身边跑掉。但我高估了自己,情爱可以绵长,欲望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只以新鲜感为标准。再美的姿色,也会让朝夕相处的爱人熟视无睹。我固执地以为,如果一个男人在爱你的过程中掺杂了欲望,那他必定会有辜负你的那天。
所以,我出了一个那么难的选择题给你。我知道这让你很难受,我也早早知道你会如何选择,但对不起,先生,我怕再被这种冲昏了头脑的爱情所伤害,而我只能选择离开。你读过我的诗,应该了解我的生平,尤其那些说出来至今仍令人黯然魂销的所谓伤心往事。我相信先生能够理解我,并不记恨于我。
薛涛留言
乌去纱先生读完这张留言,疯了似的奔进书房,书架第二层中间那格,《薛涛诗选》已无影无踪。原来放这本书的地方正好留下一个空档,像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
乌去纱先生旋即出门,跑遍城市所有的书店、门市部、地摊点和废品回收站,都找不到一本《薛涛诗选》。他突然记起,《薛涛诗选》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便通过114查询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电话,打了过去。他问,出版社是否还有《薛涛诗选》这本书。对方反问他,这本书是十几年出的,哪里还会有?他再问,那你们什么时候重印这本书呢?
对方颇不耐烦地答道:“都什么时代了,还出《薛涛诗选》,你要我们血本无归是吧!”说完,啪地挂断了电话。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