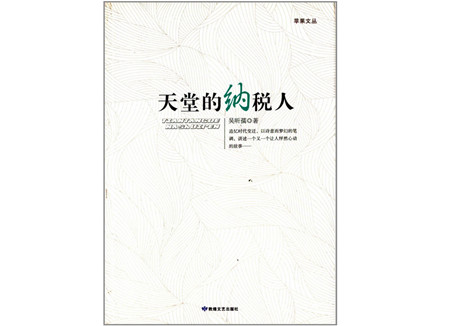
天堂的纳税人(小说集)
作者丨吴昕孺
梦中人
这几天晚上,老张连续做着同一个梦,让他挺纳闷。他活了四十八年,从没出现过这种状况。
以前也常做梦,那些梦都像梦,杂七杂八,拼拼凑凑,鬼扯腿一样。一觉醒来,往往只剩下支离破碎的印象,或者最后一个镜头的特写,其他的则成了一锅粥,煮在脑袋里,即便用上回忆的温火,那粥也是越煮越烂,横竖理不清个头绪来。
他似乎从未做过一个可以清清白白讲出来的梦。所以,平时在单位听同事说起、在家里听老婆说起、在麻将馆听牌友们说起,他们做出的那么完整的梦,说得头头是道、绘声绘色,他羡慕不已。
他很想做一个像故事那样好听的梦,为此他宁愿三天不打麻将,一周不跟老婆做那事。但那样的梦,就像千把块钱一桌的宴席对于他,始终是一种妄想。
自然,他也不会三天不打麻将,更不会一周不跟老婆做那事。
老婆比他小四岁,一周不做那事,她就会在麻将桌上揪他耳朵、扯他头发,骂他蠢得做猪叫。他要是状态好,打牌赢了钱,或者有人请他吃了羊肉串,有时一周能来三次,老婆一天到晚红光满面,笑脸迎人,好比赖在秋风中一顿乱开的菊花,样子虽只有那样好看,到底还算是一朵菊花。
十年前,老婆背了一麻袋毛巾,从毛巾厂下岗,在楼下开了一家小小的日杂用品店。那麻袋毛巾到现在还没卖完。
三年前,他从汽车电器厂内退,每周只要去一天,每月领六百块钱。这六百块钱,统统交给老婆,老婆当即返回一百,留着打一块钱的麻将。输光了就在麻将桌边看别人打,帮刚进场的新手当当免费参谋;如果赢了钱,就被允许和几个相好的牌友喝点小酒。
老张对这样的日子毫无怨言,唯一的遗憾是梦做得不够好。这一点,他真在其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有一天,好朋友老王说起他做了一个梦。他带领一个连队,是独立连,在湘江边上抗击日军。
老张说,只听说过独立团、独立旅,没有独立连吧?
老王斩钉截铁地说,我记得真真切切,就是独立连,我是连长。
老张只好不做声了。
老王继续说,日本鬼子真多呀,杀都杀不完,起码宰了他们一个团,后面还是密密麻麻地冲上来。这时,我的秘书对我说,连长,你快撤,我来掩护!
老张心想,连长怎么会有秘书?但他没说出口,他怕老王生气,老王一生气,讲话就喜欢吐唾沫粉子。有时那唾沫粉子罩你一脸,半天还干不了,又不好意思伸手去擦。
老王说到了高潮。我厉声告诉秘书,我是连长,必须身先士卒,怎么能退?我从腰上抽出砍刀,高喊,同志们,冲啊!就向敌人冲去,结果发现后面只跟着秘书一人,其他的都死了。我想起一个独立连,只剩下连长和秘书两个,即使把他妈的日本鬼子杀光,我这连长也差不多是个光杆司令了。我气得嗷嗷直叫。我老婆拍我一巴掌,说,你叫冤啊,叫叫叫,睡个觉都不得安宁。我回他一巴掌,你吵死啊,吵吵吵,你不拍老子,老子把那些鬼子都杀光了!
老王讲完,仰头哈哈大笑,那种豪迈盖世无双,还真有点独立连连长带着秘书的派头。
老张也伴着呵呵了几下,笑得勉强、尴尬,干巴巴的,是那种贫农对富农的赔笑,谄媚中灌满了嫉妒。
梦做不好毕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日子照样轻松、悠闲地过。打牌、喝酒。不多的心思,一边指望手气好点,赢几个钱;一边尽力维持着与老婆的一周一次。倘能达到一周三次,老张便乐不可支,觉得做国家主席可能也不过尔尔。
有时,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国家主席繁忙的外事活动,老张在心里问,他这么忙,一周能和老婆来三次吗?我就不信。
这话让他感到自豪,但他藏得紧。跟老婆没说过,跟老王他们也没说过。国家主席,可不能随便开玩笑。他偷着乐。
老张满四十八岁之后,大约不到半个月,九月初的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奇怪的是,从梦中醒来,那梦的过程历历在目,每个场景、每个细节都像刚刚发生的那么清晰、有序。
他从家里出发,向某一个地方走去。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走在一条马路上。马路上飘荡着纸屑、包装盒,滚动着矿泉水瓶之类,可见时间应是清晨,环卫工人还没出来打扫。风很大,纸屑被吹离了地面,打在他的裤腿上。
他无法走得更快,但他显然想走得更快一点。前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
终于,前面是个十字路口。路口停着一辆豪华大客车。白色的,圆顶,巨大的玻璃窗……仿佛是天下降落的不明飞行物。
他忽然明白,他正是奔着这辆大客车去的,他们好像被安排去某个地方旅游。他兴冲冲地跑起来,可当他马上要碰到大客车时,大客车“扑哧”一声,像发出一声冷笑,肩头一耸,向前驶开了。
他赶紧喊道:“等一等,还有我呢!请停车,我还没上车啊!”他无论如何使劲,就是喊不出声音来。客车越开越快。这时,有人从车窗里伸出头,并向他招手,意思是要他快些跑。
他跑得飞快,却不可能追上汽车。他被拉得越来越远。从车窗里伸出的头面目模糊,好像是他的同事们。
站在马路上,四周不见一个人。他气喘呼呼,仿佛把命都赔上了。好在这当口,他醒了,似乎极不情愿地睁开着眼睛——他不在马路上,而是躺在床上,对着黑乎乎的天花板发呆。
看不清天花板,但他知道他目光对着的地方是一块黄中带黑的污渍,污渍形状活像泡在水里的墨鱼。那是前年夏天停水,楼上小胡家开着龙头,一屋人去动物园玩了。不多时,来水了,家里没人,水漫金山,弄得老张家里像落雨一样,床上、柜子里全湿淋淋的。为这事,他老婆和楼上小胡的老婆好几个月不讲话,因为小胡和他老婆连声道歉都没有。
碰到这样的倒霉事,是个梦总要好受些。老张琢磨的是大客车没等他就开走的事。
他一辈子没旅过游。他最想去的地方是衡山。他想去衡山拜拜菩萨。倘若真的去了衡山,日子这么好了,拜菩萨求什么呢?求能去衡山吧,他已经在衡山了;求做一个完整的、能讲出来的梦吧,这个梦他也做了,而且就在今晚。多好啊,明天他就可以跟老婆和老王他们讲“梦故事”了。
虽然没赶上大客车是个遗憾,但总算能有一个梦讲给别人听,也不错了。人要知足。知足常乐。老张这样宽慰着自己,天就亮了。
早上起来,老张迫不及待地把昨晚做的梦讲给老婆听。不料,老婆听了非常生气。她不是生老张的气,而是生老张同事的气。她怪他们不等他,看见他来了还开车走,明摆着要甩掉他,都是些没良心的东西。
老张讪讪地说,我没看清,也不见得是我那些同事,他们跟我无冤无仇,甩掉我没必要啊,又不是多一个人坐不下。
老婆扯开嗓门叫道,不是你那些同事还会是谁?你除了去厂里,没走出过这条街,未必是老王、老李、老孔他们啊,你们打麻将总凑在一桌,他们会撂下你吗?
老张觉得老婆把一个梦看得这样认真,生这么大的气,有点没味。到底是女人。他不和她一般见识。想起这一周还没来一次,他估计老婆的情绪可能与此有关,便低着头、弯着腰走出了家门。
他到了老王家。老王颇为吃惊。老张很少串门,他们扯谈聊天不是在麻将馆,就是在街尾“盼盼南食店”门前坪里。一瓶啤酒,一碟花生米,扯一个下午。要是落雨,就从坪里移到店里,继续扯。扯得没东西了,也闲坐着,把屁股在凳子上扭来扭去,仿佛不停地拧一颗松了的钉子,怎么也拧不紧。有时叹几口气,打几个哈哈,让时间像气体一样挥发掉。
跑到家里来了!老张必是有国家大事以上的要闻相告。老王甚至有些紧张,筷子上夹着的一粒油炸花生米趁机逃脱,滚到饭桌下面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老张请坐。倒茶。东风还是西方,把老张你给请来了,没“9·11”吧?要不,汶川又麻烦了?
老张坐在一张资深谷牌凳上,接过茶,又起身放到饭桌上,脚伸过去,不小心把从老王筷子上逃出来的那粒花生米踩得粉碎。
“我做了一个梦。”老张喜滋滋地说。
“一个梦?从没听你说过梦呢,说来听听。”老王放下筷子,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好像在说,来客了,我不管你了。
老张便把晚上做的梦原原本本讲给老王听。老张讲完了,老王还做出一副没听完的样子。老张只好说,讲完了。老王嘴一张,就完了?老张说,是的,完了。
老王叭嗒了一下嘴巴皮子,不屑地说,这梦有么子味,没得一个屁久。
老张面露愧色:“是没得味,但也有点怪啵?他妈的明明看见我快到了,车却开了,而且越开越快……”
老王若有所思:“如果按《周公解梦》,你可能是得罪什么人了,有人要报复你。”
“厂里每周去一天,报个到就回了;平时我没出过这条街,想得罪人都没机会呢。”老张两手一摊。
老王手往腿上一拍,豁然开朗:“那就算了,反正是个梦,你又没损失什么。随它去吧,那些人还不是都从你梦中消失了,但你能醒来,醒来了你还是一条好汉。你一醒来,不等于把那部大客车掀到山崖下面去了,不等于让车上的人都死光光了。”
老张认为老王说得有理,心里释然。
接下来的两天晚上,都重复了这个梦。唯一增加的细节是,老张临出门前,老婆催他快点走,怕赶不上。所以,他一出门、一上路就像飞一般地跑,路上依然空无一人,只有纸屑和矿泉水瓶,围着他的裤脚打转转。
豪华大客车依然停在那个十字路口。在他快要到赶到时,它一声冷笑,肩头一耸,扬长而去。有人从车窗里向他招手,面目模糊。他不记得他骂了一句“操你娘的”没有。更大的可能是,他想骂,还没骂出口,就醒了。
他有些懊恼,不为没追上那车,而是为没骂得出那句“操你娘的”。他没跟老婆说,怕老婆神经质;也没去老王家再唠叨这个梦,怕被人齿笑。他只是暗下决心,如果晚上再做这个梦,他一定要把那句话狠狠骂出来。
整个白天,他心思全在那句骂上,叮嘱自己无数遍。从吃早饭起,他的嘴巴仿佛鸡啄碎米,叨个不停,听不清他叨些什么,老婆听不清,他自己也听不清。老婆把面碗往桌上一顿,呵道:
“你脑壳进水了呗?喊你端面半天不应,两片嘴巴皮像抽风。莫装成这熊样,老娘可不吃这一套!”
老张正在心里训练“操你娘的”。任老婆吐词如何快,他也能迅速调出一个个“操你娘的”,精准地卡在她的每一个字之间,给她以迎头痛击。当然,老婆听不清,他自己也听不清。他体会到了意念的奇妙。
上午打牌,他一双手臭得像茅厕板,一连给老王放了三个大炮,不仅让他小七对、清一色,自己去开杠竟然把那朵杠上花送给了他,一眨眼,三十几块钱从腰包里滚滚流出。虽然,每放一炮他都骂一句“操你娘的”,可老王赢了钱,不计较这个。如果能一路赢下去,背时老张一路操下去,他也会乐呵呵的。
老张没那么蠢,熬了两个多小时,后来自摸几把,一盘点,输在个位数之内了,赶紧起身把位子让给如饥似渴的老孔,怏怏而归。
可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让白天的一切亏损、失落都变得毫不足惜。老张照例做了那个梦,当他快要赶上豪华大客车时,豪华大客车发出一声冷笑,肩头一耸,扬长而去。老张追呀,追呀。大客车越开越远。这时,老张冷静地停下来,用尽全身力气喊道:“操你娘的!”
他还清楚记得,停下来之后、用力喊之前,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快喊,快喊,再不喊,就会醒了!
果然,他喊完,就醒了。
老张睁开眼睛。夜幕调集所有的黑暗,也遮挡不住他脸上哗哗流淌的笑意。不仅眼睛开着,他的嘴巴也咧开了,两只鼻孔也撑开了,一对耳朵也支开了。脑袋上,城门悉数洞开,跑出一支又一支快乐和得意的队伍,消灭了黑夜。
早晨起床,老张在老婆面前神气活现,跟昨天比,像换了个人。老婆阴着脸:“昨天输那多么钱,神气个屁!”
这个星期只顾着和梦作斗争,把老婆晾起了。来了一次,还有点马虎,加上输钱,老婆生气自有她的道理。老张态度良好地跟老婆赔着笑脸,这些笑脸得来全不费功夫,都是昨晚快乐和得意的余波。
吃了一大碗辣酱面,老张心里热乎乎的。他抹了一把嘴巴,擤掉辣出来的一串清鼻涕,朝门外走去。
他没有去麻将馆,没有去“盼盼南食店”,更没有去老王家。
他碰到老孔,老孔问他打麻将去不。
他摇摇头,说,有点事。
他径直向西走出了街道,再往北拐。
他到了江边上。这里没几个人,除了一些正在晨练的老太太、老爷子们。
他往北走,不急不慢,走得轻快而有节奏。宽阔整洁的江边大道随着他的脚步向前延伸,仿佛是他用脚走出来的。我要一直走到美国去,这条路也会通向美国。他不自觉地挺起腰杆,头微微昂着,步子更匀称、更有力,好像真要这样一直走到美国去似的。
隧道口拦住了他的去路。去美国得先穿越这条隧道,再往前走。隧道刚建成不久,上个月,他看了电视新闻,通车那天,市长来剪了彩。他还有点纳闷,这么快又换了市长。第二天打牌,跟牌友们说起,老王嘲笑他:“换了快一个季度呢,你才知道?只在自家屋里打屁,听不到外面打雷。”
他突然很不喜欢这隧道,便无意一直走到美国去了。正好有条斑马线,他横过马路,真正到了江边。
这是他小时候玩得要不要的地方。这里每株草的位置,每颗鹅卵石的形状,太阳升起和落下时光线的明暗度,他都一清二楚。但现在,完全不同了。那些野草被拔掉了,换成了绒毯一样的进口草,他不认同那是草,那只是地上长出的一层汗毛,哪里有那么齐斩斩的草,没道理啊!他童年时玩的鹅卵石好大一颗,如今越长越小了,江边很难看到一颗像模像样的鹅卵石,都是些不堪蹂躏的碎石和砂砾。
江没有小时候感觉的宽了。两边建起很多高楼,密密麻麻,把这条江夹在中间,以前在江这边能看到那边的山,现在只看得到楼。山在楼的后面,就像美国在隧道的后面,只不过美国可能远一点、山近一点罢了。
堤也高了很多。以前每到春天,江水会漫过堤岸,跑到他们院子里去。大伙儿纷纷卷起裤腿,提着网兜、铝桶之类的,跑到水里去打捞上面漂下来的拖鞋、衣物和鱼。水大的时候,一楼都被淹掉;待水退,某家水缸里或许会留下一条鲤鱼或一只乌龟,引得街坊邻舍围观。
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多年前就没有了。现在,人们一年四季都在麻将室吆喝喧天,几个小钱从这个荷包转到那个腰包,又从那个腰包流到这个口袋里。每个人都迷醉在这种游戏里,读书人叫他“国粹”。他不懂,他只晓得和街坊邻舍一样,吃了打,打了睡,睡了吃,吃了打。他们的日子就是这样打发的。
他有好多年没来过这里了,算起来走路还不到四十分钟。今天,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老孔喊他打牌,他说有点事。其实,啥事都没有。
他坐在一条水泥凳上。这是江边专供行人休息制成的长凳,离他几米远,长凳的那头坐着一对情侣。乍看,是一个人,好胖好大、忧心忡忡的一个人;细看,是两个人,抱在一起,快快乐乐的两个人,女孩的头埋在男孩怀里,男孩的手臂盘着女孩的腰。老张怕打扰他们,又移了两屁股远;再移,就要跌到凳子下面去了。
老张要求自己不去看那对情侣,而是看着江面。江面有五六只挖沙船。有两三只鸟。有一抹风,正对着他吹过来。
为了把不去看那对情侣的要求落到实处,他回想起这几天的梦,尤其回味昨晚那声痛骂,仿佛一颗炮弹,射向无情无义、不诚不信的大客车。“操你娘的!”他摸拟了好几遍,感觉都不如在梦中那般有冲击力。
可是,老张转念一想,既然我在梦中能告诉自己“快喊,快喊,再不喊,就会醒了”,那也完全可以跟自己说“不要追了,去不了没一点关系,反正是在做梦”,这不,连骂人的劲都省了。甚至还可以提前到出门前,我索性告诉自己不要去了,起那么早干什么,留在家里睡觉岂不更好!
老张恍然大悟,哦,自己到河边来,原来就是要想通这件事的。任务圆满完成,他起身,拍拍屁股,高兴地回去。走的时候,特意路过那对情侣,瞟了一眼,现出一种不可言喻的优越感。
效果出奇地好。晚上在梦中,当老张追赶那辆豪华大客车,大客车越开越远,他正要对着大客车的屁股痛骂那句“操你娘的”时,他突然冷静下来,对自己说:
“不要追了,去不了没一点关系,反正是在做梦。”
说完,他就乐呵呵地醒了。醒来已是早晨,老婆在厨房里煮面条。他走进厨房,想向老婆汇报他的最新成果,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一方面担心老婆不信,反受她的奚落;另一方面看能否把这个梦控制到不出门再说,那就是更加伟大的胜利了。
接下来几天,老张发觉,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入梦境,老婆就催他快走,他也急不可耐地沿着那条满是纸屑和矿泉水瓶的马路向前走,很像他平时去上班的东风路。那个十字路口,应该是东风路与解放路交叉的地方,距离他所在的汽车电器厂只有五百米远。这让他相信了老婆的话,坐在客车里向他招手的那些人是他的同事。
我平时从没得罪过谁呀?他们干吗偏偏丢下我呢?是我穷,还是地位低?我们厂像我这个样子的多啊……
不要胡思乱想,老王做了噩梦时总说,梦是反的,做噩梦有喜事来。不过,他做美梦就不这么说了。
唉,反正是个梦,犯不着去计较,又不是真的。老王做那么多当独立连连长的梦,还带着秘书,一觉醒来,还不是只能去麻将馆当“条子连”连长,带着“幺鸡”那只丑不拉几的秘书。在梦里,即使让我上了那辆大客车,它不成真能把我运到衡山去?
如此一想,老张心里更加释然。每晚照例做那个梦,他总是能在追不上大客车的时候,让自己停下来,平静地告诉自己,去不了没关系,反正是做梦。
他把这一套玩意操练得游刃有余,每一次都成功地将梦里面豪华大客车的傲慢与歧视消解于无形。他决定,明天一定要好好跟老婆和老王讲讲自己的梦,他几乎能把这个梦倒背如流。他们若相信,会对我心生佩服;若不信,那也是嫉妒我,就让他们嫉妒去吧!
可能是因为明天要讲梦,晚上的梦竟然多了些内容。
他梦见天未亮,老婆猛地把他推醒,对他说:“我忘了件事,昨天下午你们厂里捎信来,说今天要组织内退的职工去衡山旅游,六点钟在东风路与解放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上车,过时不候。现在五点多了,你快起来,怕赶不上。”
他迷迷糊糊起床,从家里出发了。
他凭感觉走上东风路,也是他每天梦里出现的那条马路。马路上飘荡着纸屑、包装盒,滚动着矿泉水瓶,环卫工人还没出来打扫。风很大,纸屑被吹离了地面,打在他的裤腿上。
他奋力想走得更快,效果不佳,风不是抱住他的腿,就是搂着他的腰。
终于,他看到前面十字路口的大客车了。
他不由自主地跑起来。那辆大客车忽然肩头一耸,开动了。
他边跑,边喊:“等等,还有我!等等,我还没上车呢!”
大客车越开越快,越开越远。奇怪的是,这次没有人从车窗里伸出头来,更没有人向他招手。
他停下来,气喘吁吁,显得比往常累,也比往常着急。但他还是冷静地对自己说:“去不了没关系,反正是在做梦。”
更奇怪的是,这次说完这句话,他没有立即醒来。
他仍然站在那条路上,前面是大客车消失的一个大拐弯,后面是那个欺骗了他无数次的十字路口。
他回过头,仔细瞅着。不对,以前梦里的那个十字路口只有草,没有树,更没有这么茂密的法国梧桐……
这个才真的是东风路与解放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啊!
他转过身,怔怔地看着前面。不对,以往梦里的豪华大客车是直直地向前走,这次却是走了一段后拐一个大弯消失的。那个弯是解放路通往城市南郊方向的,从那边出城,就上了去衡山的107国道。
老张猛地举起手,一掌拍在身边法国梧桐沧桑的树干上,痛得他直打哆嗦。他全身颤抖着,在城市淡薄的晨光里,痛哭失声。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