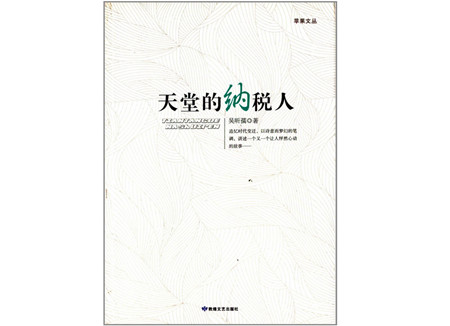
天堂的纳税人(小说集)
作者丨吴昕孺
秘 密
老头没想到午睡醒来,身边老伴不见了。
这么多年来,无论晚上还是中午,他们休息时总在一起,就像组成一个词语的两个字,比如“夫妻”、“恩爱”、“幸福”等。他们这辈子,或许受了很多苦,有过很多分离,走过很多地方。但一到晚年,曾经受的苦都平淡了,曾经有过的分离都弥合了,曾经走过的地方都消失了。甚至连那些引起无数作家们牵肠挂肚、魂飞梦绕的童年啊、故乡啊、大海啊、草原啊,在他和老伴眼里,都不算什么。他们仿佛一出世就是七十岁,就有乖巧的一子一女,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节日快乐,哦,对,天天像过节一样;哦,不,每一天都是节日。刮风下雨,落雪结冰,日出日落,月明星稀……每一个日子换上不同的布景,变成不同的节日,其实所有的节日都是相同的。所以有时候,后台的人(西方人叫它上帝)偷懒,十几个或者几十个节日都是同一种布景,比如下半个月雨,比如出一个月太阳,他们也懒得管。老头和他的老伴,只管在生活大舞台的一个小小角落,缓缓推进着自己的晚年图景。屋后山上的泉水就是他们的大海,校园的中心广场就是他们的草原。童年和故乡呢?并不远,只有打一个盹的距离。
老头年轻时走南闯北,有自己想跑出去看看的,有被别人抓了去的,有不得不去出差的。有一次,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吧,有人铐住他的手脚,用一块黑布蒙着他的脸,把他推到一辆车上。四周全是黑暗,他自己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所有的声音、气象、物质,包括其他人,都被黑暗虚拟成一道模糊的光亮,他看到了,不是眼睛看到的,是通过黑暗看到的。很奇怪,在黑暗中,反而能看到那么多东西;更重要的是,能看清一些在光明中看不清楚的东西。嗯,这里应该举个例子,比如用黑布蒙住他脸的那个人,他看到他的脑壳里有一团紫红色、像西瓜瓤一样的球状形物质,那个紫红色的球安睡如初生的婴儿。能看得这么清,他感到很震惊。从此,黑暗与光明的对立意义在他的心目中完全消解,他养成了每天晚上关着灯在黑暗中静坐一会的习惯,他觉得这是他一天最明白的时候。那一次,他后来被人推下车,走进一间屋子。在走进那间屋子之前,拐了无数道弯,他开始还记着,左,右,左……弯到他实在是记不住了。按他的体会和估测,拐那么多弯至少应该去了一趟祖国的边陲,他甚至有一种远行的兴奋感,大大冲淡了他离开老伴的孤独感,那时他们结婚不到半年,还是新婚夫妇呢。他和老伴是初中同学,接着是高中同学,然后是大学同学。从很早的时候起,他们就结成伴儿,早晨一起去上学,白天一起在课堂里,傍晚一起放学回家,晚上经常在一起做作业。“一起”这个词,被他们赋予了无穷的含义,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从而远离了政治的碱化和爱情的酸化。“一起”,好比童年时故乡村口那株古老的枫树,谁都望得见它,谁也没有认真端详过它,它无时无刻不在那里;可现在它早已不在了,它和老伴“一起”被移植进了他的心坎——它不在村口并不意味着它的消亡。如今,谁都望不见它了,可他每天都会认真端详它,它的每一条枝桠、每一片树叶以及每一根经脉。它们构成了“一起”这个整体,是老头和老伴必不可少的生活元素,虽然他们再没有回到过那个村庄。
从这所学校一个较高级别的职位上退休后,他到哪里去都要老伴跟着,或者是跟着老伴。有人笑他,他不管。在他看来,那种笑,很像村里的无知少年拼命地摇晃那棵枫树,摇得它不得不落下一些枯叶,却对它的根基毫发无损。更多的是另一些人,他的朋友,尤其是他的学生,得益于受过他的教诲而成才的,他没有教过他们什么,或许是他记不清教过他们什么,但如果他们认为这对他们的成才很有用,他也乐于接受“恩师”这一称号。他们盛赞恩师与师母纯真、深挚而永恒的感情,有人写文章标榜他们是“神仙眷侣”。他逐字逐句地读了那些文章,不置可否,也没有会心一笑。活了七十多年,他太明白,生活是一回事,写文章是另一回事,生活做不得假,写文章却当不得真。作者花了很多笔墨,用了很多词汇,写出了他们眼里的“恩师”,但是,他们写的不是真实的生活。这怪不得他们。生活从来不会钻到某个人的笔下,它是敞开的无边无际的原野,是四面八方,是阴差阳错,是无限的可能。文字好比漂浮在水面上的几片树叶,而不是矗立在水边的大树,因为生活本是茫无际涯的。他一直很想把那次被人蒙着黑布、铐着手的远行经历写下来,每次想写的时候,胸中便涌荡着一股如火的激情。遗憾的是,每次拿起笔没写下几个字,他便掷笔长叹:文字无法再现生活;一旦写出,便是另外的生活了。那次远行,其实是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行动,当有人解开他脸上的黑布,他眼前立刻有一大堆银子在跳舞,跳的显然是“忠”字舞,银光闪闪,原驰蜡象,他的心里猛然敲起了鼓点。过一会,舞蹈停止,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仍然在学校礼堂的舞台上。有人要他跪下来,他不愿意。一辆黑色的微型坦克轧过他的腿关节——那个学生踩过他之后,还用手掸了掸皮鞋上的灰尘,很恼火地认为他把他的皮鞋弄脏了。这位被斗得差点落下残疾的“现行反革命”,十年后变成了这所高等院校的副校长,变成了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这是什么“神仙眷侣”呢?患难夫妻就是患难夫妻,不要拿神仙来说事,不要用神仙二字去勾兑过去的苦难,变成一杯味道别扭的鸡尾酒。老头不计较过去。那位踩他的学生,后来跪在他面前,请求他的宽恕。老头随手捡根柳枝充当鞭子,在学生背上狠狠地抽了一鞭,说,我们两清了,你去吧。看着学生离开的背影,好像一册发了线的书,掉了一页,他哈哈大笑。他仍然想拾起这一页,塞进书里,再好好装订,让它成为一本完整的书。
老头没想到午睡醒来,身边老伴不见了。
即便这样,他心里也有底,老伴不会出事的。这么多年来,什么狂涛骇浪没有经历过,什么牛鬼蛇神没有见识过,什么暴风疾雨没有承受过。不是好好的吗?一切都好好的,每一天都像任何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分不落、一秒不差地过着。他摸了摸那边,老伴睡的地方还温温的,散发着一股独有的气味。他的一生都充盈着这种气味。他想,哪怕他是一只动物,不会说话,不会思考,只要他能闻到老伴的气味,他就会安静、踏实下来。窗外的泡桐树忽然开满了花。树上没一片叶子,花就到齐了,在树枝上推推搡搡,闹成一团,有的花不慎掉了下去,惊得麻雀子使劲地叫喊。老头把身子俯在窗台,伸出头,目送一朵掉落的花跌到地上,花与地相接触的刹那,他的心里猛然敲起了鼓点。花却是那么平静,扑进了大地的怀抱,花一定熟悉大地的气味。但我心里怎么敲得这么响,心脏似乎要跳出来了。不对吧?不是心脏,是什么东西在响……呵,电话!电话响了,莫不是老伴从外面打来的?
老头赶紧到了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拿起话筒,他像在家里和老伴说话一样,“喂!”随意而短促。
“喂——”对方是男中音,拖得很长,嗓门仿佛用一块砂布刚刚擦过,故意露出锃亮。
“你找谁?请问。”老头回过神来,很是失望,但不想失去礼貌。
“你是Z校长呗?”
“我……退休十多年了,什么校长,你是……”
“我呵,是你的一个老朋友,你肯定不记得了,贵人多忘事。好多年没联系了,还好吧?”
老头稍作迟疑,脑子里迅速掠过一些熟悉的图像,他认为算得上老朋友的。这个过程并不需要很长,这一下他惊讶地发现,虽然活了七十多年,但真正算得上老朋友的,屈指可数。岁月是一把无情的筛子,筛得越久,留在筛子上面的“老朋友”就越少。在他看来,永远筛不下去、永远留在筛子上的,只有老伴,那个初中时就陪伴在他身边的小个子女生。以前是小个子女生哦,他们一起在舞台上表演过《兄妹开荒》,现在长胖了,胖得……
“喂,你在听吗?”那边问,因为急切,中音陡然变成高音,拖长的腔调被拦腰截断,仿佛一个在悬崖边玩耍的孩子,不小心掉了下去。
老头心里一惊,仓促地应道:“呵,在听呢。你说。”
“我晓得你脑子里在想我是谁,哈哈,想不起来吧。我是你的老朋友呢,好多年没联系了。后来我做了几年生意,实在是没时间。”
对方猜对了,老头的确在想这个老朋友是谁,他无法跟他脑子里那些一掠而过的熟悉图像对号入座。他的声音耳熟,仔细听却一点也不熟;以这么多年的阅人经历,他听其声音似可想象出其神态面貌来,这面貌眼熟,仔细一勾勒,却是那样的陌生。应该不是什么老朋友,可能是很多很多年前在餐桌上见过一次面、聊过一次天的这类“朋友”吧。
“最近好吗?”那边恢复了男中音和悠长的腔调。
老头立起身子,调整了自己的坐姿。电话经常也是一种博弈,他见得多了。可他现在完全进入了对方的话语圈套,跟着对方的节奏走。他想尽快结束这个电话,便说:“还算好,你有事吗?”
“还算好?不要自我安慰了,一个人有什么好!”
老头更加吃惊,这家伙真神,他怎么知道我正好一个人在家?难道他看见我老伴出门?或者,这是楼上楼下某位老年痴呆症初期患者打的恶作剧电话?不会呀,我这是最顶楼,没有楼上;楼下几位七老八十的,都不是这种声音。对方继续在说,先听听他的:
“老Z啊,我们都是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要想得开,要学会享受生活。”
老头有些发懵,我一个人在家与想得开和享受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老伴丢下我跑出去,怎么会是我想不开, 也绝对不会是她想不开。他云里雾里地接上一句:“我才想得开。”
“想得开就好。你老伴走了有三年吧,一个人冷火消烟的,崽女难得回来。你以为我们好多年没见面,我就不关心你了,我经常从朋友们那里听到你的情况,了如指掌呢!”
老伴走了三年?他是什么意思?老伴分明在我身边!这人到底是谁,拿腔捏调的,我没一个这样的朋友啊。他经常从朋友们那里听到我的情况,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提供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他意识到必须马上打住了:
“我不是一个人……”
“哈哈,请了保姆啊?请保姆不是长远之计,保姆又不能共被窝暖脚!再说,请保姆很不安全。我一个同事,也是老伴死了,从乡里请了一个保姆,五十多岁,开始蛮尽心,性格好,勤快,哪晓得搞了不到一年,把家里的钱财洗劫一空,跑了,气得我那同事吐血……”
“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你是谁,也没有一个你这样的朋友。我老伴下楼买菜去了,等会就回来,我要做饭了。再见!”
老头把话筒重重扣在电话机上。他的心里急骤地敲起了鼓点,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他张开双手,劈开两腿,整个身体仰躺在沙发上,仿佛一条晾在沙滩上的鱼。从来没有感觉这样虚弱过。哪怕他被蒙面送到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哪怕他挨斗时跪在舞台上,哪怕他被押到五七干校一年没见过老伴的面,他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害怕和绝望。
门铃响了。他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动物,霍然而起。打开门,老伴笑吟吟地站在外面,两只手里全是菜,烤鸭、鸡蛋、排骨、豆腐、西红柿、胡萝卜、茄子,全是他喜欢吃的菜。菜里面夹着一只他最喜欢吃的菠萝——削了皮,露出金黄色的果肉和用刀斜着切出的一轮轮花纹,香味顿时像浓雾般弥漫开来。
老头扑上去,一把抢过老伴手里的菜和水果,扔到客厅的地上,他用劲将老伴扯进屋里,关上门,抱着老伴眼泪直流。老伴连忙问:“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老头的脸在老伴的胸部擦了擦,语无伦次地说:“平时你不这样出去的,为什么一个人出去不和我打声招呼?”
老伴说:“就为这个哭啊,傻呢!儿子明天过生日,你忘了?我要他们一家三口回来吃饭,去买点菜。你今天中午睡得好香,没叫醒你。”
“答应我,以后我们只能一起出去,无论我睡得多么沉,你也要叫醒我!”
老伴抬起手,贴到老头的额头上:“你没发烧吧?说起胡话来了。”
“我是认真的,你赶快答应我!”
“好咯,好咯。”老伴一边捡起客厅里的菜,向厨房走去,一边叹道,“哎,老小老小,真是越老越小。”她胖胖的身体像一道缓缓移动的山脊。
这个可怜的老头,一辈子活到七十多岁从未背着老伴有过什么秘密,而现在,他不得不拥有一个小小的秘密了。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