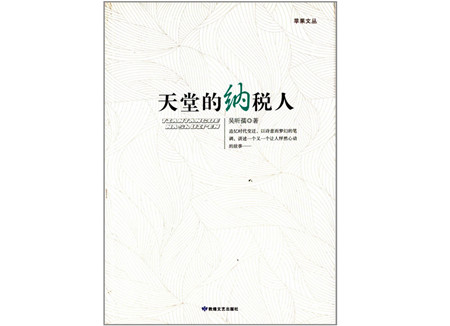
天堂的纳税人(小说集)
作者丨吴昕孺
天堂纳税人
去年秋天,我搬进了城市北郊、临近浏阳河的四季美景小区。看中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浏阳河一衣带水,从阳台前飘然而过。我太喜欢门前有条河的感觉。曾经住在城市中心,城市的心脏是由钢筋水泥制作的,有足够的承受能力;但人心是肉长的,住在那样喧嚣、动荡的地方,实在受不了。我每天都不想待在家里,你坐着只听到周围全是下水道的声音,仿佛那些下水道是插在你身上的管子,由它们给你输氧、输血、输你赖以生存所需要的一切营养。你每天就是这么一个全身布满管子的人,一个生命垂危之人,一个上气不接下气之人,一个无法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连书架上的书籍们都死扬拉气,无精打采,你好不容易把它抽出来,想翻到某一页,它硬是不让你翻过去,不是落到你所要那页的前面几页,就是落到那页的后面几页。按理,距离你要的那页很近了,可你朝前或者往后翻,手指蘸着口水,搓掉一层皮,那一页还是躲在其他页码里面,死活拽不出来。有一次,气得我用力把书一扯,哎,手上撕下来的那一页,正是我要的。这好比我要从鸡屁股里掏出一个蛋,却不小心要了鸡的命,那种沮丧与愤慨简直让我抓狂。
搬迁势在必行。我跑遍长沙市的东南西北四郊,最终定下了这个“四季美景”小区。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因为我现在可以安心坐在家里看书和写作,享受岁月静而姝好的时光了。若有疲累或不适,我便打开封闭阳台的窗子,浏阳河款款从东边流过来,它虽然已经走了几百公里的远路,但依然从容有致,风度翩翩,它的色彩、声音和姿态所形成的巨幅画面走进我的房间,成为房间里的风景。我再不受下水道的压迫了,站着与浏阳河对视的时候,那些下水道仿佛是簇拥在我身边的童子,好不威武。
住在这么好的地方肯定得付出一定代价。除了付给房产商二十多万白花花的银子之外,另一个问题是这里暂时不通公交车。我上班必须步行走完小区西边一条路的全程,才到达一个公交站,然后坐上能到达单位的807或143路。这条大约1500米的路在一个长而陡的岭上,故名陡岭路。出门从小区到公交站是上岭,回来从公交站到小区是下岭。我通常清早七点起床,五分钟穿衣、洗漱;十分钟吃早餐,以稀饭为主,前一天晚上母亲熬在紫砂电炖锅里的。七点一刻出门,从小区大门左拐二百多米上陡岭路。沿陡岭路向南走五十米,是浏阳河大堤,这是我周末、假期在家时傍晚散步的胜地。平日上班则没有这种雅致,得往北先上那个陡岭,陡岭两边是两道山壁,嵌着拼成各种几何图案的石头,山壁上隐约可见几栋民居,在树林中遮遮掩掩,仿佛窥视城市生活的密探。到了岭上,虽然岭仍在缓缓继续,但已平坦很多,再说路长,与走平路无异。
陡岭路两边是密集的厂区和店铺。西边自北而南,依次是:长沙第二机床电器厂、博爱社区医院、英子专业美容美发店、世华饭店、长沙光华织带总厂、佳佳超市、养天和大药店、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陡岭路生产基地、陡岭路派出所。
东边自北而南,依次是:长沙正盛特种活塞环厂、湖南省金鼎消防器材厂、福泰家菜馆、长沙胶鞋厂、奇志装订厂、陡岭建材商店、浏阳蒸菜馆、白香炒货店、长沙铝制品总厂、创新废品店、开福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
这些地方有个特点:凡店铺都热闹非凡,亲热调侃笑闹者有之,吵嘴推搡斗气者有之,其声势不亚于教授学者们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和西方政要参加的议会;凡工厂大多寂寥无声,各家厂门关着,留传达室一扇小门,里面坐着无所事事的老头,身高、长相、穿着、说话的腔调几乎让你觉得他们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爹娘生的。这些工厂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大多无计可施,处于关停与半关停状态。像西边的长沙光华织带厂,厂牌旁边还挂着两块更新、更洋气的牌子,一块是顺兴进口汽车修理厂,一块是湖南媲美印刷有限公司,三块牌子挂在一处,好比成群的妻妾,妻已年迈色衰,妾却光彩照人。无独有偶,东边的长沙胶鞋厂也被一家汽车修理厂和一家印刷厂占领,这年头还有谁穿胶鞋?但开汽车的和印书的可比浏阳河里面的鲫鱼都多得多了。
我偶尔出门比往常早,加上天气好,心血一来潮,决定走路去单位,便早早地横穿马路,行走在陡岭路的西边,过陡岭路派出所,右拐穿到伍家岭立交桥,五十分钟后可坐在办公室。但绝大部分时候,还是走陡岭路东边,在开福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门口左拐到九尾冲公交站,坐807或143路公交车,二十分钟后单位在望。不管如何,陡岭路这千多米的距离只能用脚来丈量,小区刚开张,住的人少,出租车更少。当然,天天坐的士上班,我还不会那样打肿脸充胖子。“摩的”倒不少,都是无牌无照的黑色经营户,我从没有朝他们热切的目光里砸进过一枚硬币。
那天,我照例走在陡岭路东边,手提公文包,以比正常人稍快的速度走着。快要到金鼎消防器材厂门口时,看见一个老头也以比正常人稍快的速度迎面向我走来。
金鼎消防器材厂是陡岭路诸多工厂中最大的一家,我们单位墙壁挂的、墙角放的消防器材上,统统写着“金鼎消防”字样,那个像一团火一样的徽标我更是熟视无睹了。金鼎消防器材厂的厂门在陡岭路也最气派,约十多米宽,电动闸门像一条断腿蜈蚣,拼尽全力地耸来耸去,但总在原地,没挪动一寸。老头不是从厂里出来的,他也是沿陡岭路过来的,只是方向与我相反。所以,他不见得是金鼎消防器材厂的人,很有可能是长沙胶鞋厂或者长沙铝制品总厂的人。但自从我那天注意到他,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和他都差不多在相同的地点擦身而过,也许从我走在陡岭路上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这种游戏。
我为什么要说是一种游戏呢?我认为,游戏应当是两个人以上(含两个人)共同开展的活动,一个人自娱自乐不能算作游戏,因为无法实行规则。游戏实际上是一种同谋关系,它必须在共同制订的规则下才能运作起来。我和老头虽然互不相识,可我们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相遇,无形之中构成了一种同谋关系。这种本来无意识的行走,在这一地点、这一时刻便演变为一个斗智斗勇的游戏。
老头个子与我相当,身胖,头圆,秃顶。上穿一件焦黄色夹克,里面是衬衣;下穿卡其布蓝色裤子,裤管较大。脚穿一双胶鞋。我们叫“解放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不管男女老少,脚上几乎都是这种鞋。我小时候穿烂过好几双。现在已少见如文物,他的脚上竟然有一双。他穿着那双鞋,健步如飞。我据此认为,他更可能是胶鞋厂的退休工人。在来来往往、慢慢悠悠的一大群人中,我们两个一看就知道是异类。这也是我能从人群中发现他的原因。当时他大步流星向我走来,瞧那架势,我以为是来找麻烦的。我下意识放慢速度,稍稍侧身,靠在绿化带一棵臭皮柑树后面。他没作丝毫停顿,大步流星走过去了,经过我身边时,眼角似乎有意无意瞄我一下,很快收回去,一眨眼走得远远的。
第二天早晨,我又在快到金鼎消防器材厂门口时,看到他敏捷的身影。我想,不避让了,索性硬碰硬。他低着脑袋,我则高昂着头。陡岭路改造加宽之后,人行道变得更窄,还要配上装模作样的花坛,坛里栽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臭皮柑树。这些臭皮柑树移植过来时就严重老化了,很多枝条的顶部已经枯干,它们本应在乡下光荣退休,不期然来到城市充当绿化的新兵,苍老让它们身上绿意斑驳、支离,仿佛一桶桶因长久不用而干裂的绿色油漆。两个人在同一条道上,面对面疾步相向,老头在即将碰着我时,倏忽侧身,我被他的气势逼得一让,差点撞在臭皮柑树上。老头脸上露出歉意的微笑,但我分明看到这笑容背后藏着的调皮与调侃,好像这正是他要看到的效果。这一笑甚至让我觉得,他早已知道我的底细,对我路过这里的时间、步幅、速度,对我心里的种种想法,悉数了如指掌,因而在与我的对抗中,他怀着必然的胜算。
第三天早晨,我一上陡岭,视野里便出现他从胶鞋厂那边像一枚导弹发射过来的幻觉。我脑海中的防守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几次试图进行拦截均被它强力穿越。不出所料,我在快到金鼎消防器材厂门口时,无可回避地再次看见那个比灯泡还亮的光头。他大概也看到了我,不像平时那样低着头,而是平视前方,笔直与我的视线实现了精准对接。更令人气愤的是,他脸上早早准备好了那调皮与调侃的笑,仿佛那是一团稀泥,他在和我擦身交臂的刹那,又稳又准地将它泼到了我身上。我愣在那里,目光像只蝎子样狠狠蜇他一眼;但没蜇上,他一晃,隐入我后面的人群中。仓促间,我目光的毒针误伤一位美女的右颊,她的手不停地摸着那个部位,哭丧的脸像被筷子夹住的花卷。我赶紧逃之夭夭。
我发誓要和老头针锋相对,决不退让。第四天,我一出小区就把脸绷得紧紧的,发动脸上的每个细胞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所以整张脸恰如一个批斗现场。我高举这个现场向前挺进,快到金鼎消防器材厂门口时,一眼看见那个让人憎厌的光头。待他走近,我将“批斗现场”像个金钢罩一样向他掷去。不料,他手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拿着两个包子,走到我面前时,他歪起头咬了一大口包子,嘴角溢出酱色的油汁,一直流到手背上。他只顾忙乱地舔手背上的油汁去了,压根儿没瞧我。我满脸阶级斗争,两眼圆瞪,凶巴巴地俯瞰着一个刚买了早点、匆匆往回赶的大妈,她受到不小的惊吓,呆在那里,浑身发抖,像面对一个蒙面持刀抢劫犯。我又逃之夭夭。
我在这场游戏中没有讨到半点便宜。我不玩了。我讨厌那个身轻如燕的光头,私下里我曾骂过他“老不死的”。虽然我骂过之后十分自责,毕竟他是一个与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老人。然而,我们在情感领域和思维领域已经有着脱不开的干系。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喜欢的人之一,我却不得不每天要那样面对他一下,这对我的尊严是一种考验。于是,我想着逃避。上陡岭路是我去单位的必经之道。空间上无法逃避,唯一的办法是改变出发时间——上班迟到要扣奖金,唯一中的唯一是提前出发。比如提前十几分钟起床,为了彻底避免在陡岭路的任何地段与他碰面,最迟七点要走过长沙铝制品总厂。
早晨的睡眠比金子还贵。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生物钟,六点四十分左右起床好比受刑。而且,上班迟到领导觉得你懒散,不上劲,会对你有看法;总是早到同事觉得你发神经,或者有评优升职之类的不良企图,大家都看不起你。人还是正常点好,不就一个素昧平生的老头子吗!人家没招惹你,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样跟自己做思想工作,通了,继续按老时间作息。前面几天我有意走陡岭路西边,一直到派出所门口再过斑马线折到东边来。每次走到与金鼎消防器材厂隔路相望的佳佳超市和养天和大药店附近,我转头仔细寻找那边人流中那个铮亮的光头,都没有找到。绕了路,心里还很不舒服,好像在跟一个莫须有的东西作斗争,真不值得。我命令自己走回东边去,恢复日常状态,祛除心魔,莫把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头当作怪力乱神。
那天早晨,下着雨。我是个宁愿淋湿也不打伞的人。长沙的秋天难得下雨,雨一下就挺认真的,可以兢兢业业下个半天一天。雨下得这么早,老头该不会出门了吧?我快走向前走着,的确没看见那个熟悉的光头,心里窃喜。你厉害,总拗不过我年轻!即便你敢出门,那个光头肯定也藏在某把雨伞下面,没法威风了。但当我走到金鼎消防器材厂门口时,发现老头站在传达室外面兴致勃勃观看一张刚贴上去不久的通告,他依然穿着那件焦黄色夹克和卡其布蓝色裤子,脚上一双解放鞋,只是光头不见了,赫然戴了顶蓝色旅游帽,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我感觉自己又被打败了。为了消除这种不好的感觉,我大步走过去,站在他后面,仔细看起那张通告来,并且口里念念有词:
通告
近来厂区多次发生偷盗现象。为确保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经厂办公会议决定:下班后六点整生产厂区一律关电拉闸,生产厂区传达室小门落锁,禁止任何人进入厂区洗澡。如车间有加班任务的,必须提前报主管经理,经批准后,保安部方能放行。早上七点三十分开门。
特此通知。
金鼎消防器材厂保安部
2008年月10月25日
老头回头看了看我,很快返过去,继续看那张通告,仿佛要从这张通告里将小偷抓获归案似的。通告旁边有一张遗失启事,我接着读:“本人于昨天下午在三车间遗失充电器和电源插座各一个,请拾到者通知本人,电话:130xxxx3535。刘先生。”老头再次回头,但没有看我,他转身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调皮地笑了。终于打了一个胜仗。雨的空子都显得大些,我钻来钻去,到了公交站进了公交车,身上全是干的,雨打在别人的伞上、淋在别人的身上,噼里叭啦,像开花一样,声音好听极了。
以后,我照例在金鼎消防器材厂门口附近碰见老头。他头上一直戴着那顶帽子,身上还是那件夹克和那条裤子,只是随着气温降低,看得出里面渐渐增加了衣物,但这些丝毫不影响他的轻快与敏捷。我基本可以断定,他是在进行晨练。如此准时,可能是他做工人时留下的不可改变的习惯。让人费解的是,别人晨练,包括在这条路上经常能看到的这类老中青,一般穿着运动服,甚至短衣短裤,架势很足;而他晨练和平时穿着同样的衣服,把运动当作一次普通的外出。他消解了晨练的外在形式,因此才有边快步走边吃包子的怪行,才有聚精会神看通告的闲情,才有对着陌生人调皮微笑的胆气。他没有架势,却是最能坚持的;他没有形式,却是最为生猛的。我在猜想,是什么使他如此特立独行,贫困、孤独,还是清高?
我没有答案。我迫使自己理解他,弄不好还有点佩服他,然而,我实在是无法喜欢他。他对我的挑衅施与我额外的压力,我不得不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和迎面而来的他进行一场电光石火而又惊心动魄的战斗。其实我知道,这场战斗弄不好只关乎我一个人,只是我一个人的战斗,但他已被无情地卷了进来。我们之间,没有谁是无辜者,我们都在承担我们该承担的。好在自从那次我站在他身后念通告和遗失启事之后,他变得审慎多了,不轻易做出那样调皮加调侃的笑容。我也装作和悦些,不轻易板起自己的面孔。我从他不自然的表情里,看得出他感受到了我的不快,他似乎也不愿意碰到我,目光再不愿意与我对接,只要我望向他,他便主动收回,向内视去,看着自己的消化道和胸膜一带。于是,我豁然省悟,或许在他心里,我同样一直是他很不喜欢的人。人生真奇怪,从不认识的两个人,相差那么大,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却能在对方心里引起如此复杂的情绪。他们永远不会相识,却总是以同一种方式相遇。
我们这对陌生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熟人”。后来,我经常出差,那些天他肯定看不到我,直到我从外地回来,我仍然能在快到金鼎消防器材厂门口时碰见他。即便不出差,我们并非天天能碰面,有时一连两三天没看到,不过他过不了几天总会出现。我们渐渐平静地接受了对方的不喜欢,接受了这种几乎是命运强迫的相见。
春天来了。往年这个时候春雨绵绵,无休无止,今年却出奇地雨少,每天天上挂个太阳,整个天空像一张盖了公章的发票。风稍大,刮走天边的一块云,好像拿了发票的手刮掉上面的涂层,露出“纳税光荣”的字样来。
有段时间,老头的精神状态似乎特别好,天天看见他健步如飞,神气活现的。所以,那天没在金鼎消防器材厂门口碰见他,我蓦然觉得豁了一个口子,仿佛一堵墙倒了,呼呼北风吹得人心里发凉。我放慢脚步,过了福泰家菜馆,过了长沙胶鞋厂,过了奇志装订厂,过了陡岭建材商店,过了浏阳蒸菜馆,过了白香炒货店,过了长沙铝制品总厂,过了创新废品店,过了开福区农村信用合作银行,到公交车站了,那个口子仍然醒目地豁着。
第二天,还是没有碰见他。下班回来路过长沙胶鞋厂时,隐隐瞧见厂区前坪架起一个长长的牛毛毡棚,看上去像是一列废弃的火车车厢,里面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和飞扬的哀乐。
第三天下班回来,那个牛毛毡棚里更加热闹,锣鼓和哀乐愈益迫促、粗犷,鞭炮炸得震天价响,还有繁密的人声,没听到哭,大多是说话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
第四天早晨,快到金鼎消防器材厂门口时,我已不抱希望能碰见老头,可连行人都没几个,让人颇为纳闷。我孤零零地走着,加快了步伐,刚到福泰家菜馆,看见长沙胶鞋厂门口围了很多人,手臂上戴着黑纱,门口停着几台车。大清早的……我想避开他们,路上车少,我下了人行道,大摇大摆在陡岭路的马路上走着。走过胶鞋厂门口,一个比灯泡还亮的光头和那无比熟悉的、调皮而又调侃的微笑,震烁了我。我僵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一个双手捧着相框的青年,他神情悲戚,站在殡仪车旁边。
相框上挂着一条黑绸带。但里面的光头是那样明亮,笑容是那样调皮,神气活现的。他手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拿着两个包子,歪起头咬了一大口,嘴角溢出酱色的油汁,一直流到手背上,他只顾忙乱地舔手背上的油汁去了。我对着他鞠了一躬。这时上来一位戴黑纱的中年人,递给我一支烟。我接了,问:“老人怎么过世的?”
他说:“前天晚上打了麻将,看了电视,快零点的时候,突发脑溢血,没出屋就落气了。”
“去得快是福气。高寿?”
“刚吃73岁的饭。身体好咧,上下楼比我们年轻人还快,都以为他会活到一百岁。你认得我叔叔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呵呵,在这条街上,每天打照面。没想到今天碰上出殡,所以鞠躬送行。”
“谢谢你,再抽支烟。”中年人又递过来一支烟,他嘴里嚼着槟榔,舌头有点大。
“我不抽烟的。今天破例,一支够了。”
我最后看老头一眼,离开了那个人群。太阳高悬在天上,整个天空像一张盖了公章的发票。我们向天堂交付了一个老人的一生,要它开张发票是应该的。一阵风吹来,刮走天边的一块云,好像拿了发票的手刮掉上面的涂层,上面写着“纳税光荣”。我迈开大步,昂首挺胸,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命的尊严与光荣感向单位走去,向我的工作走去,向明天走去,向我的天堂走去。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