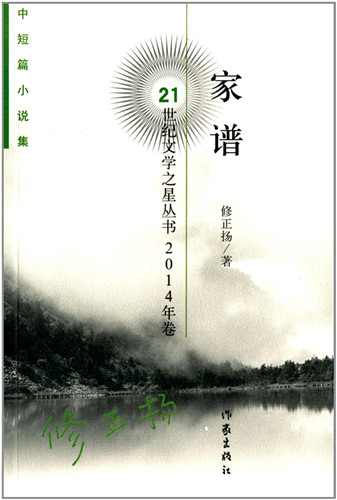
恐怖事件
作者丨修正扬
北京时间九点整,马军匆匆赶到教师新村七号楼。时间记得这么准是因为钟楼刚刚报点。他踏着钟点爬上最后的一层楼梯,同时对了对腕上的表。他的汗已经出来了,透过楼道通光的方格能看到太阳在山那边。
门虚掩着。马军轻轻地挤进去。他靠着门,一动没动,怔住了,有些不知所措,咬着嘴唇,手插进裤兜里,静静地看着。李连生正背对着他随着电视里的舞蹈教练摇晃“小荡漾”,荡得真好,电视上几个性感的女人就不说了,连生可是八十公斤重、皮黑肉粗的一条汉子,现在穿着小裤衩,光着膀子,像那么回事地对着女人,还是几个女人晃腰,应该是腰,尽管事实上主要是颠簸的大肚子。
马军挪到沙发上坐下来。很小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做的事一定是很重要的,不该打扰。比如马军这么早跑过来有不能耽误的事情,许许多多的人不得不早早起来是要谋生。马军拍了两下手掌。客厅里的舞者转过身吃惊地看着他,问什么时候来的?
才来。
李连生走到门边上认真地瞅了瞅,踢了一脚,说,奇怪,我忘了关了?
马军说你继续,先忙你自己的事。李连生拒绝继续。他挠挠头皮说,我想试试减肥。他把频道换到中央一台。屏幕上变成巴勒斯坦的断壁残垣,阿富汗蒙着面纱的女人和美国第一号人物到第N号人物的讲话,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每天都是这些。
不看这个吧,马军说,看小荡漾。
他一声不哼地盯着电视上的恐怖分子的头目,一个缠着头巾的老人,好像颇感兴趣,又好像在生闷气。这个老头长了一把大胡子,犁一般的鼻子,耕过后的土地样的脸,怎么能和几个健美、暴露得恰到好处的女人相比?难为他还要装出一副爱好广泛的认真样子。
一个有尊严的人,新闻过后李连生点起烟,吐出第一口后如此说道。
你说哪个?马军说。他在点李连生甩过来的烟卷。
干得多么漂亮啊,李连生深深地吸了口烟说,我佩服这样的人。
恐怖分子。马军说。
这只是一方的看法。
也许是吧,马军从腰上把枪掏出来,我把它带来了。
连生看了一眼,走过去拿在手上。
这世界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他继续说。
错的就是错的。马军说。
屁话。李连生使劲地弹下烟灰,用力之大,把火都弹熄了,心底的火却难以熄灭,脸颊上的两道刀疤开始泛红。有的人的关节能预报天气,有的人的疤痕能预报心里的天气,一个道理。这个功能是李连生自己说出来的,当然不是炫耀什么。小小的自嘲。
把枪拿好了,我和你说个事。
别和我说不好的事,正烦着。连生说。
马军不明白他为什么激动。一个提着枪的人是不能这样激动的。马军也不明白连生为什么提着他的枪像提着自己的枪,过去他曾经央求马军把枪带出来玩玩,至少让他过把瘾。昨天办案回来,马军没把枪缴回队里,心里其实就想着他的。马军攒着子弹呢。可是他握着马军的手枪几乎就像握着自己的手枪,看都没多看一眼。
马军按着脑袋想了想才说,那把枪还给我。
连生掂了掂,把枪放在茶几上。
收拾一下,马军说,我们出去吃早饭。
马军把枪插进枪套里,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
李连生的两道刀疤是停薪留职去深圳做“的哥”时落下的,一次是遇见劫匪,一次是见义勇为,两次遇见的暴徒都选定那个部位下刀,在医院打针你如果请求他们,都知道左右屁股换着来,医院的态度大家都知道,这些狗杂种比医院还歹毒。谋生真不容易,一个人在外面谋生更不容易。所以开了两年车他终于回来了。他们是同学,从小学同到高中,到小学五年级时基本就确定了关系,不说他们的关系好到什么地步,一句话,没得说。那种终生的兄弟般的情谊。马军他爸还在的时候曾经怀疑他们是同性恋,他要是活着马军得骂他懂个屁。敢说这话时他爸已经死了。这就像歌里唱的,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却没了时间。李连生回来后第二天给马军打电话,约他到老顺兴楼吃饭。不过到了酒家的包厢里看见他的脸马军就呆了。他得好半天才能确信这就是连生。他说,连生。连声说是我。他又说,连生。连生嘿嘿地笑着。他说你这是怎么了啊?连生笑着说我是怕没脸见你了。那天他们喝了一箱啤酒,大部分是连生喝的,马军喝得也不少。李连生简单地述说了这两年的生活,大多时候在喝酒,拿牙齿掀开瓶盖斟上酒,泡沫浮上来,咕噜咕噜喝下去,接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上一会儿,然后又拿牙齿掀瓶盖,如此反复。就像有人说话老是“是吧是吧”的,他那天老是“真他妈的日子”,比丢在地下的瓶盖还多。他是怀着美国梦般的愿望去深圳的,结果还是回到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和美国没有关系,和深圳也没有关系,和这些美好的梦幻般的所在没有关系。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他把完好的,现在想起来简直是美好得让人心痛的脸留在那里了,为建设国际花园城市贡献出了微薄的砖瓦。仅此而已。那天马军喝醉了,呕吐了一场,平时他是没有这么容易醉的,那不过是啤酒,一泡尿就能摆平的。但是他真的醉了,趴在洗手池上的时候不小心把镜子还打碎了,手掌出了不少的血。
他是五月四日回来的,昨天是青年节。今天是五月五日。
这房子两室一厅一厨一卫,除了没有装修,看起来简单一点,对单身汉来说还是蛮好,对单身汉的朋友来说也蛮好,是个聚会的好地方,紧急时候还可以借用一夜。当然,对结婚来说这房子小了一点,老前天吃饭的时候连生对马军说他准备买套宽敞些的房子。
连生的女朋友叫金蓉,比他小五岁,他们都曾是粮食局的职工。金蓉学校毕业刚进单位,连生就追求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然,也没花铁棒磨成针那么长的时间,半年多吧,终于追上了。那段时间马军去警校进修去了,回来才知道他处了女朋友。马军问他睡了没有啊,问了两次,连生烦了,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谈恋爱也不是就那一件事情。马军说你烦什么烦,我理解你,根子还不是为那件事烦恼,你别冲我发火,你的火要找对对象。后来没几天连生隐晦但显然是骄傲地和马军说他现在是个真正的男人了。马军装着没懂他的意思,说真正的是什么含义?他说干脆地和你说吧,我们睡觉了。马军说你们睡觉了?连生说我们睡觉了。马军说你的意思是她不再是姑娘了?连生想了想才说:她永远是我的姑娘。他说得很矫情,但给马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原预备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真正的男人也不在那件事上面。但是他没说这个,而是真诚地拥抱了他,说,可喜可贺,真正的男人。
金蓉人长得秀秀气气的,脸上的轮廓很清晰,谈不上是什么美人胚子,但是女朋友或者说老婆太美了也不见得是很好的事情,一个伤身体,二个很可能还要伤心。过得去就行,过日子呗。她现在开着一家专卖女人衣服的成衣店,粮食局改制后她调了个单位,连生跟堂兄去深圳跑出租,因为据说来钱快。她在新单位也没待太久又出来,店子是去年开的,生意还不错。马军很少去她的店子,主要和女朋友分手很久了,没必要去那里。二是他不喜欢逛街,自然,这和第一条原因也有关系。还有个原因,怎么说呢,其实他和连生说过,他不喜欢金蓉。连生当时说你小子还敢喜欢她?他揍了他一拳头又说,她怎么让你不喜欢了?这能怎么说呢,事实上,马军找的女朋友连生也不以为然。真奇怪,你觉得是鲜花他觉得是狗屎,他认为是美味你认为是毒药。上天好像都安排好了。话说回来,金蓉倒不是他眼里的毒药狗屎,只是不喜欢,他甚至不想多看她一眼。他觉得自己和她不是一路人。她当然和马军不是一路人,否则连生不会答应,他是个死心眼,从一而终,爱一个人会爱一辈子。
李连生穿上丢在床头的衣服,一件印着虎头的T恤和条黄不黄、白不白的休闲裤。他洗脸的时候马军问他最近有什么打算。他一声不吭使劲拧帕子,蒙在脸上,热气蒸腾着。等挂好帕子转过身,马军看到他很萎靡根本不像洗过脸的样子。
没什么事吧。连声反而这样问他了。
没什么事,马军想了想又说,我房里的电路坏了。
走吧,他说,然后拿起刚才弹熄放在桌上的那半截烟卷,我有点饿了。
他们坐车到马军家附近的“天下客”,要了两碗猪脚粉。李连生多要了杯米酒,大概是三两三。他爱那杯酒。在露天临时摆的餐桌上马军看出他是真饿了,大口大口地吃粉条,吃带皮的肥肉,然后细细地嚼骨头,嚼得咯咯响。让马军吃惊的是他一口就把那杯酒干了,说喝得那么急搞什么。连生说你又不陪我喝。马军怕给自己惹事,吸溜着粉条,把骨头从碗里夹出来。
舒服。连生说。顺手从卷筒里掐截卫生纸擦嘴。
马军同意他的意见。在外面办案吃的东西那真不是人吃的,刑警不是人做的差事,当初哭哭啼啼地要求调到刑警大队,那时真是太年轻了。
连生的视线丢在空酒杯里,他吃得太急了,脸上沁出了汗珠。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连生问。
知道什么了?
连生用食指和拇指揩了揩嘴角,露出一个奇怪的笑。
残酷,我现在才看清生活,在深圳受的苦算个毛啊,真残酷。
马军从事的工作让他见的事情多了,不相信人生有什么真正残酷的事情,就像不相信有什么真正的乐趣。他喝口汤。上午十点钟的阳光又稀薄又明亮,隔得远远地洒在水泥坪上,狭长的一道,好像是条温馨的天路。他的汗也出来了。
我是你哥,你不该瞒我的。
马军放下碗筷,用舌尖抵牙缝里的肉屑,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她把开店子的钱都还我了。他说。
谁?
你知道金蓉的事情,你肯定知道,你从来没和我说过。
怎么说?
我们分手了。她另外有了人,有很久了,她直接和我说的。他盯着马军说,好像那个人就是马军。不知怎么搞的,马军突地心慌起来。他摸出烟盒,给他一支,自己点上一支。
她和你说了?
她好像都等不及地和我说了。她的心早都没在我这里了。
等等再看。
不分手我还能怎么办呢?连生有点神经质地说,我跪下来求她,我哭,我想死,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好久都没睡一个安稳觉了。我是不是瘦好多了?
说实话,马军看不出来。如果真瘦了,说明减肥起了效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不该这么难受的。
爱情。半晌过后马军说。
他诅咒了句,狠狠地吸了口烟。
狗屎,他干脆地说,什么真正的爱情,除了脸上这两块刀疤,我什么都不相信。
沉默了会儿,马军说,你也许是对的,这世界变化快。
他们都曾狂热地喜欢崔健的歌,从《假行僧》到《花房姑娘》,还有那首唱个不休的《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去深圳时他还唱过“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那时马军刚弹了个,哦,是接着又谈了个女朋友,想唱“解决”。
马军站起来结了账,说,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连生说还想喝一口。他说别喝了,不然怎么整电。
连生说也是。走了几步他又说马军试图让心里如此灰暗的人给自己带来光明,真好笑。
那就笑一笑。马军说。
马军住的是自家的老院子。现在城里这样的老院子不多了。院子里有两棵上面钉着市文物局编号铭牌的槐树,一个人还抱不过来。他小时候这院子里住了好几户人家,落实政策后陆续搬出去了,当然,为跑这事家里也花了不少的钱。他爸不在了之后,他妈也长住长沙了,给她有出息的闺女带孩子,做饭菜,安享幸福的晚年去了。
房子没人住愈发破败。电线陈旧而且拉得凌乱,有一次短路起了火,幸亏发现得早马军又奋不顾身才没燃起势头,马军想不然烧死了立马见到攒了几代的铜板才修起这大房子的祖宗可怎么交代啊,就算把脸烧坏了,就算那世界永远是漆黑一团,也没脸混下去啊。
他把这里面的严重性和李连生说了。他们很快行动起来。连生要马军找个梯子,可是家大业大的要找这么个小玩意儿还真不容易。马军找来桌子板凳,一个桌子两个板凳,摞起来。连生负责一截一截地检查线路,他负责移桌子扶板凳,提醒连生小心,像掌舵的艄公,把握方向,吆喝号子,看起来也很重要。只是连生后来爬到楼上去检查,完全和他没了干系。他坐在板凳上抽烟。连生不能抽,安全重地,小心烟火。连生每走一步马军觉得这房子都要颤抖一下,灰尘弥漫,细微的颗粒在一缕阳光中缓慢地旋转。马军说你小心点,是你抖还是房子抖啊?共振就危险了。连生说狗日的房子。
他坐在树下抽烟,头靠在树干上。郁闷得很的时候张开手臂抱住树是很有效果的,抱上那么一会儿就会觉得好多了,这是经验之谈,不过现在这样粗的树不好找,这和大腿是两回事。他甚至在大雨里也抱过这树,从科学上来说这是危险的,但是有时候危险是其次的事情,甚至巴不得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巴不得天意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
好一会儿上面没动静,叫唤几声也没有回答。马军不放心,把屁股下的板凳拿起来摞到高凳上,悬乎悬乎地站上去瞅连生。矮楼里黑咕隆咚的,好半天才看见他蹲在楼板上接线,嘴里叼着块胶布。他把胶布缠上去,拿电筒照马军,灰尘又在光柱里飘舞了。
狗日的被电了一下,他说,你走开,让我下去。
马军下来看见房里的灯亮了。说亮了亮了。
帮我扶下板凳啊,他的头探了出来,你去买捆电线,我给你重铺下。
不用了,那大工程了。
我不怕辛苦,你还怕辛苦了?电击疗法还能解忧呢,我找了个好差事。
铺好电线差不多用了两个时辰。这中间马军烧了两壶开水,沏茶,把园子里的花草浇了一遍。预备他下来冲澡,好容易给他找了件格瓦拉头像的T恤,只有这件能和他的虎头T恤媲美。他们坐在大树下抽烟喝茶。他记起了马军的枪,他说把枪拿来瞅瞅。
不太威武。连生掂着他递过去的枪说。
七七,好用。
有子弹吗?
有子弹的,一满仓。
我的子弹都送给豺狼了。
连生说完很短暂地一笑,脸上很快现出上午洗过脸后的萎靡、颓废的色彩。他刚刚冲了澡。他这人是不是一见水就成这样子了?
打几发吗?马军说。
他看了看手上的枪,又想了想才说不打了。他说别再把枪拿出来,挺危险的,我是恐怖分子。他把枪放在马军手上,让他收起来。
我收起来,我以后不再和你提枪了。
记不记得小时候一架飞机从这棵树上飞过,那时我们也坐在这里。他突然问马军。
是啊,战斗机,把树枝都打下来了,我甚至都看见了飞行员。
训练的地方变了?飞机再也没来过了。他说。
没来过。
他抬头看着天,一定是透过树叶间隙的光线和云朵把他痴迷了,他看天的时间太久了。
看什么?马军说。
他还是看天,不睬他。马军也看天,一小块一小块细碎明媚的天空掉在眼睛里,花眼睛,树叶在微风中轻轻地摇动着。他想起那个止鼻血的笑话了,他甚至觉得鼻血流到了嘴里,他咂吧着嘴唇呼了口气。
连生不再看天,要马军进去把音乐关了。他说受不了。
连生自己走进去,音乐马上停止。过了会儿他出来说保险烧了,你这里有没有?
坐下来吧,等会儿我买回来自个儿装。
他想他要坚强,他这身躯应该敞着胸脯背着刀去演另一出戏才对,才像那么回事儿。
高二下学期那年他们和别人打了一架,祸是马军惹的,下夜自习路上被五个人截了。马军被踢翻在地看架势不对想溜,事实上已经溜出去好远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连生却和他们交上了火,马军只好提块砖头又跑回去。他们有五个人,都抄着家伙,所以回去得有些犹豫,只希望连生赶快跑过来,又怕迎面碰见他们。连生没动,一动不动靠着电杆笔直站着,满脸的血,在碘钨灯的光晕下像连环画里战斗到最后一刻怒睁双眼不愿倒下的英勇烈士。在连环画里打扫战场的战友看到这场景都流下了悲伤的眼泪。马军也哭了。连生没死,他说他们都跑了,这下了结了,你若要打我也扛得住,我们一个个来。他说话有气无力,还那么豪迈。他不想打了。他把连生弄到医院包扎,回到寝室连生觉得腹部潮湿,一摸一手血,肠子都要流出来了。他们又赶到医院,那医院小,不敢收。学校派车送到市中心医院。在校车上他脸色惨白,左手捂着肚子,向马军招右手要支烟抽。马军想那时候他都没说要死,在深圳挨那两刀也没和我说过要死,现在他真不该这么说。如果肠子、脸皮、身躯都是坚硬的,千万别要一颗纤弱柔软的心,这样不好。
别想了。马军说。
说不想就不想了?是块肿瘤割下去轻松,还是放个屁舒坦?是心呢,现在这里空一块的。他的手放在胸前就像起誓一样,又说,这空把我都要整个儿吞的。
马军不知说什么好。
小时候多好啊,那时候我们的梦想里没有女人的,也从来不为这个烦恼。
他摇了摇头。
其实我有思想准备,我现在这个样子,不该自私的,我预备和她说分手的,没想到她忍不住先说了。她早有了人,在我出去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有张好脸。
你不应该出去这么久的,你压根儿不应该出去。
我出去又是为了什么呢?我是想我们能活得好一些,我们。
这就是生活。
可能你是对的,你早说过她不好。
我说过?
你说你不喜欢她。
我不知道,我对女人没有鉴赏力。
我日他妈的女人。连生说。
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不就是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踢了,难以承受,自以为是地发现了生活的真相和残酷面目?一个男人在快三十岁才觉得生活残酷是不是应该庆幸呢?话说回来,这算得上真正残酷吗?他说过准备向她提出分手,问题是她抢先一步没给他这个表现男子汉胸怀的机会。她是残忍,但是结果并没什么不同,不就是分手吗?他没理由这么难受的,不应该的,如果他遇见真正残酷的事情会怎么办呢?
阳光明媚。马军戴着墨镜出来显得多么的明智。他也不明白怎么会想到戴墨镜出来的,当时还怕不合时宜的。马军说去哪里吃饭?连生说随便,走走看。他们从龙兴讲寺红漆斑驳的围墙边走出来,拐上建设街,然后横过过街天桥。在古城西路时一个卖花的小姑娘拦住他们说叔叔买朵花吧,叔叔买朵花吧。他们侧身走过去。走了几步李连生却停下来。小姑娘真聪明,一下又拢了过来。他在花篮里翻动几下,拣了一枝玫瑰。这是一枝红得发黑的玫瑰,最外面的花瓣有点憔悴,叶子倒是青翠,刺上还挂着水珠。他付了钱,继续往前走。马军有点后悔没有坐车了。他把墨镜摘下来,一个男人捧着朵花,一个男人戴着大而无当的墨镜,他开始觉得不合时宜了。他想起连生说过他的爱情正是从一朵花开始的。“我用一枝野菊花俘虏了她的心,野菊花野菊花野菊花。”他们一前一后走着,步行街人多了起来,有时候他走在前面,有时候他走在后面,很快马军发现是自己跟在他屁股后面走。他们已经很接近金蓉的服装店了。
我们往哪儿去?
连生停下步子,回头说,我去找她,这玫瑰不是给我自己的。
他说完径直往前走,马军不得不跟着他。他的步伐是轻快的,丝毫没有犹豫,和他的语气一样坚定。马军说算了吧别去。连生要他在外面等。马军还是跟着,连生拐进她的店堂时他才停了下来,附近金茂大厦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分外炫目,他把墨镜戴上又摘下来,点了根烟,他总觉得会出什么事,连烟都抽得急煎煎的。他把烟甩掉走了进去。
她坐在店堂深处的柜台里面,除了她还有两个人,一男一女。连生站在柜台外,背略微弓着,左手按着柜台的玻璃,右手是那枝玫瑰。
他说,不说句话吗?她勾着头,不说话。他重复一遍,声音有些变了。她说,该说的都说了,说完了。
你真的不要这朵花儿?他说,最后一朵花儿。
我不能要。她说。
那一男一女围着一个方凳默无声息地玩牌,看到马军进来后眼睛往这边瞟一眼,很快又转了回去。牌中自有乐趣,牌中甚至能看到命运。他们不关注这边很好。
我们走吧。马军说。
他根本没听进马军的话,低沉而激动地说,那第一枝花儿,最初的花儿呢?
她说不要再说了,我们不是都说了吗。
他把玫瑰移到左手,用右手扯花瓣,从那乌黑憔悴的花瓣开始,一片一片地丢在柜台上,落英缤纷,让人心跳,最后他拈着光秃秃的带刺的梗,凑到鼻子上嗅。他盯着她,他看到的一定不只是她,而是很多很多的回忆,她却不对他看,这激怒了他。他把花梗在柜台边缘的铝合金框上抽了一下,丢在花瓣中。他说,你看着我。她看着她的指甲,剔着指甲里的污垢,其实哪里有污垢,她的手指只是交叉扭动着。他俯下身子,出乎意料地“噗”地吹了一大口气,好大的一口气。花瓣跌跌撞撞身不由己地奔向金蓉,跌落在她的头发上、身上、膝盖上。她站了起来,拿手背擦脸,脸上没有花瓣,如果有那倒是很好的装扮,她擦的是吐沫。那一下连生太用劲,他的脸涨红了。玻璃柜台上只剩下孤零零的一枝花梗,它在狂风暴雨中趔趄了下,移动了个位置,并没有飞出去。鉴于它微型狼牙棒的形态,飞出去有点危险。她终于看着他了。她也看了马军一眼。
你不该拒绝这最后一朵花儿,它是你的,我必将送给你,我曾经那么爱你。他说得不紧不慢,平板单调,仿佛每个字都颇费思量,都被他庞大的身躯碾压着。但是马军看得出他是多么虚弱,他会把玻璃柜台压塌的。他注意到金蓉的眼神,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你无法喜欢抑或不喜欢一种眼神。马军不敢看她的眼睛,他感到难受,说不出的难受。可怜的人,他对自己说,这世界怎么了啊。
我求求你了。她说。
一瓣乌黑的花瓣栖息在她的头发上。马军拉李连生的胳膊说我们走吧,别这样,我们走。
他甩开马军的手,第一次没甩开,不得不用力再甩一次,他太虚弱了。
我说我求你了成不成,我求你了,我们走吧。
等等,他说,等等。
他早都想好了还是一时的灵感呢?他甩开马军的手从兜里掏出把刀子,亮闪闪的刀子,两寸长,原来是挂在他的钥匙串上的。他利索地刺向他一直放在柜台上的左手,刺在手掌和胳膊的连接处。他叫了一声,刀子跌落在柜台上。金蓉捂着脸蹲了下去。两个打牌的人还是一动不动,一个人把打出来的牌拿回去插进牌面中,仔细地看牌,仿佛这里面有好多玄机。
马军拽着连生往外走。连生说我的刀我的刀,我要把刀拿回来。
马军转过身把刀拿在手上。花梗孤零零地搁在玻璃上,玫瑰花瓣剥干净之后真的是根狼牙棒,狼牙棒,一点没错。他迟疑了一下,拈起花梗丢在地下。她捂着脸蹲着,花瓣还在头发上。马军拽着连生,他的手在淌血,眼神迷乱,仿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马军知道得赶快找家医院。他知道这个。
攥着他并不轻松。连生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不把他当回事。他几乎完全倚傍着马军。马军想起高中那次殴斗后送他去医院,流的血不知比这要多多少倍,他也没像现在这个样子,人怎么越活越没志气了呢?精神和肉体之间是种什么关系?它们为什么不互相怜悯呢?快点挣脱出来吧,马军对自己说,就像过去从父亲和老师的桎梏中奔逃出来,漫无目的地游荡也好。如果有了创口,别想它别触碰它,那最后一朵玫瑰应该挡在那儿的。生为男人的痛苦,女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又看到了她的那双眼睛),至少应该装扮得光鲜些过活下去,把玫瑰留给自己,照相也有个道具。
在不太远的一家诊所马军把他交给医生。清洗,包扎,打了针破伤风。马军对医生说他喝了点酒。连生的样子实在像是喝了酒,另外还能给人怎么解释呢。马军把他扶到病床上放平,要求给吊两瓶点滴,没有别的办法。一开始连生还自言自语地咕哝,好一会儿后渐渐安静了。他的脸有些发潮,马军替他擦拭他也没动静。他睡着了,开始打鼾。马军感觉到自己的脸也潮了。
马军坐在床沿上抽了根烟,肚子饿了,他和医生交代一下,跑到附近的超市买了两块萨其马和一盒牛奶,在诊所门口稍稍垫了垫肚子。这个诊所在菜市场边,菜叶子的气味,油炸食品的气味,卤肉的气味,人的辛劳味混杂在一起,往来穿梭着,地上流淌着污秽的黑水。他坐在门口一辆单车的后架上,机械地狠狠地像肉食动物那样咀嚼着。他的眼睛模糊了,他勾下头,慢慢地啜吸着牛奶。
他又回到床沿上,他觉得疲倦,靠在旁边的病床上假寐了一会儿。腰上的枪把他抵了一下,他爬起来看了看药水瓶。连生的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他问他好些了吗?他嗯了一声。
一会儿就好了,马军说,打完了我们去吃饭。
叫人来抽针,我已经好了。
别急,打完起来,慢慢来。
我还是想她。连生隔了会儿说。
马军把枪套往后移了移。
我不恨她,不恨,恨不起来。
这样好。用不着恨,想都不要想。
我真不恨她,我一直是爱着她的。
爱不是个好东西,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爱的是什么,马军说,一刹那的疯狂。
我是不是看起来都不大正常的?
会过去的,会好的。
应该会好的,我是男人,连生说,真正的男人。
马军转过身去,给自己点了支烟卷。
给我也来一支。
马军把嘴里的烟放到连生的唇间,自己又点了支。
叫人来抽针吧,这水吃不饱的,没味。
医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马军说滴完起来吧。连生说够了够了。马军自己找根棉签自己动手给他抽了。时辰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
他们在菜市场出口边的小饭馆吃的牛肉火锅。马军不让他喝酒,后来让他少喝酒。都没有用。他一定还要给马军倒一杯。三两三的杯子。马军以为喝不完的,喝得慢,不过最后还是喝干了。马军说他不喝了,吃饭。他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一晃一晃的,身体当中像有个大洞,四肢和阳物都全无依凭。吃了碗米饭下去他觉得好过些了,可能沸腾的牛肚也起了作用。马军给连生盛饭,夹菜。吃饱饭会好得多。连生也吃了两碗,他有点醉了,不过话语不多。这一天马军总觉得连生在种醉酒的状态之中,现在反倒是醉得轻一些。他们带着三碗米饭,一斤用粮食酿造的酒,两个皮囊回到连生的住处。马军执意要送他回来。
你休息一会儿,我回去了。
不再聊一会儿吗?
你先休息好,我明天再来。
来早点,我们一起扭“小荡漾”。
小荡漾。马军揉了揉鼻子说。
连生斜靠在沙发上,醉意浮在他的脸上。
对不起,我没把你的灯弄亮,我预感我干不好这事,起初我就说了,最后还是要你动手。
没事,不就搭根丝嘛。
回到家的时候马军才想起没买保险丝,他几乎一直就没记着这事,想着为这事还得出去一趟他骂自己。他说你这个杂种。这时候连生打来电话问他保险丝装好了吗。马军和他说了,说你还没睡啊。
睡了,又醒了,他的声音迷迷糊糊,像双疲惫的眼睛一眨一眨,我做梦梦见你没接好把房子烧了,好大的火。
莫骇我。
我在扑火,可是火却把我烧死了,好大的火,在火里真他妈的温暖啊。
睡安稳起来,好好睡一觉就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马军没出去,他哪里都不想去。他脱光衣服,冲了个澡,冲了好久,用力地搓洗。然后赤裸着身体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开始只是睁着,什么也没看见,后来看见窗外的树叶和投在墙上斑驳的影子,天花板糊着的老报纸上的新闻和图片,一层又一层(它们是他爸妈糊上去的,他打的面糊),看着自己眼里的阴翳,后来他又什么也看不见了。一阵铃声把他扯了出来。他坐起来,拿过电话,看了看号码,把它放在耳朵边。
他木然地听着,找到根香烟点着。
我没有说,没法说。马军隔了会儿说。
你说了你会说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我会死,我恨不得一枪打死我。
我和他说。
不,不,我下次和他说。
我会和他说的,我受够了,我们怎么不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等我想想,给我点时间。
有的事情一开始就应该想好的,你为我想想好不好。
她哭了,他安慰她,他觉得自己也想哭,又觉得自己并没有资格哭。他拿着酸胀的喉咙说,我再想想,我说了明天早上,等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他关了手机,爬上床。他又起床到厨房取了两罐啤酒,坐在桌边慢慢啜饮,过后又取了一罐很快地喝干。他爬上床。
醒来的时候天已全黑了。他摸到床头的手机开机看时间,差不多八点。手机响了两下,是队里的短信叫他归队。大概紧急,手机还在响,一样的内容。发短信的时间是下午四点五十分。他回电话过去,然后放下手机嘟嘟囔囔诅咒,摸黑套上裤头内衣,穿好警服,背上枪,草草地洗了把脸。他说,哪里都短路的。
出租车快到金茂大厦的时候他觉得事情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马路上到处都是拥挤的人,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警察。消防车,救护车,警车的警灯无声地闪烁着。金茂大厦是这个城市地标性建筑,打个比方吧,比如世贸中心大楼在纽约。当然,现在世贸中心大楼没有了,不该打这样的比方。金茂大厦高二十八层,通天塔一样高耸云端,的确是这块天的支柱。
戒严解除了,开出租的师傅说,交通台刚刚说戒严已经解除。
怎么了?
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师傅笑了,爆炸案。
爆炸?
听说死了十几个,具体还不大清楚,我可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马军心里咯噔一下,想不可能,没有和我说死人,不可能死这么多人,不可能。他笔直地靠在椅背上,双眼盯着前方。大楼从外面看来不像爆炸过的样子,没有变成废墟,也没有残垣断壁。一切看起来还是好的。
司机师傅使劲地按着喇叭,虽说戒严已经解除,警察维持着秩序,更多的警察武警和警车正在准备撤退,但是被疏散出来的人和赶来看热闹的人实在太多,肩上扛着摄像机穿梭工作着的记者也有好些,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在采访机和镜头前既紧张又兴奋地说着什么。车子缓缓地前行,车灯柱里晃过许多黑色的脸。马军把脸贴在车窗上,车子渐渐地快了起来。
马军赶到重案组,跑着上的楼梯,江文一个人在大办公室里。
约会去了是吧?
我睡着了。
一个意思,我们说的一个意思嘛,江文呵呵地笑了,你别这么露骨好不好。
出的什么案子?
你看见楼下聚的记者就应该知道是大案子,看明天报纸头条吧。
马军坐下来,给自己倒了杯水,他高兴看到同事轻松的表情。
我第一个抓住案犯。嘿嘿,你说金茂大楼用一百公斤TNT炸药热身会是什么效果?
不知道,我只在电视上看过飞机撞大楼。马军顿了顿又说,没人伤亡吧。
没有,我及时赶到,化解了一场绝对危机。
江文个子瘦小,说话时眼皮眨得很快,好像是嘴皮牵动着它们一动一动的。
你狠,马队人呢?
在审讯室,哦,江文把嘴嘟起来,来了。
马军转过身站起来,马队叼着烟,站在门口,招手让马军过去一下。
知道案子了吧,马队在沙发上坐下来说,把门带一下。
爆炸案?马军掩上门,在对面坐下来。
犯罪嫌疑人打电话说在金茂放置了一百公斤炸药,随时可能引爆。金茂是不能出事的。大楼人员进行疏散,专家在全面排查。
没事吧?
李连生你认识吗?
马军怔了一下,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李连生,脸上有块刀疤,挺大的块头。马队说。
他是我同学。
我们在他的手机通话记录上查到你的电话号码,他现在在隔壁,刚刚被批捕。抓他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可能是喝了酒,他甚至记不得他打过这样的电话。
马军嗖地站了起来。他的嘴唇蠕动着,但是好半天都没说出话。
他说的放置了炸弹?不可能的,不,他一整天都和我在一起。
他一天总共打了三个电话,在打这个电话之前给你和一个姑娘打过。
天。马军喊了起来。
马队看了他一眼,一截烟灰掉在地上。
就因为一个电话把他逮捕了?这该是治安案件。你刚才是说逮捕吗?
这是恐怖事件。
但这不是事实。
你没看到造成多么严重多么恶劣的影响?金茂明天还不会恢复正常,交通戒严,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干扰,谁来负责?这个玩笑开大了,实在太大了。
他喝醉了,下午我们在一起喝酒的。
他会真的放置爆炸物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马军机械地摇头,然后猛烈地摇头,他说不不,他一整天都和我在一起,他一定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他不知道,他做不出真正恐怖的事情。
马队咂吧着嘴唇,搓着手站起来。
你坐一会儿,年轻人啊。他说。他叹了口气。
你要帮他,马军抓过马队的左手,你一定要帮帮他,他是我兄弟。
天,我现在是这个,马队用拇指掐在小手指尖上,这是多大的事你还不明白啊。
不要关机,说了不能关机的,他拍拍马军的肩膀,坐下来冷静一会儿。马队想到了什么又说,你兄弟口紧得很,他一直说不认识你。
他坐下来,坐了好久。周遭安静极了,越是安静耳膜受的压力越大,仿佛在大洋深处一样。那些看不见的始终存在的黑暗的水包裹着重压着他,水流把他荡涤得空空荡荡,就像一块千疮百孔的石头。还是这些水流把他绑缚在石头上,动弹不得,缓缓地但是不可避免地下坠,直至布满稀泥的漆黑的海沟。他捂着脸伏在膝头上,痛苦地呻吟着。
听到外面的骚动声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外面已经围了好些记者,摄像机和照相机正对着第一审讯室的门口。李连生刚刚被带出来。他拿双手遮在眼前挡闪光灯,他的手被铐住了,所以看起来仿佛在痛苦地祈求着什么,或者是种投降的姿势。
马军说,连生。
他说的声音太小,说在自己心里,周遭太嘈杂,连生听不见,除了他自己谁也听不见。他们走了过去,警察把连生押上车,车顶警灯闪烁。他用力跨过几大步,拨开身边的记者大声说,连生。他抓住他的手,他们看着对方。他牵着他的手分开众人奔逃,像过去一样奔逃,不停奔逃,耳边是呼呼的风声,是倒退的风景,是河水般流淌的清澈明亮又稀薄的时光。马军说,连生。连生抿着嘴唇,脸上的刀疤红艳艳的。我被抓了,警察同志,他生涩地说,我跑不了的。
马军说不出话,他几乎要哭了。
你爱她吗?
他的喉咙堵塞了,说不出话。他说不出第一次见到她的感觉,说不出他甚至不敢多看她一眼,说不出他一直是爱她的他亦一直痛恨着这爱,也说不出他一直是想逃避的、跑开的,但终究还是跑不开。
对她好点,他说,灯整亮了吗?
马军摇摇头,我应该自己和你说的,我该和你在一起的。
连生咧开嘴,车门砰地拉上,马军被簇拥的记者挤开了。警车走后几个记者围住他。他没听清他们说些什么,他粗暴地推开他们,他的脸色太阴沉,以至于一个几乎跌倒的记者一个字也没哼,扶着眼镜看着他走回去。
马军回到家时夜已经很深了。队里弄了点宵夜,江文给他端了碗面条来,面条很烫,他吃了一口放下筷子等它冷一下,他发现自己吃不下东西。江文说开车送他,他拒绝了。街上亮着灯,行人不多,绿化树黑漆漆地排列着,浓云聚拢,把月亮遮住了,天上奇怪地飘起了毛毛细雨。金茂大楼和往常一样耸立在那里,灯火通明,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他发足奔跑起来,跑过一条街又一条街,他一直跑,在新建街的拐角处有几束电筒灯光照来,喝令他停下来。他们紧张地围过来,穿着联防和老的警察制服,光束晃动着,他们把他当成可疑的夜行客。恐怖事件让人提高警惕,加强戒备。他慢下步子,调整呼吸,喘息着。他们看到是个警察觉得有些尴尬。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不好意思地说警察同志,追赶什么?要我们帮忙吗?马军摇摇头。他说下雨了。他继续跑。
金蓉在门口等他。他喘着粗气站定在她的身边。她站在屋檐下哭,她的身体抽动着。他像一棵树立在旁边,等到呼吸平定下来的时候他把她拉过来。
我没想到会这样的,她说。
你和他说了。
我受不了这个,我不能这样下去。
这不关你的事,他说,我会处理的。
我不知道会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她的手紧紧地抠着他的背,我害怕。
他们的身体轻轻地颤抖着,他的手拢在她的脖子上。
我送你回去。他说。
我不回去,她说,我回到哪里去呢?
今天不成,我单独待一会儿,他说,我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我们等待的就是这个吗?我们等来了吗?
别再说了。
我害怕。我真的好怕。
他们蹲下来,她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哭声越来越大,哭得委实伤心。他抱住她的头,试图安慰她,但是说不出话。他跪下来紧紧地搂住她,他说明天,明天总会好的。
后来他把她送上了车,孤独地走回来,孤独地站在院子里,站在和风细雨之中,站了良久。他掏出手枪,很快地把一弹夹子弹打在老槐树的树干上。
他直接上了床,在黑暗中脱掉衣服,蜷缩在被窝里,然后把身体伸直,试试这样是否会好受点。他从搭在床头的衣服里摸索出烟卷,抽几口又吐掉。他觉得身体又疲又乏,时冷时热。好多年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马军和连生犯了事一起出走,迷了路,他们好像是准备去哪儿的,在三一九国道上一直朝前走,走了二十五公里,穿过好些小镇和村庄。夜里他们在路边的山洞里烧火取暖,柴火和茅草烧完后洞里一片漆黑,他们依偎着。我冷,马军说。连生说没柴火了。马军说你不饿吗?连生说出去看看,你在这里等我。他把外套丢给马军。他去了好久,马军以为他找不回来了,一个人待在夜晚的山洞里真是恐怖。他真想沉沉睡去,可是办不到,怎么也办不到,迷迷糊糊中连生摸进来了,提着一袋子发面饼和一罐头瓶的水。马军说,是你吗?连生?那还有谁,还会有谁呢,连生说。因为有吃有喝的了,他的调子很高兴很自豪。马军哆哆嗦嗦地站起来,挺没用地哭了,挺没用地说吓死了,我怕。连生呵呵地笑着说没那么恐怖,想想我吧。在黑暗中马军循着声音去抓他,他在床沿上打了个旋,抓不到。他抓到灯绳,把它拉断了。房子里静悄悄的,他摸摸自己的脸,把它压在床单上。
第二天早上马军吃猪脚粉的时候要了份早报。他坐在前一天早上来过的粉馆摊开报纸。李连生的大幅照片登在头版,摄像师大概特意彰显恐怖分子的恐怖,两处刀疤格外明显。他潦草地扫过连篇累牍的报道,记者都是些胡编乱造的家伙。他把报纸揉成一团,攥在手里,大口大口地吃着粉条。连生的刀疤在他的指缝里挣扎着。他攥得太紧了。他弓下身子剧烈地呕吐起来。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