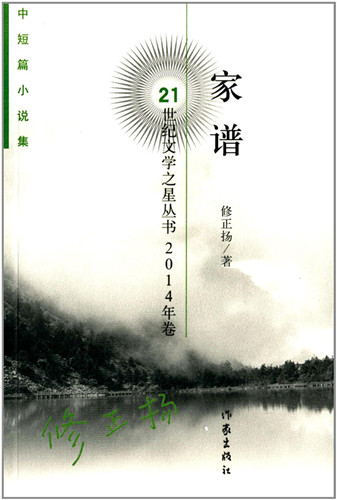
家 谱
作者丨修正扬
我们认识的第一天他就说很想回来看看,这之前他说欢迎我去他那里做客,说了两次,然后说到想回来看看,这是他小小的愿望。这些话都是在Q上说的,我盯着他的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是位中年男子,网名“修正涛”,很可能也是真名,除此以外我一无所知。这样是不是太鲁莽了?他的愿望让我有点紧张,好像我回一句“欢迎你来做客”他就会像仙女一样突然出现在面前(他当然不是仙女),我甚至有点恼火,因为沉默着老是斟酌显然不太礼貌,尤其在我出于礼貌对他的邀请简洁而轻率地回答了一个“好”之后。每当我走出一着臭棋,就知道免不了被人棒喝将军。我举棋不定,实在不知怎么应好。他的头像在框子里摇头晃脑的再次读秒般嘀嘀响起时,我简直没心情点击打开。他一直在叫唤,我还是打开了。他说现在工作忙,等有时间了再说吧。他还说谢谢,真的谢谢你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资料。我说没事,您太客气了,一家人这样说就生分了。话一出口我就觉得真是个臭棋篓子,我借故有点
事,不等回答麻利地隐了身。
话说回来,起初是我先找上他的,那天鬼使神差进入了一个叫“修氏渊源”的网站,我不知道全国各地有这么多姓修的,一直以为就我们辰州这地方有,外地有的话也都是从这儿流散出去的。一下见到这么多同姓还真不适应。父亲先前说过天下姓修的都是亲戚。以我的经验看也是这样的,现在看来我是成语里面那只看天的青蛙了,而父亲显然也搞错了。另外,网站上的修氏名人堂里竟然没有我的先人,所以我叹了口气,每个人都难免做一只青蛙啊。我这种情绪多少是有点依据的,我的家族曾是四大家族之首,我是说,大约六十年前,在辰州这地方——不要先入为主自作聪明地以为什么,不过有人喝烧刀子不就菜我也不会骂“娘希皮”,人的知识面总是有限的——我的堂祖父做过蔡锷的秘书长,讨过袁护过法,晚年影息家园,主修辰州志。本家的大姐是台湾中山楼的设计师,该楼图案印于现行邮票及台币上。我认为他们应该比名人堂上的两个演员要名人得多。老实说名声本来就是件奇怪的事,我能接受这些,只是这样一来面对网站上的言论难免有听取蛙声一片的感觉。这个时候我看见了他的名字,这个名字和我一个班辈,可能还是我不太熟悉的本家兄弟,名字后面是他的Q号,我略一犹豫把他加为好友,他好像在那边等我,所以很快身体都摇晃着小鸟问答起来。他是附近一个自治州的,隔我这二百多里地,和我的家族并没关系。他听我说是辰州的之后很兴奋,他说他那一支正是从辰州迁过去的,家里的长老都这么讲。这样说来我们还是有点关系。他打字很快,面对面说话一定会喷我一脸吐沫,不过他的兴奋还是感染了我,我很久没让人这么兴奋过了。我手上刚好有本堂祖父的诗集《柘园诗草》,我记得集后附有辰州修氏昭穆表和支系表,我让他等等,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在一个堆着废物的纸箱里找到了那本书。那个下午我做的工作就是一个个字地把这些原始资料打出来给他看,我是用拼音打字,字打得慢,很多字对我来说还很生僻,不得不查字典(我唯一的工具书是本重约十斤的合订本辞海)找出正确的读音,几次都想不打下去了,总之坚持下来我费了不小的力气。他家几代人都是按昭穆命名,为了印证他把曾祖父到孩子的名字都打了出来给我看,他说太好了太好了。他还说我简直是部修氏活字典。看得出他是嗷嗷待哺的需要这些粮食,而他的赞美是发自肺腑的掏心窝子话。做完这些工作我有点疲倦,身体很快影响了心理,我厌倦了,我本是搜索一条法律条文来的,却被人从我这里搜索去一套家谱,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太不靠谱。如你所知,最后我心情糟糕地隐了身。
这是四月份的事情,过些天他告诉我他把这些珍贵的资料和网上的朋友分享了,大家很高兴,有几个人甚至给他打了电话。他还给我一个群号,让我有空多去上面转转。我答应了,但是一直没去。他给我留了个手机号码,出于礼貌,我也给他留了,当天他给我发了条短信,我也回了,不外乎是谢谢和没事诸如此类的。当然,我没再说一家人。我还看到我家族我所提到的两位增补入了名人堂。这自然是他的功劳。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很少上网,他在Q上留言问贤弟你在吗?还发短信问好,同时问我最近可好?我一概没有理睬。这不是专门针对他的,那段时间我不想理睬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尤其是我自己。
怎么说呢,辞职过后我一直在做编剧,我是个剧作者,“巨人”,但是最近一个剧本让我心烦意乱,我甚至怀疑是否还有写下去的必要。如果说“巨人”只是一个玩笑(当然是一个玩笑),那么实实在在地说我开始严肃了。我怀疑剧作里人物的意义,也怀疑自己的意义,长时间在院子里关注蚂蚁和花朵。这是无意识的行为,当我意识到这点,还是恹恹地坐回电脑前码字,我还能怎么做呢,一个无意义的人孕育另外无意义的人并非无法忍受,世世代代无非就是这么延续下去的,事实上,我像大多数人一样,多多少少感受到了其中的快乐。我的妻子比我小五岁,她和我最新的关键词是“冷漠”,其实我不是这样的人,前一阵她还总说我狂野,她总是要唠叨点什么,女人嘛。但是老是这样唠叨我又不忍让她看起来荒谬,为什么总和一个女人较劲呢,反正到后来我都听她的,她总是正确的。我承认,这是溺爱,我知道这不好,但也不比原来更不好。有一次我们激烈地争吵了,她要我滚出去,这是我的房子,我家的祖业,但我还是依她了。我们很少争吵,这样对我们并不适应,她接着说她收回她说的话,我也依她了。我一直都是依着她的。六月初一个早上她留下张纸条和我告别。纸条压在电脑桌上,最后四个字是“你要快乐”。前面的五个字是“我走了。保重。”一共九个字,还没到两位数。我起床的时候已近中午,我夜里工作,起得很迟,不过她完全可以把我弄醒来告别,我可以送她去车站的,我记得她好像说要出一个月的差,我尤其记得她说就算不是出差她也很想出去走走,一个人走走。老实说,想到这点我很萎顿。我拿起电话,又放下了,我掏出笔,在纸条上面添了行字,“我努力快乐,”想了想我再郑重地加了几个字,“一路顺风,保重。”写完又觉得幼稚,我对文字的感觉显然越来越糟糕了。我伤心地画了把叉,笔把纸划破了,我干脆把纸条撕碎。
剧本的进展不顺利,一次在浴室构思的对白把自己感动得多出两个花洒,我装成阿基米德湿淋淋地冲出浴室,赤裸坐在电脑前,发现问题并没发生根本改变,或者根本没有改变。我很焦虑。作为排遣,我又挂在网上,他也常在,这样我们偶尔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我现在知道他比我大一轮,用他的话说“痴长十二岁”,在重点中学教语文,桃李满天下,有一个读中学的儿子,我们主要谈的还是家族的事,他问我答。我们还能谈什么呢?很多问题我回答不了,其实我对祖先的事一直不大上心,除了清明节上坟磕几个头让他们保佑,仔细想想,除了这个,我还有必要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呢。我突然回忆起我有好些年没上过山了。这让我有点吃惊。最近几年不是太顺,根本顾不上这个。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因为这个才一直不顺呢?我遗弃了他们,他们也把我遗弃了,但是我能算遗弃吗?我多少是个迷信的人。窗外的光有些耀眼,我站起来把窗帘拉紧,然后回到电脑前坐下来抽烟,他见我不出声就像往常一样说你忙吧不打扰你了。他已经把我打扰了,打痛了,只有那些过得滋润上老下小都摆得很平的人才有心思和闲情再去操心祖先的事。他们关心他,他关心他们,这些幸福的人啊。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对祖先的事如此感兴趣呢?我忍住没说的是为什么还要跑到我这边来呢?他沉默了半晌,这是原来从未有过的,接下来的话就显得很郑重,他说请问对历史对传统对根和来处的兴趣是件很奇怪的事吗?我按着桌子站起来,没有回答,眼睛瞟着窗帘的缝隙。他又说兄弟,这一切是有意义的,你如果仔细想想就会觉得里面的意义。我慢慢坐下,靠在椅上想了想,又想了想,他说还在吗?有什么事兄弟之间无妨直言?我说没事,我在想。我坐了好久,显示器慢慢黑了下来。
我们好几天没再说话,后来又说话了。到六月末剧本顺利了些,好人要死了,剧团执意要坏人死,好人要结婚。争执一番过后对方竟然让我有点同情心,善良一点正常一点好不好,“我花了那么多钱,拯救一个人,而且是好人难道都不行?你干脆让我死得了,你反正不就想好人死吗。”我妥协了,巨人总有个柔软的脚踝,怎么走下去还是他们决定吧。那天下午我又挂在网上,修老师和我说他明天去长沙,经过辰州。我破罐破摔地又妥协了,也不能说是妥协,而是推己及人的悲悯:一个人“小小的愿望”怎么就这么难呢?我很快地说好的,欢迎你来。我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他只停留一天就行了。我说好的。他说那实在是太好了,真的给你添麻烦了。我说不麻烦的。他不厌其烦地说真的不麻烦吗?这样说话我真的觉得有些麻烦了,但我还是言简意赅地说:真的。
他离我这里有三个来小时的车程。估计中午能到。那天是星期天,上午我到永生堂做礼拜,最近有不少乡下妇女来做礼拜,穿着不是很干净,唱赞美诗时声音却很虔诚很响亮,我不知道她们受洗了没有。捐了一百块钱后我出去抽了支烟。抽到一半符牧师走出来,他抱歉地说今天很忙。我说没事,我马上要走了。我和他说书下次给他带来。他说没关系的,慢慢读吧。
我走着去的车站。我在候车室坐了会儿,走到后面的停车坪里。坪里围了很多人,叽叽喳喳的,好像还有哭声,边上的人说大巴倒车轧到了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脑浆溅出来了。我远远地张望了会儿,只能看到若干长头发短头发的人头,我干脆走远一点,看了看时间,正想着是否给他打个电话,手机响了,他已经到站了。说了两句话后我注意到隔我几步远一个正在打电话的男人,他说的话和我电话里听到的无不同,话筒离得越远越清晰。我把电话拿在手上走过去说你是修老师吧。他还在说话,露出不喜人来打扰的样子,不过很快反应过来,他看了看电话,又看看我,他说你是……贤弟?我不大自在地微笑着,点点头,从来还没有人这样当面称呼过我,我说叫我小扬吧。其实也很少有人这样叫,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小名。他忙着把手机别到腰里,伸出双手,我的手机没来得及放回兜里,所以四只手和一只手机握在一起。他的手十分厚实,热乎乎的。头发花白,但是并不老相,穿着件圆领衫,戴副黑框眼镜,背了个蓝色的阿迪旅行包,脚上是帆布运动鞋,好像他是风尘仆仆一路走来的,而且他能够走这么远的路。他和我想象的样子有些不同,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和寻找剧中人的作者不是一回事,抽出手后我有些失望,对自己失望,我一直还认为我对人物的把握能力是到位的。
我犹豫着是先去吃饭还是带他回去冲凉。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他。他说不饿不饿,先回家吧。我们从车站出来上了台三轮,三轮车噪音太大,他说了几句话我都没大听清楚,我说什么,他大声说真好,就像回家了一样。他拉开遮阳光的布帘子,兴趣盎然地巡视大路和边上的建筑物,我靠在椅子上,避免光直射在身上。下车的时候他抢着付钱,一张五十元的票子,我说我来,他拦在中间,催着司机找钱,司机听他是外地口音就说同志这只一块钱的生意。他急急地说找我四十九吧,好像这是他的错误。司机有点过分地像上帝一样语重心长地解释说同志是一人一块钱。我终于凑到边上递了零钱。他的脸在太阳下红彤彤的,汗水上泛着油花儿,他说你这个同志你这个同志。听不出来他是说司机还是说我,也可能是说自己。我开始摸钥匙了。
我上午出门前把屋里打扫了一番,准备让他睡我房间,我则住妻子的那间房。他在院子端详了半天才走进来。他给我带了些土特产,姜片糖和蜜枣。我不吃太腻的东西,不过我没和他说,我说谢谢,你太客气了。他说天气热储藏在冰箱里会好一点。我按他说的做了,顺便给他倒了杯冰水。他还给我带来了他那一支的家谱,用小楷眷写在奏折般的黄纸上,我夸赞真漂亮。这是实话。他说:“这是枝丫,根还在你们这边。”收藏好枝丫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吹风,他不抽烟,我也没准备什么东西招待,喝了两杯水,聊了房子(他说宽敞,凉爽)和有哪些人(我说我一个人,所以宽敞,凉……爽),爱人呢(她出差了)之后,我带他到洗澡间冲凉,他自己备了香皂毛巾和一把深红色的梳子,这些东西装在一个精致的透明塑料包里。我坐在沙发上,听着洗澡间里流水的声音,好像我的待客之道就是里里外外灌水,只是这和网络没有关系,我已经在想接下来去哪里吃饭了。
他换了件白衬衣,扎在皮带里,由于压在包里的缘故有点皱,不过这个样子真的很像老师。我起立说吃饭去吧。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望修公?他接着带着点抱歉的口气说他是不是有点急。修公是我们家族最年长的一位,今年应该九十多,多多少不大清楚,按辈分是我的堂伯父,因为年纪长得太多,我叫他老伯伯。他家应该有家谱。来之前我答应过带他去他那里。我说吃完饭再去吧。他高兴地说好的,好像一块石头落地,终于能空出肚皮放心吃饭了。我们就在附近的一家饭馆,由于近,我和妻子在这里来过好些次。点菜的时候互相推托了一下,他说随便吃点家常菜最好,我按这个意思点了红烧肉,桂鱼汤,油花生,西红柿和茄子煲。我以为他会说太多,他并没出声,我又担心是不是寒酸小气了,我说不够再添。他郑重地日本人那样用力点头,好像表示绝对服从和尊重。我说喝点酒吗?他说不能喝高,只能喝一点。前面我们多少有点拘谨,碰了几次杯之后放开了,话语多了起来。他追忆了祖先的荣光,可能是放得太开,他说武功赫赫文名昭昭,他现在比我还清楚这个,我们在酒盏中高山景仰同时唏嘘感慨。关于这些我们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我岔开话问了问他教书还辛苦吧儿子听话否?他指了指花白的头发:“粉笔灰染的,”他笑了笑又说,“其实是遗传,我妈头发也白得早。”他儿子就在他教的班上,几次他把儿子和他的学生混为一谈,反过来说也行,他说现在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啊,有一次他还试图把我笼进去,这不怪他,人感慨起来有时就这样无边无际。问题是:他感慨的是什么呢?我也不好多问。他端起杯轻轻地抿口,问到弟妹,半天我反应过来是说我妻子,我说她出差了。去哪里了?我说她没和我说。他把酒杯放下来为我打抱不平,她怎么走了都不说一声去哪里呢。我说这不重要,走了就走了吧,一个人还自在一点。他扶了扶眼镜,正视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说:“你的意思是你们离了?”尽管我有时难免胡思乱想,还从未这样想过,也没这样看过,哪怕他把他的眼镜扣在我的脸上,如你所知,我们之间除了一张白条(是的,我签了字,又撕碎了)之外没有任何协议和证书。我喝口酒,告诉他没有这回事,只是走了。她走了,但这里是她的家,事情就是这样的。我说不说这个,妇人家又入不了谱的。他很理解,说不说不说。他提起瓶子给我斟满酒。
我喝酒一般吃不下饭,他胃口很好,倒是吃了两大碗。吃饭的时候他出了不少的汗,好像在田地种粮食,不得不拿下眼镜用餐巾纸擦拭,他自嘲说劳苦命的人就是这样。我说这样才健康。他笑了笑,仿佛很欣赏我这样说。结账的时候他又要抢着来,我生气了,我说我是地主,这是我的应尽之谊,打不定哪一天我还会去你那里呢。这样一说他把手缩回去,他说好好,说话算数,到时可一定得来。出来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太阳正猛。
我们没直接去修公那里,而是折返回来,他要取照相机。他还备了份礼物,和给我的一样。等车的当儿他拍了几张院子的大门,他说有历史有故事,一见之下就想摄下来了,从这扇门开始记录是不是很有意义?我要是老师我会告诉他打开门翻过段落大意还会找到中心思想。我不是,我咽了口吐沫啊了一声后学生样稀里糊涂地点点头,念书时我就是这样干的。
修公的家在一条又窄又深的巷子里,边上新搭的一些小建筑干扰了我的记忆,小小的干扰,我们还是走到门前了。父亲先前说过修公和祖父的样子很相像,比他还要像得厉害。家族里血液的流动是奇怪而微妙的。这个下午我带着他去看和祖父很相像的修公,以前都是父亲带我去的,我从没单独去过。我拨动门上的铁环敲出声音,敲了会儿我开始喊门,我喊老伯伯,同时继续拨动铁环。他说修公不会不在家吧。我说年纪大了耳朵背得要命。说完我扯起喉咙大喊了几声,声音在老巷子里起了奇怪的回声。我回头看了看,他也回头看了看,然后我们对视了一眼。
开门的是修公的女儿,她也有七十多岁了,我叫她大姐姐,而不是老姐姐,但她的确老了,老糊涂了,好半天才想起我是秋生的儿子,她对我父亲印象深刻一些。她把我们让进屋,他恭敬地叫了声大姐,呈上礼物。我向老姐姐介绍了他,不知道她老人家听明白了没有,她遗传了修公的耳朵。他微笑着频频点头,她掂量礼物,又像打量走失多年的儿子一样仔细端详他,她终于也点头了。她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谦卑地说“正”字班的叫正涛。我帮着说了一遍,她还是点头,说:“还好还好,都是一个班辈。”我说老伯伯他人呢,他身体好吧。“身体不好,”她反应敏捷,声音很大,生怕我们听不清楚,她捏起拳头捶了捶腰,“我一辈子没锄地没作揖,背现在却伸不直了,时常作痛。”“那老伯伯呢。”我说。她瞅我,仿佛没听明白,我只得再重复一遍。“他去年已经过生了,”她说,“他身体比我好,一直很好,睡梦中走的,安详。”我不晓得,没人和我说这事,我摸了摸头,有点出乎意料。“按他的意思,操办得简朴,没有惊扰大家。”她说。我记得今年初在白氏路上还见过老伯伯的,我甚至叫了他一声,他并没听见,显然那次不是他耳背,而是我看花眼了,我怎么会看花眼?他又不是花枝招展的姑娘,不是看花眼还能是什么呢?我感到有点惶惑。“我们应该来的,我会去山上拜祭的。”我轻声说,神情内敛而哀伤,大姐姐应该能猜出我说的什么,她偏过头看了看墙上,老伯伯在客厅对门墙面的中央上方笑眯眯地俯视着我们。大姐姐转过脸说:“坐会儿吧。”他挎着照相机肃穆地站在那里。他往里面走了几步,把照相机搁在方桌上,然后跨了一大步,在老伯伯的遗像前三鞠躬。这很符合礼仪,等他鞠躬完毕我也走到他适才站立的地方鞠躬三次。我后悔穿的是件不伦不类写满字母的T恤了。我后悔的其实还是我竟然没把老伯伯的生死搞清楚:“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不过这些诗歌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那里坐了大约一刻钟的时间,唠叨会儿家常,主要是他聊,大姐姐也不知道他们那支是何时分出去的。他和大姐姐提到家谱。
“大姐姐,”他现在开始这么称呼了,语态自然,“我能不能看看我们家族的家谱?”
“家谱?”她确定一下。
“家谱!”他肯定地而且听得出来是带着惊叹号说话。
“没有家谱吧,”她有点困惑,“有吗?”
我坐不住了,站起来积极地说有的。我和他的目光碰了下,他能听见我的话。“老伯伯曾经给我看过,”我在大姐姐边上蹲下来,“在《柘园诗草》里也附录得有一点的。”
大姐姐回忆了片刻,赞许地点了点头:“是有《柘园诗草》这本书。”
“我家里也有这本书。”我说。她接着说了说这本书,她甚至记得是她亲手把书送给我父亲的。“秋生比我要小十几岁,可是我得叫他小叔叔,他终归是叔叔啊。”她这样说的时候拉住了我的手背,用指尖捏我的手掌心,捏了好久时间,好像在纹路上徘徊。
“可是,可是,”我忍不住说,“你还能找到家谱吗?”不是我忍不住,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有责任落实一下,事实上,我早都应该,至少在他来之前把这个落实清楚。我一直是个实在人。
“家谱?”
她又来了。我们都点头,这样来得直接些。不过显然我们点得都没什么信心。我点得格外用力,为了鼓舞大姐姐,还有他。
“你看见过家谱?”大姐姐问我。
“看过,”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然后我思索了一下,“我记得老伯伯好像这样和我说过。”
大姐姐没和我较真,但他终于对我说话了,声音之大一定让大姐姐都听得清楚,“你是说你听老伯伯说的,”他说,“你记得。好像。”
我很尴尬,没有回答他,心想这就是说真话的代价。我为什么不能小小地骗一把呢?这样大家都好过一些嘛,对自己对他对大姐姐都是一种尊重,我为什么要思索呢。有的人一思索就总要出问题,就像我下棋一思考一定会把最臭的招找出来,而且自以为是地郑重落子。
“你老伯伯在就好了,”大姐姐拍着我的手背,“他了解这个,”她又对他说,“你要是来早些他肯定会和你唠叨好多,他是活家谱。”他曾经这样说过我,我想他一定也会想起这个。
“是我来晚了,”他沉痛地说,“他活了九十多岁,我还是来晚了。”
有人说过这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太早就是太晚了。这是一个安慰。
走出巷子之前我们都没说话,他走在我前面,我跟在他后面,我想他总不会就这样走了吧。到大街口的时候他在一株绿化树下站定住。他给我留了块阴凉地。我站在他身旁,犹豫了下,还是开口了。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说,“让你有点失望是吧。”
他叹了口气,接着是用力地呼吸,嘴巴动了动,想说点什么,还是没有吐出什么来。我只听见他嘟囔出一个“你”字,但是他决定还是另起一行了。他说我们现在去哪里呢?我说你说吧。“带你去龙兴讲寺转转?”我提议道,“唐朝的大庙,很不错的。”我又自觉很有分量地加了句,“贺龙北伐时送给堂祖父的一对宜兴花钵也保存在那里。”
“我们去祖坟看看吧。”他扶了扶眼镜,没理会我的提议,看着我说,“烧点香纸拜祭下。”
我抹了抹额头上的汗说时间已经不早了。
“很远吗?”他说。我说也不是远,不过要乘船才能去。“那我们就乘船去,好不好?”
虽然是问我好不好,但是他仿佛取得了某种优势,而且表达出某种决心。
“明天上午去行吗?”中午喝了酒,我有点晕,当然,也不一定就是酒的原因。我说,“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船。”他说那先去看看有没有船再作决定如何?他又说我刚刚答应大姐姐会去山上拜祭的。他这样说让我不大舒服,但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点了支烟,脑子也转过弯了,想今天把他心愿了了,明儿一早把他送走就算了笔事。话说回来,我也乐于看见他有所收获,尽管我很怀疑是否能有收获,不过他人既然来了,我总得尽到我的本分吧。我承认,这之前我做得不好。
“那好吧。”我说。
在河街我们各自买了些土香、烧纸和鞭炮。他说这些东西必须各买各的,他还买了四个苹果。我们在一只写着“洲头”的小机挂桨木船上等了会儿,我有点急,和船老板谈妥十块钱跑个来回。小机挂桨比三轮摩托的噪音还大,大腿都震麻木的,而且这种麻木的感觉还在顺着小腹往上走,我打开舷窗,麻木地看着劈开的河水,偶尔溅到脸上的水花让人清凉,我把脸往下俯得更低一些。影子黑黑地吊着。
二十分钟后到了“洲头”,我有十多年没来过这里了。我在这里没亲戚,不知道当初先人为什么把家族墓地选在这个偏僻村落里。我问过父亲,他也不知道。现在我站在田埂上,问一位面色黎黑扛着把镰刀的老头知不知道修家的墓地。我迷路了,我没和他说,装着能找到,有那么一会儿我也认为的确能找到,但我决定还是问问的好。老头嗅了嗅我敬的烟卷,夹在左耳朵上,偏过头比画着指路。
墓地还是我印象中的样子,好像小了一点,大概是那时年纪小,眼里的世界要大一些。这是块五百平方左右的开阔地,没有围墙,没有供台,至少现在没有了,只有二十几座墓和若干粗大的松树,格外寂静,充满阴翳。我们在外面站定了一会儿,他轻声说真大,比他想象的还要大。这里最大的墓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位居正中,墓碑已经断成三截,不过接起来依然竖立着。他拿出香纸,把苹果放在墓碑下面,默默地恭立片刻,才仔细端详碑文,我猜他是在碑上密密的文字里找他那一支祖先的名字,字迹漫漶,他伸出食指轻轻地摩挲,好像盲人一般。石粉沾在他汗湿的手上。他让我帮着辨认一个名字,我认不出来,名字已经浸到石头里面去变成石头本身了。我问他找到了吗。他说他还在找。后来他说老伯伯的墓没在这里啊?我说到我爷爷那辈基本都葬在公墓了。我点了支烟,吸完后说把香火点了吧。在弥漫的烟火之中我们拜祭了一番,他跪下来磕头,磕了九个,每次头抬起的时候口中念念有词地默祷着,当然我也磕头了,我也有话要说。礼毕他给每座碑都留了影。“你来一张吗?”他说。“不,”我说,“不必了。”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在这里留过影,抱着株松树露出大半个脸,红领巾绑在头上,作出胜利的手势,我记得有这张照片,可是记不得丢到哪里去了。
有一会儿他拎着相机沉思地站在哪里,喃喃地说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家族墓地,再不会有了。他说现在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孩子的孩子没有叔伯姑舅姨,没有枝丫,也就无所谓根了。“以后的孩子能够想象我们的关系吗?”他对我说,“他们能想象我站在这里的理由吗?”我正在想利索点办完好下山,老实说,别说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连我都不是特别清楚,我不大自在地笑了两下,推他一把,嘀咕着说:“你这个同志啊你这个同志啊。”
他在坟墓间走动,突然把我叫过去,指给我看最大那座墓后面的洞。“盗墓贼弄的,”他说,“真可恶。”其实这里大点的几座墓早都被盗过,后来请人修整了,我看不出这是修整的人偷工减料还是贼的穷凶极恶。
“真可恶,”我说,“有时间我请人过来。”
“你会请人的是吗。”
“当然。”我说。
他蹲在地下,用手捻土,而且放在鼻尖嗅了嗅。我也蹲了下来,很快又站起,我的肚子忽地受不了了,我要方便方便,问他身上有纸吗?他没有,不过他说山上有树枝树叶。
“能用吗?”
“它们是纸的祖先。”他说。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我怀疑自己是否和他说过我的职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我面前搬门弄斧实在可笑,但我笑不出来,仿佛被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怔住了。我边退边说我试试。
我在火热的草丛里纹丝不动地蹲了好久,汗水把我湮没了。我把一根筷子粗细的树枝沉下去,然后浮了上来。回来之后没看见他,他能到哪里去呢?我走到大墓后面看着那个洞,趴下去往内窥视,真疑心他是不是钻进去了。我在空地上五步一徘徊,不消说,内急过后我开始焦急了。手机没有信号,环顾左右的墓碑,除了等他我没有别的法子了。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哭哭啼啼吵着要来,一脱离我的视线又溜号了,把我一个人落在这里,孤零零地像块墓碑,或者说成心让我和周遭的墓碑合群。如果说非要谁等待在这里应该是他才对,我真想走了或者躲起来让他找不到我,如果他还来的话。我没动,一个小小的影子在大松树后斑驳的光影里晃动了一下,我仿佛觉得自己突然消失了,这样站在这里他也看不见我。
他的出现让我吃了一惊,不是因为他终究来了,而是他竟然这样来了。他赤着上身,白衬衣束在脖子上,照相机斜挎在身后,抱着块足有一百斤重的石头,从下面走上来,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空地中央,透过树叶的光线在他奇妙装扮后的身躯上造成了舞台般的效果。他像是从戏里面跑出来的,而且用力地把我往戏中拽去,有那么一刻我甚至认为这是我的戏。好一会儿我才迈开步子。他喘着粗气把石头撂在地上,一股脑儿把衣服和相机撸下来,拿下眼镜用手背抹脸上的汗。我狐疑地把东西接过去,挂在树上。
“花十块钱买的,而且说了一箩筐好话。”
“干什么?”我说。
他把眼镜戴回去,奇怪地看着我,仿佛我的提问过于幼稚。“把墓后面的洞封住,”他说,“现在你把它搬过去。”他改了主意,“还是我们抬吧,别把你衣服弄脏了。”
最后还是他把那个洞封好的,我基本上帮不上忙,他比我里手,干这个很在行,虽然费了不少时间。很奇怪,这块石头仿佛原本就是这里的一个部分,反正填进去看起来很妥当很齐整。做完这一切他像尽了性的老人疲倦而满足。他双手合抱着棵粗大的松树站立着,我怕他有什么不适,他说很舒服。我不大放心地看着他,他说你不试试?我摇摇头,他说你一定要试试抱住树干站在枝丫和树根之间的感觉,很棒。我说以后再试,我院子里有树。他没强求,松开手靠着树躺下来,我让他来支烟消消乏,他摇摇头,我自己点了一支。他眼睛微微闭着,头发凌乱,手指上是泥土屑和草根,眼镜搁在他起伏的赤裸的胸脯上(也就是乳头的位置)。我说不出我的感觉,莫名其妙地觉得紧张,上古神话里一个勇猛的神祇战斗中被砍去了头就是用乳头做眼睛的,胸被砍去后用肚脐做眼睛(现在是独眼龙了),整个上半身砍去之后他只能靠两条腿满世界茫然地奔走,当然你可以牵强附会地说他还是独眼龙,但这的确是最让我不适的一个神话。在山上待得太久了,我还担心船不会等我们,抽到烟屁股的时候我用它点着了鞭炮。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船还在,船老板发牢骚抱怨,我给他加十元钱,他一言不发慢吞吞地接了过去,不知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反正他的样子像我还欠他的。我的贤兄在河边洗手脸,晚霞铺在河面上,金光闪闪的,河水几乎看不出流动,但这一天总算是过去了。
夜晚我们吃的饺子,喝的啤酒。洗完澡天已经麻麻黑了,他说随便在家里吃点吧,我说冰箱里只有饺子,他说饺子好。好就好吧,主随客便,我一个人在家还经常捞面条。吃了喝了洗了也该睡了,他今天也的确累了,我也累了,不过他并没有睡的意思,拿着罐啤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只好打开电视,陪他坐着。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智力问答节目,他抢答了两个,回答不正确,题目本身也古怪,他没再答了,批评当下电视节目的低俗,在知识和智力节目中也概莫能外。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们沉默了会儿,主持人说加一百分,一个男选手耶耶地浪叫几声。我说在碑上找到祖先的名字了吗?他说还没有,有的名字比较模糊,回去需要再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又沉默了,我习惯独处,习惯了和剧本里的人打交道,事实上,我和妻子一起坐在电视前的时间都少之又少。我和他说他住的房间有电脑。他说看见了。他问我能不能把那本《柘园诗草》找来给他读读。我说当然。起身去给他拿,心想他拿到这本书躺在床上去读对我们来说都不失为一件轻松的事。我到房里找,书堆里,床上床下,抽屉和架子上,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书,天气闷热,汗在背上缓缓地爬。当初要不是这本书我就没有这么多事,在我需要它的时候它却撇清了。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一本书突然就失踪了,好多年后会发现它静静地搁在某个地方,或者就这样诀别了。我心情恶劣地走到客厅,我说书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又找不到了,”他把啤酒放到茶几上,视线从弱智的电视节目移到我身上。他用了个“又”字,而且摇了摇头。他的言行刺激了我,我没有回答他,打开冰箱取了罐啤酒。我喝了口酒,回到沙发上。我说书上和家谱有关的资料我都在网上和他说了,“我打了一个下午的字。”
“我晓得,你别介意我的话,只是,只是……”他欲言又止,又另起一行,“谢谢你今天带我去这么多地方。”
我又喝了口酒,我说不用说谢谢,我没帮上什么忙。他说不能这么说,已经很帮忙了,他又说好的,兄弟之间不说谢谢。我沉吟了下说我有点瞌睡了,他没出声,或者他没听见。我想了想又说去院子里坐坐好吗,外面清新些。他说好的。“我喜欢这个院子,很舒服。”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飘雨了,细细的,几乎没有声音。我们拿着啤酒罐坐在走廊上,说了说雨之后好半天都没说话,喝酒,看雨和雨中的大树,好像这样很惬意。
“这个院子当初一定住了很多人。”他说,“一定很热闹。”我说我从来没看见过热闹。
“可以想象,”他说,“我想象得到。”
“想象?”我说。为什么要想象,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一个语人或者说雨人与巨人的想象有什么不同呢。
“是的,”他说,“这是必然的。”
我太阳穴上的神经突突地跳了下,我突然觉得我可以和他说点什么,我想了想,指着西首的一间厢房,“我二伯婆在那空房里住了一辈子,至少在我记忆里是这样,我二伯公新婚没几天就逃婚去了贵州。”我顿了顿问他这算是逃婚吗?他宽容地说算。“他在那边结婚生子,从来没回来过,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这里,看他追悼会的录像带,他在那边混得不错,死时极哀荣之盛,家里人把二伯婆也喊来一起看。生前他按季给二伯婆汇生活费,但是二伯婆并不承认电视上的那个人是二伯公,她说他哪里有那么老,那不是他,她记忆里还是他离开她时的样子。一个月之后二伯婆就去世了。”
他轻轻地吁了口气,“愿他们安息,”我点了支烟,接着说,“我和你说过我祖父没有?”
“说过,你说过他葬在公墓。”
“他没有墓,原来有的,不过十年前迁坟(那里准备推成停车场)时发现里面并没有棺材,祖父是父亲安葬的,有三四十年了。大姑到北京诊病,姑夫在牛棚,大伯在武汉读书,家里只有父亲。他那会儿不到二十岁,祖父在家里——就是我住的那里——停了一夜,第二天请街上的劳力帮衬着上的山。这些都是父亲和我说的,他说埋好后用小锄头刨了条流水沟,左手是两棵小松树,他就是凭着这个记忆带家人上坟的。那时候破旧立新,好多风俗后来才渐渐恢复。他请地理先生测过祖父遗骨的方位,自己也上山寻了若干次,没有任何结果。”
“愿他安息,”他又一次这样说,“他终究入土为安,只是没有找到而已。”我说我父亲也是这样安慰自己,尽管他时常为此内疚。
“他那时还是个孩子,”他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不容易,我一直觉得他够强的,”我看了看他,“你还喜欢这院子吗?”
“是的,”他有点犹豫,好像在斟酌着怎么说,“这几乎就是本家谱。”
我晃了晃啤酒罐,喝了一小口,继续说下去,仿佛手指上蘸点吐沫翻动书页,不,就像点钞票一样,无法控制不点下去,“但是我父亲并不强。五年前一个早上他晨练后就没回来,我们找不到他了。”他说这和找不到墓,和他的内疚有关系是吗?“不是这个。如果说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只是父与子的关系。我母亲前年到长沙和我姐姐住了,从那时起只有我和我妻子在这里。”
雨大了一点,起了小凉风,忽地吹过时甚至有些寒意,雨丝偶尔随风飘到身上,周遭黑飕飕的,我们几乎看不见对方的脸。
“你为什么想起要和我说这些?”沉默片刻之后他说。我说我以为他会乐意听的。
“谢谢你和我说了这么多,也许,”他说,“说出来会好过一些。”
“和这些没有关系,”我的身子稍稍往他那边转了转,“你觉察出里面的联系没有?”
“什么?”
“我家的男人每一代里总有人到哪里去了,去了某个地方,或迟或早总会如此,哪怕死去了都避免不了,这是一个宿命,你在家谱里找根,我找到的只是总有一天我会去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
“我们现在在一起,你在这里。”
“这是一个悲剧。”
“你为什么这样看呢。”他说,“为什么不去想家族里了不起的人呢。”
“无法改变了,”我眨了眨眼睛,不确定是否说下去,我酝酿了下情绪,事实上,情绪已经把我湮没了,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以至我不得不咬了咬牙关,才一字一字地说出来:“我把我妻子杀了。”
我等待着他的反应,事实上我已经等不下去了,我咽了口吐沫,随手指着院子的某一处:“我把她埋葬在那里。”我们沉默了很久,冷场了,仿佛我们都被吓到了,连雨丝都斜斜地飘打进来。我无暇关心他,颤抖得很厉害,根本看不清楚,好像出于辩解我说:“我无法忍受她在这儿孤单地等我,如果某天我堕入宿命,我也无法忍受我在这儿等她,而把宿命颠倒。新血缔结新的命运,唯有如此才能永远……”
他突然老虎一样纵过来,逮罪犯一样从身后紧紧地抱住我。
“这不是真的,”他在我耳边大声说,“你不要说,你做不了这么残忍的事。”
我像一片叶子摇晃,不是我想挣开,而是不由自主地,他箍得越来越紧,我无法动弹。真可笑,应该是我控制他的,而不是相反。我的汗汩汩而出,像是他的胳膊压榨出来的,溪流一般汇入倾泻下来的雨水中,我担心把汗箍干净最后会箍出血来。会出血的。
“这不是真的,兄弟。”他好像是在请求我,又像是命令,裹挟着一股坚定的力量,和箍住我的双手一样。我感觉我是那块他在下午寻找到的严丝合缝嵌入墓穴中的石头,他抱着它,一步步地行走在细微的光里。我们走了好久。漫漫地或者说慢慢地我不再担心了,好像我从未担心过。
“这不是真的。”我说。我身体安定,气息均匀,就像感冒的人出了大汗之后。
“你好些了吗?”他说。
“我很好。”我说。
“真的很好吗?”
“真的。”
他松开我,双手做了个合抱的姿势:“还记得我在山上说的吗?”
我想了想,我说好的。“好的。”我用力点了点头。
我回到房间,给妻子打了电话,我哭了,这不是编剧,她也哭了,仿佛院子里从天而降的雨水。对这一切巨人并没做好预备。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