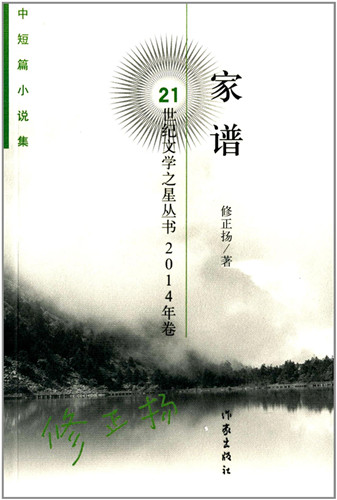
幸福村
文丨修正扬
十二岁生日夜我第一次梦到她。以前我从没正儿八经做过生日,后来也没再做过。这差不多是个闹哄哄的成人礼。我穿着妈妈做的小西装,行止得体,接受长辈的祝福,在表兄妹面前像个大哥,安慰吵闹哭泣的小孩子,我对自己的成熟表现很满意。现在我还记得自己那天小大人的做派和澎湃心情——我尽量不回望这些,这不是愉快的回忆,现在看来是这样的。
事实上第二天早晨醒来这感觉就起了变化,我在高的地方重新看待自己,低的地方看了床单和身体(在梦里面我表现也很成熟),呆怔片刻我躺下来。很忧虑。
她叫张娜,比我大五岁。
她又疯又野,大家都这样说,张阿姨也默认(这的确没什么好说的),不只是默认,还打她——我们小时候都挨打。
后来就不打了,其实每次都是张阿姨哭。快四十时她生了一个儿子,小儿子。
张娜不喜欢小孩子,从不带他玩儿,后来
连她人也见不着了。
好些年我们没再见到张娜,她去了长沙,也有人说是香港,她有个男朋友在香港,一次我在黑白电视上看到香港,还有她。我想是她,她的背影,一闪而过。
张阿姨不光有个儿子,她又有了女儿,但他们说这是张阿姨女儿的女儿,换句话说,是张娜的女儿。
怎么可能呢,这女孩儿有好几岁,会说话了。而她,张娜,还那样小。
街坊有时候就是乱传谣言,又恶毒又龌龊,像沟里流的水。
不过女孩儿站在他们一边,她叫张阿姨“奶奶”。
我不会相信小屁孩的话。张阿姨怎么会是“奶奶”?我为张阿姨的无动于衷气愤,她竟然不纠正那丫头的错误。
这就是她的教育。
张阿姨和我父母是同学,知青下放时在一个大队,张叔是当地人。张阿姨下放没多久就和他结了婚。他是条敦厚汉子,宽肩膀,红脸膛,几乎不说话,进城后一直这里那里打小工,很少能见到他人。妈妈说他长得好看,不然张阿姨不会嫁他。我没觉得他好看。爸爸也不觉得,他说不知道你们女人是怎么看的?另外,好看能当饭吃?不是这样的吧?
“总得一头想,”妈妈说,“我跟你也没享上一天的福。”
爸爸耶耶叫了两声,也找不出过硬的理由反驳。或许是他根本不想反驳,因为妈妈是笑着说的,看着妈在笑我问那小姑娘是谁呢?
“我操心你们都操心不过来,还有,你怎么不操心下自己的功课?”
“他知道关心姑娘了。”爸爸说。
“你等到就是的,你儿子出了事你就满意的。”
爸爸说儿子的好处就是不担心这方面会出事。妈妈反感他这样说话,而且她认为他从没在我身上用过心。
“好像这就是女人的事,”妈妈说,“归根结底就像是我一个人的事。”
“你能干吗。”爸爸在她屁股上拍一下就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我走开的时候妈说你跟他走就是,你怎么就不听听好人的话,听到心里面,而不是从另一只耳朵钻出去。
我不是跟在他屁股后面,我不跟任何人。
我溜到自己房里,然后拴上门。
后来我不再梦见她,不为这些梦困扰,这根本不算一个事。进入高中后我住在学校,半个月回次家。我偷偷摸摸谈爱,偷偷摸摸腻待在一起,有一次我拿她和她比较,我想这样做,但是我发现自己几乎把她完全忘了。这似乎有点奇怪,仔细想想却也在情理之中。我的姑娘很安静,她不出声,那时候也不出声,咬自己牙齿,咬我耳朵。她害怕,我疼。她没说我好还是不好。她是个好姑娘。
她一直是好的。是我不好。或者说,有的事情说不好。不提。
再次谈爱是工作以后的事,我没去读大学,所以这并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谈爱已经不能让我不孤单寂寞,落到实处也不行。我简直不知做什么好。我读了点书,从学校出来后我才知道我爱读书,爱到做爱时也读,自然还不至废寝忘食,如果对方不是完美主义者,她会发现这年轻人的缓兵之计,不失为一件愉悦的事情。事实上这里面没有什么愉悦的,难免她撅起屁股打我或者把书丢在我脸上,甚至把书撕了。
当然,破裂的不光是书。
我活该如此。好的方面是我被单位派到省城的一所部属大学进修,我乐意有个机会,期待有所改变。三年后我回来发现并没改变,而且,在学校里我又没读到什么书。
我还待在老地方。我住的地方叫“杏浒冲”,原来我一直以为是“幸福村”,出去念书前我才知晓。我给家里写过两封信。
张娜的弟弟叫张民,女儿叫张敏。张娜离家前她弟弟已经发蒙读书,看到他们就知道时间真快,一晃张民高中快毕业,张敏十六岁。第一次见到张敏她还扯着张阿姨的衣角刚会走路呢。
张民学习好,听话,模样声音都像女孩儿,张敏恰恰相反,成绩不好不说,还不学好,像个混小子,或者说,像她妈。她和她妈像神了,没有人知道她父亲是谁,容貌上也看不出有男人参与进来,仿佛就是张娜独力完成的,正如人们记得的,她太好强了。
张敏几乎是她脱的壳。“这孩子怎么那么像她妈呢?”
这意思是她真不该像她妈。张阿姨来我家几次都带着张民,我妈也只夸张民,绝不提到那丫头。我妈一直想要个女儿,老在我面前提这个羞辱我,我说现在不再迷信这个了吧。
“他真像个姑娘不是?”妈妈说,“你张姨总算可以吐口气了。”
我妈说啥我都基本同意。
“你呢,你呢,”妈笑了,“你什么时候让我吐口气。”
“我还好吧?”我迟疑着说。
“好,怎么不好,”说完她叹息一声,眼珠转动着又申明道,“我不是吐气。”
我妈就是这样的人。
我在库管局工作,单位上没什么事,不常去,这样有时间干点自己想干的事,这样或者那样,就是这样到末了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我和妈住在一起,她看得到,也许吧,她戴着老花镜读报时我就觉得是自己把问题看得严重了,摘下眼镜我又担心某天我会上了报纸。我在市里晚报每周有个豆腐块用假正经和夸夸其谈的调皮文风解答读者来信,我不是指这个,而是作为头版或者社会新闻的当事人。我可能还是看得严重了,无论如何,表面看到的总是真实的,这没错。
她也不满意我在报纸上写的小玩意。我说到年底就不写了。
“为什么不是现在?”
“我答应人家的。”
她看着我的眼睛:“你应该给自己写封信,诚恳一点,然后好好地作出回答。”
专栏上的信起初就是我自己写给自己,然后自己回复的,很久没这样干了。
我不会再走到老路上去,这也不是她的本意。
“我晓得,”我说,我点点头,“我试试看。”
张敏和我要好,我们是朋友,她说的,她说了算。她太小,还在念书,不过也几乎抽身出来了。我不能由她胡说八道,但我和她这样说她就掴我耳光。好多事情就是这样,一开始由着自己性子来,不瞻前顾后考虑清楚,等到清楚了祸福厉害,事情又由不得自己了。
我从来不是那种强硬的人。
她是名副其实的野孩子,孤僻冷漠,目中无人,走在街上根本不往两边看,迎面撞见认识的长辈也不打招呼,你和她打招呼,她也不打招呼,要不是没看见,要不是来不及,她总是走得太快了。最主要的,她根本不想打什么招呼。
两只蚂蚁遇见了停下来碰碰触角,嗅一嗅?她不干这样的事。
她有自己的圈子,一些臭味相投的野孩子,有时候她会和我说到他们和他们的事。
“这些畜生,”我忍不住喊出来,“怎么能这样干?”
“你伤到我了,你注意点。”
我像父母亲担心别的孩子把自己孩子带坏了一样,忧心忡忡地让她别和他们混在一起。
“你给我死开,”她相当老成地说,“本质上你就是这样的人。”
我是哪样的人?因为我和她混在一起?其实我忧心忡忡的更多是自己,尽管我们交往没什么人知晓,但纸包不住火,我不想藏掖这个累赘自己。无论如何,这事情到头来人们只会说是我的错。这当然是我的错,毫无疑问。
我开始找理由说工作忙或者身体不大舒服。
“你是不是每个月都有几天不舒服?”
我能说什么。我真的觉得不舒服了。
“别提身体好不好,”她说,“我用不着。”
这是真话。她说过以身相许,说笑而已,因为在我这儿拿了钱(不是金钱关系)。另外她说的也是以后,我是越来越不敢想以后了。
这样我更应该和她撇清关系。
我是这样想的,不是怪她,我怎么能去怪她呢,她经常好久都不找我,等你刚刚适应了她又像只猫蹿到你鼻子底下,喵喵喵地叫上那么几声,爪子抓到你心里面,甚至在那之前爪子已经在心里面。你控制不了自己,你有你自己的爪子,你生气,你甚至不确切知道为何生气:是她又找你来了还是她竟然迟迟才来找你。
初夏在铁马路游泳,她突然问起当初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说在她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我说真正的认识。”她坐在芦苇下面,“拉面馆吃早饭那次?”
“你说你想穿裤子,他们要你穿裙子,你不习惯,迈不开腿。”
“你招惹我。”
“我急着找个位子,面碗烫手。”
“应该是现在才觉得烫手吧,那时你一定想的不是这个。”
“你还是给我让了位子。”
白色卵石在太阳下,对面溪边空无一人,史前一样沉静。
“得意是吧。”
“那天好像六一节,你们要盛装游行?”
她从后面箍住我的脖子,恶狠狠地说:“你羞辱我。”我说我喜欢她。
“还是羞辱,”她贴着我的脸,“你好老,而且你根本不喜欢我。”
“那就不。”
她咬住我的嘴唇,然后放开,隔得很近地说:“你要死。”
“我要死。”
她手脚并用把我推到水里面:“去死,逗我玩,逗你弟弟去玩吧。”
溪流湍急,我呛了口水,更多的水裹着我飞快向下。
“你没有弟弟,你是软蛋,没主见的娘儿们,杂种。”她说。
挣扎了百来米我才爬上岸,膝盖磕出了血,我又羞又愤,甚至心慌意乱地拉开泳裤松紧确定一下。水往下滴。
我踩着青草往回走,她在半路上截住我,我推搡她,她搂住我的脖子。
“你哭了啊,原谅我好不好?”她说。
怎么会哭?那是溪里的水,汹涌的水。我无法推开她,这原谅又从何说起?
“我真担心你会淹死。”
我抱住她,又推开,我说了我无法推开,我们的距离刚好够我俯下身子亲吻她的乳房和上面的水滴。这是对我适才掉进身侧溪流里的补偿?
谈不上任何补偿。这是从哪儿开始,又会在哪儿结束?
我记不得了,我也不知晓。我厌恶我自己。
夜里我恍惚地回想了我的一生,从梦里滚落到床下面——自打一个人睡觉后我还没犯过这样的错——我梦见张敏,她在河里挣扎,脸庞像硕大的花朵,我打捞她,她的身体像水一样从我指缝中溜过去,越用力溜得越快,仿佛正因如此,我手里捧住的只是她的头颅,我拯救她却杀了她,不得不亡命天涯,这是我的未来。好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梦见张娜,她问我身后藏的什么呢?一朵花,我说。给我瞧瞧,她说。我不给她看,她还是看见了。好一朵美丽的花,她说。我绞着手悄没声儿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两清了。你说什么,她说。我说的是什么?说出的是什么?我没听见。我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巨大的惶恐中我才发现我手上捧的的确是一朵叫不出名字的大红花,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哭了。
我就会做这样奇怪的梦。我扯过被窝慢慢地在地板上躺下来。
我们也谈到她母亲,说得很少,她不想谈及这个,我也是。
“我问候过你妈吗?”我问她时她说,“别惹我问候她。”
偶尔她又会主动提起,不经意地轻描淡写地说她身上的新衣服是她妈寄过来的。
“她在哪里?”
她嫌我又话多了,过会儿又说她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她不总是在一个地方。”她说前年暑假去看她时住大宾馆,和王宫一样,每天早饭有人伺候送到房间来。
“还有游泳池,”她说,“中午我就漂在里面,天棚是透明的,天的颜色好怪异。有回我游得太猛,在电梯里呕吐了,吐得像个醉酒的猴子。”
“在香港?”
她懒得再和我说的样子,“是中国,我只能这样和你说,香港也是中国,随便你怎么去想。”她说,“你认识我妈,还记得她的样子对吧?”
“也许,让我想想,”我想了想,“看见了也许会认识,这么久她就没回来过?”
“回来过的,住在宾馆里。”
“有人喜欢冷冰冰。”
“什么?”
“没什么。”
“我读过你在报纸上的文章,还好玩,”她说,“有趣。”
我照实说这没什么有趣可言。
“我说了算,”她说,“什么时候给我写个故事吧。”
我笑着应允了。这是做梦之前的事情。
“不要太造孽,美好一点。”她温和地说。
我还是应允了。我想我可以做到,尽管我很少写故事。
“别勉强,我很强的,”她说,“我坚强。”
“我相信,”我说,“而且会幸福。”我点点头。
她身子凑过来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张娜就是这一年八月回来的,香港回归都好几年了,她一个人回来的。谈不上衣锦还乡,不是这样。她穿着破了洞的牛仔裤和白色吊带,扎着头发,拖着一口箱子,显然没顾及大家的感受,就是说,大家对香港的感受。算起来她已经三十多岁了,不再年轻,如果不说雍容华贵,至少也应该得体一些,如果没有车,实在犯不上拖着两个小轮子的皮箱,轮子若再大一些,这和黄包车有什么区别呢?
我是几天后听说的,我和他们说这没什么,大地方的人就这样随意自然,洒脱,率性。
大家就笑了,好像我是在嘲讽。
几天后我看见了她,她倚着护栏等谁,不是在巷子,而是城里的街心花园,尽管如此,尽管事先知道,我还是觉得没做好准备。她没注意到我,我也没有停下步子。
我和一个路人撞了个满怀,我道歉。
她几乎就是我记忆里的样子,比原来瘦了,但是一点没老,时间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
好些人肯定都有这样的感觉,过去了好些年,好些人还是记得她。
她仿佛把我们都忘了,她为什么要记得我们呢?她和谁都没有说话。
大家已经在传她去的不是香港,而是长沙边上一个叫星沙的小镇。她一直在那里。
“那她为什么一直不回来呢。”
“外面的钱好赚嘛,”王魁说。他在开翻斗车,替水泥厂拉水泥。“谁不想赚快活钱?”
“你就女的也赚不到钱,在哪儿都一样。”端午说。
“你是说我丑还是我硬脾气?”
端午说不管她去了哪里,她只要想回来尽可以随便回来。“我穿开裆裤时就认识她了。”端午也在开车,大卡车。王魁开了个玩笑,嬉笑着说是不是认识她你的裤裆才被戳破了?
端午不和他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端午有个狠角色的名声,王魁害怕了。
“算我没说。”
但是他已经说了,他也知道自己说话不算数,所以他亲热地说不会为这戳我几下吧?
“不会。”端午说,“我保证一下搞定。”
王魁没有异议,笑眯眯地点头。
这就是他说的硬脾气,反过来说,这样好,海阔天空。巷子太狭隘了。
张娜不在乎大家怎么看她,荣辱不惊,或者,在外面的这些年她已历练成这个样子,其实她一直是这个样子。她像是准备长久待下来了,在自家房子后面大兴土木,蚱蚂车拖来沙子、水泥和红砖,张叔也帮衬着干活,俨然还是个主力。
“好大的阵仗,砌房子啊。”
“搭个厨房。”张叔放下手中活向询问的人说。
“不是要搬迁的嘛。”
“说了几十年了……不还是老样子。”
下游的电站苏联人五十年代来测量选址过,后来苏联人走了。八十年代美国人和澳洲人来过,也走了。现在自己人在干,成不成也不一定。
“闺女回来了,要个干净地儿做饭。”
张娜在下午的时候会站在外面看他们工作,圾拉着拖鞋,指间夹着烟卷,头发松散地扎在后面。一次下班回来我顺便到她家对面的小卖部买烟,她刚好从家里慢腾腾地走出来,她看了我一眼,我不确定她是否记得我。我和她打了招呼。
我一直等着和她打一个招呼。
她眼睛眯起来,好像这样能集中精力。
“别说话,让我想想名字,”她说,“我能想起来。”
我微笑着等了等,她皱着眉头,想了那么会儿,不顺畅,甚至有那么几分挣扎的意味。我不忍心了,说出名字,她重复了一遍,点点头。
她问我在哪儿工作,我和她说了。她说结婚了?我说没有。
“女朋友呢?”
我不知道怎么和她说。我说:“这次回来准备住多久?”
“能住多久就住多久。”
她把我手上的书拿过去翻了翻,退给我。她说来支烟,我拈根过去,点上火。她又眯起眼睛,吐出烟雾。
“这些年了怎么就没一点变化。”
她是说我们这里还是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没变化呢?变又能变到哪里去呢?砌起一半的小厨房丑陋地立在那里,我不明白为什么突发奇想要建这么个东西,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不住宾馆,这些年她如果像张敏说的总是住宾馆又是怎么过来的?
我努力去想我记忆中她的模样,却不大恰当地想起张敏。我还看到我自己的样子,穿着蓝色的海魂衫和两个兜的短裤,打着赤脚,脚趾间夹着个小卵石,跟在她的屁股后面。
“你看看我。”我说。
“你究竟是谁,”她微笑着说,“我还得想想,好熟悉。”
说着她大声笑了起来,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笑,这并不出乎意料。我把书卷在手上,卷成个单筒望远镜。走出好远转身凑在左眼上朝后望了望。
她已经没在那里了。
我不再想看见她,我也没怎么撞到她。
有人言之凿凿说她吸毒,而且警察上门找她了。“是不是皇家警察把她的资料传过来的?”这仿佛有点太快,另外,还有人在派出所看见了她,他们开始互相串门儿了。
“有一天她会住进去的。”
我看不出她吸毒,我们局里也有几个人吸毒,不说我也看不出来,听人这样说了就觉得像是这么回事。不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敲打键盘,写信,又删掉。
我和三个同事乘船到乡下打了趟转,回来过后休息几天。
张敏给我打电话,要我出来。我说我在给她写故事,不出去。
“和你妈说会儿话吧,”我说,“陪陪她。”
“不要在故事里提我妈。”
“不提。”我问自己为什么不提。
她奇怪地听见了。“我不喜欢,越来越不喜欢。”
“她是你妈啊。”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不要提我从哪儿来,”想想她又说,“也不要把我弄成孙悟空。”
我说尽量把她写成观音。
“一柳条子抽死你,”她发狠说,“你先出来。”
我已经决定不再出去了。我想过一夜又一个白天,“不了。”我说。
电话挂断了,几秒钟过后她又打了过来:“你到底出不出来?”
“怎么了?”我说。
“我问你是怎么了?”
她不止我一个朋友。她有很多朋友,她和他们关系更好,更多时间在一起。
“这不好的,我想了好久……”我不知怎么说,“我写故事,我在那里面见你。”
“去你他妈的故事。”
“是你的故事。”
“去我他妈的故事。”
“你就不能给我个台阶下?”过了会儿她说。
“我出来,”我说,“我给你电话。”
“对不起,谢谢你,我不出来了,去你他妈的出来。”
她挂了电话。我用手指擦着手机肮脏的触摸屏,等着她打过来,她没再打过来。我关了电话。我没时间再这样下去,如她所说,我太老了,有的事对老年人来说就是肮脏的。看清楚这点让人不好受,另一方面,有勇气直面这个问题而且作出回答我没什么不满意的。
整个下午我什么都没做。
我交了个朋友。她先写的信,请求我回到她邮箱里,经常有人会提这样超出我工作的要求,这次我照办了。她叫李春,中学老师。我喜欢这个名字。她很快回信谢我,问我方便的时候能否和她当面聊上那么一会儿。这些本该在豆腐块里解决,上不了台面,但我还是答应了。两天后我们在城南的一家茶楼消磨了一两个时辰。
晚饭我们也是在那里吃的。
张民考上北京一所了不起的大学。我们城里不是每年都有人能考取这样响当当的学校,了不起,我们都为之觉得骄傲和欣慰,为他们家感到一点希望。谁好意思去嫉妒呢。这孩子虽然像个女孩子,但是有那么一股狠劲,有个主心骨,知道该怎么做,而且做得很不错。这真的让人高兴,不能比这做得更好了。我想张阿姨一定笑了,也许是哭,好些年第一次流泪不为悲伤愁苦的事儿,甚至把那些洗刷荡涤了,真好。
“民子,出去不会把我们这里全忘了吧?”
“不会的,”他弱弱地说,“我妈还在这里呢。”
“可以把你妈接出去享福啊。”
“我还有好些年书读,”他说,“读书是最苦的事,享什么福啊。”
这孩子为什么不能看得长远些呢,从另一方面看,他一步步走得真踏实。可不是。
“好好读出来,你妈靠着你呢,安心念书,我们帮你照看到屋里头。”
“谢谢了。”他客客气气地说。
“开点笑头脸,这是天大的喜事呢。”
他听话的笑了笑,好像只是为了让你高兴应付一下。读书人的礼貌。
张阿姨来我家的时候脸上已经看不见什么喜乐,她着实为学费愁死了。
“单位有办法没有,厂里还能帮上忙吗?”妈妈说。
厂里去年破产,能领到退休工资已经谢天谢地。显然,张娜也没挣回什么钱。
我妈借给她钱,这不够。“再想点办法,看我能不能再想点办法。”
我不知道是谁想的办法,很可能是大家知道了这里面的难处,自发的行动,街坊都捐了钱,就像红白喜事大家送份人情,五十一百的,也有人送出好几百的。
我妈帮她记账,她是会计。事后她还按张阿姨的意思用整张的红纸写了封感谢信贴在屋门口的墙上。本应该叫张民来写,他考试厉害,干这个却不在行。
“张阿姨自己可以写啊,”我说,“你们都是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嘛。”
“我喜欢做这些事,我喜欢帮忙。”她说,“你管得着?”
过后她又说,“你不晓得生活怎样毁坏一个人,这些年她是怎么过来的啊。”妈妈说,“读书时候可真是羡慕她,家里条件好,成分也好,有新衣有糖……”
“高中暑假我和你妈到河头挑沙,两分钱一担,老大的太阳,那时就像不晓得累,有人给活干就好,我带着你妈,他们瞧不上她。”
妈不同意:“是你跟着我,你说这样有力气。”
“两个地主崽子,好造孽。”父亲说,“人生就像三节草,你不晓得哪节好。”
妈看着我,她的样子就像回忆起了过去,她的心一直很年轻。
“看我干吗?”
她接着看父亲,嘴唇不屑一顾地向下撇着,然后往上一挑,鬼鬼祟祟地笑了,她总是忍不住发笑。他们一般大,高中同学,二十六岁结婚,在一起已经有三十来年。上个冬日回家他们正围在小桌子前看电视,戴着绒线帽,头凑得很近,嗑瓜子,灯泡低垂,可能和当时心境有关,我移不开步子,觉得这真的不错。这种真切的感觉像是锐利的刀锋。我找不到这种幸福了。刀锋难渡,我对自己的生活充满后悔。我很快爬上了楼。
张敏问我借一千块钱。她说以后不再找我了,除了还钱。那时候是下午,我让她到单位的宿舍来找我,她来过的。
她很快就来了,我装在信封里,她风风火火的样子就像很快会走,她身上有很重的汗味。
“我看见你女朋友了,”她转身和我说,“长得一点都不好。”
“在哪里看见了。”
“大街上。”
“我觉得还漂亮。”我说。
“假话,”她轻蔑地说,“明显是假话。”
我不想和她争,我低头抽烟,不出声。
“伤到你了?别生气了好吧,我们好合好散。”
“我们没好过……不能好。”
“你伤到我了。”她说,“我遇到大麻烦了,你还这样。”
“什么麻烦?”我不想问她的麻烦了,这会成为我的麻烦。我还是问他。
她说我帮不了,也不要我帮,她声音柔下来:“你已经帮我了。”
“张民什么时候走?”我换了个话题。
“很快,”她说,“他早就想走了,迫不及待。”
“你以后可以去北京看他。”
“我去别的地方,如果我出去……我要出去的。”
“你也可以好好念书。”
“我不是他,他是男的,”她突然说,“他只是长得像个女孩子。”
我看着她的嘴巴,顺着她上唇的曲线看她身后墙上的画。那是《通俗歌曲》的八开黑白插页,四个奔跑的男人和他们脚下的阴影。背景是天线杆,石拱桥,低垂的天穹。
“他喜欢我,实实在在喜欢我,”她说,“他野蛮得要死。”
我眨眨眼睛,然后眯起来,咧开嘴轻轻地吐了口气。
“好多人喜欢我,他根本不算个东西,我只是可怜他。他要我可怜他。”
“好了,”我说,“好了。”
“他要我叫他叔叔,平时他并不这样要求我,平时我叫他名字。”
“好了,”我说,“你疯了。”
“我要叫,我要叫了。”
那是尖利的让人起颤的声音,就像顽童用调羹在瓷碗上故意划动,一下一下,极其疯狂极其耐心穿过胸腔突突跳动,共振过后裹成一团堕落腹腔,一拍两散,一张满是皱褶的小脸。但凝神去听,什么也听不见,安静又光洁。她没事人一样摇晃腿,没有表情,安详。
我觉得需要说点什么,说点什么,说什么呢?说在她这么大我也做梦,梦见和某某有关系,实际上并没有,没什么,有什么啊。那是梦,是不是这样。是不是。
“不是真的。”我肯定地说。
“你就不可怜可怜我?”
我看着她。
“我骗你的,”她说,“你用不着做出那样子,没什么。”
“我晓得。”我说。
我迟疑着站起来,走过去抱住她,拍了拍她的背。
“你这样很可笑的。”说着她就笑了笑,“谢谢你的钱。”
她推开我,推开门,用力拉上,飞跑着下了楼梯。
张阿姨送张民去北京读书前到我家拜访。她在北京准备待段时间。
“如果在那边能找个事做就最好了。”张姨说。
“陪读?”
张姨的意思是待在这里她能干什么呢?家里没什么放不下,去那边安心一些。
“他只会读书,其余不会什么,”张姨停了下又说,“这也好。”
“这也好。”我妈说。
张姨串联时去过北京,我妈到武汉长江大桥打了转身,因为天冷。这次天气好,而且可以见到毛主席,上回在广场等了两天没等到,一直传言要来接见的。张姨说这回有空会去看看,这回是他在等了咱们了。
她们还说到她们突然中断的学业,读书时的好成绩,一篇漂亮的作文。
“他能写点东西完全是遗传我。”我妈说我,“可他就是不认真写。”
过几天他们坐早班车很早走了,去北京要到市里坐火车,不早不行。
打架的事我后来才知道,端午被人打了,打得很重,用这里的话说是“五脑七伤”,脑袋缠满纱布,大了不少。王魁说这样很好了,比碗大的疤要好。这事当然跟王魁没有关系,五个提马页子和擀面杖的小年轻干的,黑社会。“根本不问你一个字,不来这套,干脆得很,”王魁说,“话多是水。”大家都觉得端午活该,他竟然和张娜混在一起,光明正大地坐在他的副驾驶座上穿过整条大街,敞开窗户亲嘴。端午是有老婆孩子的人,这样太出格了。
这事当然也不是他老婆指使人干的。她干不出这样的事,她甚至不说他,她说他是和一个死人混在一起,这样能有多久呢?她到医院服侍他。她庆幸就只伤了一个脑袋。
“你好蠢啊。”他老婆心痛地说。
他还把自己的车赔进去了。车子换了包子。这里把毒品喊包子。车还在他手上,但他只是打工的司机了。
“你没有吃包子吧?”
他没有吃,她说那就好。能抵挡住这个的诱惑,的确是对他没能抵挡住那个诱惑的慰藉。
“我现在清醒了,”他轻轻地摸着脑壳,“打打就清醒的。”
她从来没打过他,都是他打她,但也很少打她,她太温顺了。
他还说这辈子都是他打别人还没被别人打过,哪有这样的好事,他早等着这一天的。
他们赔了端午医药费,这事算是了结了。他和张娜的关系也算是了结了,至少看到的是这样的。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能看到张娜和“社会上的”——不一定是黑社会,就是什么都不干或者不务正业的混社会的年轻人混在一起。他们有时候会来杏浒冲找她,据说黑社会老大也来找她,一个肥胖的秃子,走路一晃一晃的,还横着,胖男人和瘦女人,这一切都怎么了。
你要安静。她说,你要安静。我们安静地裸身躺在一起。我们算是谈过爱了。我们谈到结婚,谈到未来,谈到在哪儿买房子,谈了不少。
“你犯不着那样用力,”她柔声说,“我们快乐的对吧。”
她个子小巧,身体却结实有力,一团肉。她在学校是女子百米冠军。
我的头在她的胸部磨蹭,她抱住我的头,手指在我的头发里。
“你回答我。”她说。
我回答了她,接着我用行动做出回答。画蛇添足?她并不这么认为。隔得很近的时候她显得柔软漂亮,自有迷人之处。
过后我睡着了。
她打来电话时我以为是张敏,她说是她,她想起来了。她是笑着说的。我说想起什么了?
“想起你是谁了。”
“我是谁?”
她不笑了,电话里听得到抽烟的声音。“我后来就想起了,”她说,“我一直记得的。”
我没出声,摸索着点了支烟卷。
“我是不是不记得还好一些。”
我抽烟,咳嗽。我没做好准备。我甚至笑了笑:“不提这些,不提,好多年……”
“那时你好小啊。”
“你还提!”
“不提。”她说。
沉默。电话本身的电流在机身里窃窃私语。
“我记得的,”我突然激动了,声调起了大变化,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是个偏执自闭,自以为是,胆怯又执意倔强,时常虚弱无力的家伙,这声调把我的秘密暴露了。“我记得的,”我说,仿佛和自己赌气,我使劲地说,同时又一次觉得自己的虚弱无力和由之而来的似是而非的矫情。我挂了电话。
坐在沙发上我脑子一片空白,眼前晃过好多破碎凌乱的片段,我想到很小的时候,再大一些,想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是这个样子。过去总以为一个人如何影响一个人,一件事是如何关键重大足以改变一个人,这也许不错,在别人的经验里是可能的。但现在我觉得这实在不算什么,和这并没多大关系。若说命运,从很大程度上这是有道理的,不过命运有什么值得去想的呢,想这个有什么用,想都不要想。还有爱,如果能称之爱,这东西差不多也是命运,我无法解释这个,这和我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关系,我甚至不能说这是我的命运,我说过这些不算什么。这着实让人委顿,我不能再说自己糟糕,这真的真的不算什么。
我平躺下来,把烟卷从嘴唇间拔出来,翻身将脸埋在沙发的垫子里。
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刘婶在自己小卖部门口骂人。她到后面厨房打转回来,抽屉里的营业款不见了。她还发现一直坐在对面自家屋门口小板凳上的张娜不见了,所以她跑到张娜屋里问她刚才看见有人进铺子吧?张娜没有看见。
“有多少钱呢?”她打着哈欠问刘婶娘。
刘婶没数,她想张娜没来得及数,一会儿可以数清楚,而自己没机会再数了。
她站在铺子前骂人,她说:“砍脑壳的那门要钱啊,要死啊,买纸钱给自己烧啊。”
还说:“我这钱来得容易?小买卖一分钱一分钱挣来的,不是卖逼,不要脸的逼。”
又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就算你是鸡,我又不是往地上撒的一把米。”
大家围拢过来看热闹。张娜坐回到小板凳上,漠然地看着圈子,事不关己地抽烟。
有人说算了,折财免灾,以后多提防就是了。
“没有钱大家捐,”她继续说,“又不是没募过捐,偷人我不管,有本事把我家老王偷走我都不管,偷钱不行,那翻天了。”
人越聚越多,动静越来越大。有人偷偷看张娜,看她的反应。
“你是在说哪个呢?”张娜终于过来说话了。
“谁偷的就说哪个,”刘婶说,“谁认为是哪个就是哪个。”
“你说话注意点。”
她说就是太不注意,所以才被人偷了钱。
“你一定要说我?”
她是这样认为的,还会是谁?但是又不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她的老脸憋红了。
“我不怕你的,”刘婶说,“我不怕黑社会,一把老骨头有什么好怕的?”
“你闭嘴好不好?”
张娜说得很凶,刘婶说我钱被人偷了说说都不成?你还敢打人。
张娜瘦弱得不像个样子,像根羽毛,一阵风都会让她脱离大地,这时候她仿佛被自己的气流托在半空中,刘婶怔怔地望着,惊讶地张着嘴,她是可怜她还是惧怕她,或者怀疑是不是真是她偷的了?
她家老王把她往屋里拖时她才喘过气,她对自己男人说你做贼心虚,欠她的啊。
“蠢婆娘。”老王说,“非要惹出病来是吧。”
大家都笑了。大概想象老王这个老胖子和张娜在一起很有趣。
张娜拨弄着手机,看短信或者看时间,她还抬头看了看天。
这时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女人过来操着普通话打听张敏的家住在哪里?
她比我迟来一会儿,进巷子时我和她打了个照面,她走得慢,她没看到另外一幕的尾声,她说她是三中的老师,她来找张敏的奶奶。大家说奶奶不在,她妈在那边。
“你是张敏的妈妈?”
这个年轻的女老师像小学生在家长面前一样抽抽答答地哭了,嘴巴里都是水,水把她的话都打湿了,粘成一团根本听不清楚。
大家的注意力到这边来了,她为什么要哭呢?
张娜皱着眉头朝地上吐了口吐沫。
老师把眼镜取下来,掏出纸巾揩脸蛋,把嘴里的泪水清出来。
“对不起,我真的好难过,”她几乎又要哭了,“我忍不住。”
她还是普通话,但终于不再哭。这样她说出来的话大家明白了。
她说她把张敏留在办公室写检查,她从教室里回来张敏已经不见了,办公桌里的一千二百块钱也不见了,那是学生缴上来的资料费。
她怎么不到屋里单独去和张娜说这些?她一定是哭昏头了。
大家的头一定也被她搞昏了,还没看过这样的连续剧。
“那是学生缴的钱,不是我的。”她说。
“你来是和我说……”张娜声音很轻,“是想说张敏不见了还是钱不见了?”
“她夜里会回来的对吧。”
张娜好像没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幅度很小地摇摇头。
“我赔不起,我刚参加工作,那是学生的钱。”她反复这样说,“他们缴上来的。”
“你怎么就知道是她拿的?”
“有张条子,我让她写检查,她写了借条。”
她在衣服兜里摸索,从左边口袋到右边口袋。
“我不要看,”张娜强硬地说,“我想看到张敏,你怎么不担心她不见了呢?”
她仿佛被这个新问题吓住了,手慢慢地从兜里抽出来。
“我要报案的,我问了,五百块钱可以立案,我没有办法了。”
她又哭了,肩膀抖动着,她哽咽着表示警察也许可以帮张娜把女儿找回来。
有人安慰她说这有多大的事呢,都会回来的,老师不哭。
老师还是哭,她看样子就是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女孩儿。
“不是有张借条嘛,”刘婶说,“好好捡起来,警察帮不了你,别往那上面想。”
有人说捐点钱帮帮这小老师?
这话说得不是时候,听起来不舒服,我们这儿并没有捐钱的习惯,还不是钱,是不舒服。
“你走,”张娜木讷地说,“你走开。”
几乎没谁听到这话。
张娜自个儿走了,转身走几步,突然蹲下来,捂起脸哭了。
大家不再出声,老师也不哭了。她准备上前劝劝时有人拉住她,这个年轻老师收住趋前的脚,面色凝重,这是她进来后第一次看起来严肃镇静。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好多人听见张娜这样大声自语。
说着她的身体一歪倾倒在地上,就像她说的一样。
我们把她弄到屋里床上时她醒转过来。她还在说着什么,声音却轻得多了。
我给她倒了杯水。
“你们出去,让我躺会儿。”她说。
我望着她,我不知道我能帮上什么忙。“你们出去,”她指着我,“你出去。”
我到门口时她突然大声说:“我要走了。”
这是本意还是隐喻?她还能去哪里呢?
“我要一张票。”
“躺着休息会儿……”
她不大清晰地又重复了一次,我想她说的是票。我突然觉得受不了,我捂住嘴,捏下鼻翼,慢慢让手掌移下来。我往外跨了一步,拉上门。
那个女老师还呆呆地立在小卖部的屋檐下面。
“没事,没你的事。”刘婶说,“钱丢了就丢了吧,为这个哭,不值得。”
她摇摇头,“要是张敏真的不回来呢?”她说,“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
“这是好事,去哪儿都比这儿强。”
我搬出去住了。在这里搬迁之前搬出去了,在帮父母搬家的时候回来了几次。
政府的人提着石灰桶开始在房子的墙壁上画圈圈,圈圈里面写个“拆”。拉着皮尺量面积的人很快也接上来。人们问什么时候搬迁,测量员抖着皮尺慢腾腾地说你们以为我做的是无用功?大家很快知道给他买烟抽。不止这里拆,大半个老城都要拆掉搬迁。说了几十年,这下还是来得太快了。大家都很高兴,好像新生活一下展开了。也有不高兴的,张叔就为他砌的厨房的补偿起了冲突,老实人爬到房顶气呼呼地说不能这样子欺负人。
“老哥下来啊,居高临下怎么说话呢。”
“我儿子是大学生,迟早去美国,你们别欺负我。”
有人说他还有个女儿在香港。这时大家想起又有好久好久没见着张娜了,还有张敏。
“你这是欺负我们呢,站在那儿能站成个岛了?水来了这就是块小卵石。”
“你们是卵石,我是蛋。”
“那你下来啊。老哥。”
他应该是下来了。现在那里全是水,没被水淹的地方也被泥土填平夯实,成为沿江绿地啊广场啊的一个部分,反正不容易找出那里的确切位置。有一次我试图这样做,看来看去搞得眼眶里全是水,水上面是跳跃的光,晃眼睛。我还看到通往广场那条坡道的中段有块蓝色的路牌写着“幸福路”。他们搞错了,我搞不清确切位置,他们确切地把名字都搞错了。那一瞬我很激动,就像担心自己写的信无法投寄,或者好心人无从通过挂在脖子上的联系牌把年迈的我送回家。我在路牌前站了好久,我又看水,水面的光消逝了,多平静。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