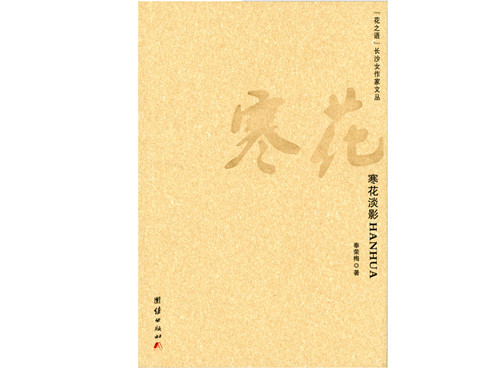
“零公里处”的风景
——读奉荣梅散文集《寒花淡影》
文丨刘羊
(一)
不知道是第几次打开《寒花淡影》这本淡雅厚重的散文自选集,不自觉翻到《黄棠山庄蝶恋花》一文,作者在引述了毛泽东著名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后,笔锋一转,写起了探访伟人词中主人公之一的柳直荀故居的经历:
“五十多公里的路程,山林越行越密,《蝶恋花·答李淑一》或哀婉或激越的越剧旋律,一直缭绕于耳边,总觉有一只蝴蝶振翼在连绵青山的山际线上,最后引领着我们在一条仅容车身的乡间土路颠簸,山边的枝条芭茅拂拭着车身的尘土,在几丘狭长的稻田尽头,蝴蝶飞进一栋三面环山的孤零零的白墙青瓦民居。”
这是一段引人入胜的文字。作者的文化记忆与伟人诗词、越剧唱腔中的蝴蝶意象水乳交融,构成一幅奇妙的乡村风情画。有这么一只充满灵性的蝴蝶指引,这段追慕高洁、寻访古人的经历,就增添了别样的情趣,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这个冬天,奉荣梅的文字就像一只蝴蝶,引领我走进她记忆和生命的零公里处,看到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回望家园、回望人生的别样风景。
(二)
“零公里处”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指的是道路的初始点。作者在《道州,零公里处》中写道:“故乡,是一个人零公里处,那里雪藏了我们曾经的笑与泪,惶惑与无奈,希望与梦想”。这样的感悟就像春天让枯枝开花,给“零公里处”注入了个人的体温和情感,成为全书若隐若现的情感线索和心灵足迹。
道州,是作者的出生地,也是她的文化启蒙地,作者在这里求学求知,度过了难忘的青春时光。多年后,当她已经离开了这片土地,依然通过这片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这是因为,“道州,不仅是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零公里处”,不仅是清朝大书法家何绍基的“零公里处”;道州,也是对濂溪先生膜拜的朱熹、蔡元定两位大儒,以及程颐、程颢、苏轼、黄庭坚等“濂溪学派”理学精神上的“零公里处”。这份在中国文化史上足以傲视群雄的名单,无疑给了作者足够的文化自信和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勇气。
我在初读《道州,零公里处》这篇长篇散文时,曾经疑惑作者为何把足够的篇幅给了蔡元定这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南宋大儒。毕竟,身列朱熹“庆元党案”59人伪学黑名单的蔡元定只是一介布衣,而且流放道州不到两年便不幸病逝,以致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失踪者”,即使在有关著作中略有记载也语焉不详。而相比之下,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周敦颐、何绍基,还是寓居于此的柳宗元、寇准均是开山劈石、不可再生的文化巨子。
高明的作家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她能在历史的遮蔽处发现真知,在苦难的人生里窥见光芒,在尘封的文稿中探求意义。经过作者找矿式的发掘,我们看到了一个正直豪迈、博学才高、一心传道、视死如常的伟男子形象:当蔡元定以花甲之年即将押解三千里之外的蛮荒之地时,他泰然赋诗“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与朱熹临别前,他们为了订正易学名著《参同契》同榻共宿、“终夕不寐”;抵达道州后,蔡元定不顾体弱多病授徒不倦,不仅把“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的慎独精神传给一代代道州子弟,而且写就了《易学启蒙》、《脉经》、《玉体真经发挥》等一系列学术著作,为他毕生所志的理学画下一个完整的圆;当病入膏肓时,蔡元定知道大去之日临近,请木匠制成棺木,他亲自躺卧其中测量大小。一日,蔡元定摆酒设宴约朋友相聚,告诉大家告别时刻到了(“此会是与诸友别矣”),并说大家有什么疑难问题,要问就早点问,以后想问我恐怕也回答不了了(“诸友有疑难问题,欲问者,早日问之,后我不复能言”)。不久之后,一个风雨大作、天昏地暗的凌晨,蔡元定“衣冠端坐而逝”,一代理学大师就这样走进了历史。直到800年后,通过作者饱含深情的笔墨,蔡元定才得以从充满喧嚣的历史烟尘请出,照见了这个犬儒遍地、斯文扫地的时代,照见我们这些虽同系濂溪一脉、而儒家精神全无的凡夫俗子。
作为《寒花淡影》的开篇,作为以向蔡元定致敬的厚重笔墨作为书写故乡人文地理的精神骨架,岂是随意而为?蔡元定在临终前给终生师友朱熹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写道:“天下未必无人才,但师道不立为可忧矣。”蔡元定没有想到的是,800年后的今天,师道不立、世风日下已成为这个文明国度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和受人诟病的最大软肋。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利益的最大化追逐和道德的缺席使得“他人成为地狱”,社会弊病丛生,几乎人人沦为欲望的奴隶。当复兴文明、重塑道德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取向时,作者把目光投向世所共敬的濂溪书院,投向宋明理学发源地,引导大家在文化和良知的“零公里处”感受儒家思想的共振,重温高尚人格的灼热,接续伟大文明的断裂。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传承和责任担当。在作者的笔下,无论是“断不负所学”的蔡元定、“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还是“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柳直荀,无不诠释了也光大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担当精神。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亲淡菜盘。
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周敦颐的这首《任所寄乡关故旧》被作者引用在《道州,零公里处》,无疑,这是儒家精神的最好写照。
(三)
听乐曲《梁祝》,最感人的莫过于“化蝶”一段;读《寒花淡影》,最难忘的是作者对于生死的领悟,竟如“化蝶”一般千回百转,扣人心弦。
人到中年,见多了花开花谢,人来人往,自然会对生死有所察觉,有所敬畏。作者的丰富之处在于从社会、民俗、家族、亲人、气场等不同维度观察生死、描写死亡,把死亡从单曲写成了组曲、由黑色画成了彩色,也使散文拥有了学术的视角、小说的结构和戏剧的品格。
《短路的家族血脉》和《七月半烧包》是两篇直面生死、超越生死、感悟生命的散文。前一篇通过为大舅送葬回顾了大舅的艰难一生和外婆家族的发展脉络,写出了对一个疏远已久家族血脉的回归之情,蓦然回首,“时间去哪里了、亲人去哪里了”的感叹油然而生;后一篇通过对湖南七月半为新亡亲人烧包这一民俗的细腻描写,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楚人以死为生、相信轮回的达观,也道破了乡村中国数千年来情系血脉维系家族巩固家族的秘密。在烧给祖先的包封上,作者意外地看到父亲以外的几代逝者的名字,突然感到“一股热流在血脉里流动,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家族四代的血亲,就是这样以断续的形式在延续,就像省略号一样,一个个单独的小点,单独看来似乎断流了,而将几十年几代人联系起来看,就是一个延续和传承,无穷无尽。”这不就是中国人代代相传、无法更改的家族观、历史观和人生观吗?
有了这种对待生命的旷远达观,作者在《偶然的二十五年》里对早逝妹妹的追忆,在《生与死的气场》里对葬礼仪式的细叙,在《拿什么来换健康》里对住院情景的描绘,在《步行街与医院》里对青春绽放与生老病死的对比,就有了一种长歌当哭后的超然,一种悲天悯人下的从容。在《生与死的气场》中,作者从苍蝇萦绕在死者盖着黄草纸的头上敏锐地观察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场,“当身体很好时,当身体很好时,人的气场就大,当身体不好或生病时人的气场就小,当人死亡时、身体周围的气场就离人而去。”不仅如此,她还在殡仪馆的别墅里看到了有钱人家和贫寒之家办理丧事不同的气场、丧事前后不同夜晚的氛围、不同子女亲属对待生离死别的态度,等等。当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这一切娓娓道来,我们在唏嘘之余不禁窥见了生命的本质。全文读毕,一定会对百岁老人杨绛先生关于“生死、灵魂、本性”的终极思考有了更多的感受,也自然会认同作者这样的感喟:
“人世间,不论贫富贵贱,终有一死,灵魂踏歌而行,不失一种最后的体面的归宿。”
(四)
数日来捧读《寒花淡影》,唱片里不时传来毛阿敏的歌曲,其中一首《思念》是她的成名曲,歌中唱道:“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听着老歌想着朋友。算起来,我与该书作者相识已有十六年了。十六年前,她是编辑,我是刚进大学的普通作者,我们因投稿发稿相识却未谋面;大学毕业后,她是编辑,我是同处一城的机关文员,我们偶尔文稿电话往来但仍未见面。第一次见面是2009年,我在北京学习,她去北京出差,不经意间,这只蝴蝶飞进我客居的窗口,两人从此对上了号,成为朋友。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古人常有博弈之交、饮食之交、势力之交、君子之交等种种说法,其实,对于朋友来说,最重要的交往便是文字之交。日常生活中难以了解的学养、性情、志趣、抱负,从一个人的文字当中可以轻松汲取。可以说,一个人的创作便是他(她)的生活记录和心灵隐私。走进他(她)的文字,便走进了他(她)心灵世界的“零公里处”;领会他(她)的心灵风景,便有了一个零距离的朋友。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无疑是幸福的。作为一名编辑,她就像一只蝴蝶,在万花丛中自由飞翔,得以见识不同的风景;作为一名作家,她又像一只蜜蜂,遍采百花酿出自己的蜂蜜。而她的散文就像她名字一样,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散发出一缕沁人清香。假以时日,这株寒梅一定会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本文2015年刊发于云南日报副刊。刘羊,青年诗人。)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日报新媒体
湖南日报新媒体

